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杨延斌推荐语:25年前,我亦师亦友的北大荒作家杨孟勇,创造了57岁做心脏移植的世界奇迹,并接续创造了心脏移植不久后停止服药、健康地存活了25年的人间神话。杨孟勇用一颗不正常的心脏,把生命的不可能活成了可能!他的神奇故事,曾经由中央电视台等几十家电视台制作专题广为传播。长篇纪实散文《活下来再说》,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推荐连载此书,意在引起读者对生命的尊重和感动,同时感受这个社会的优越和温暖。尤其要向给予杨孟勇二次生命的哈医大二院、及其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著/杨孟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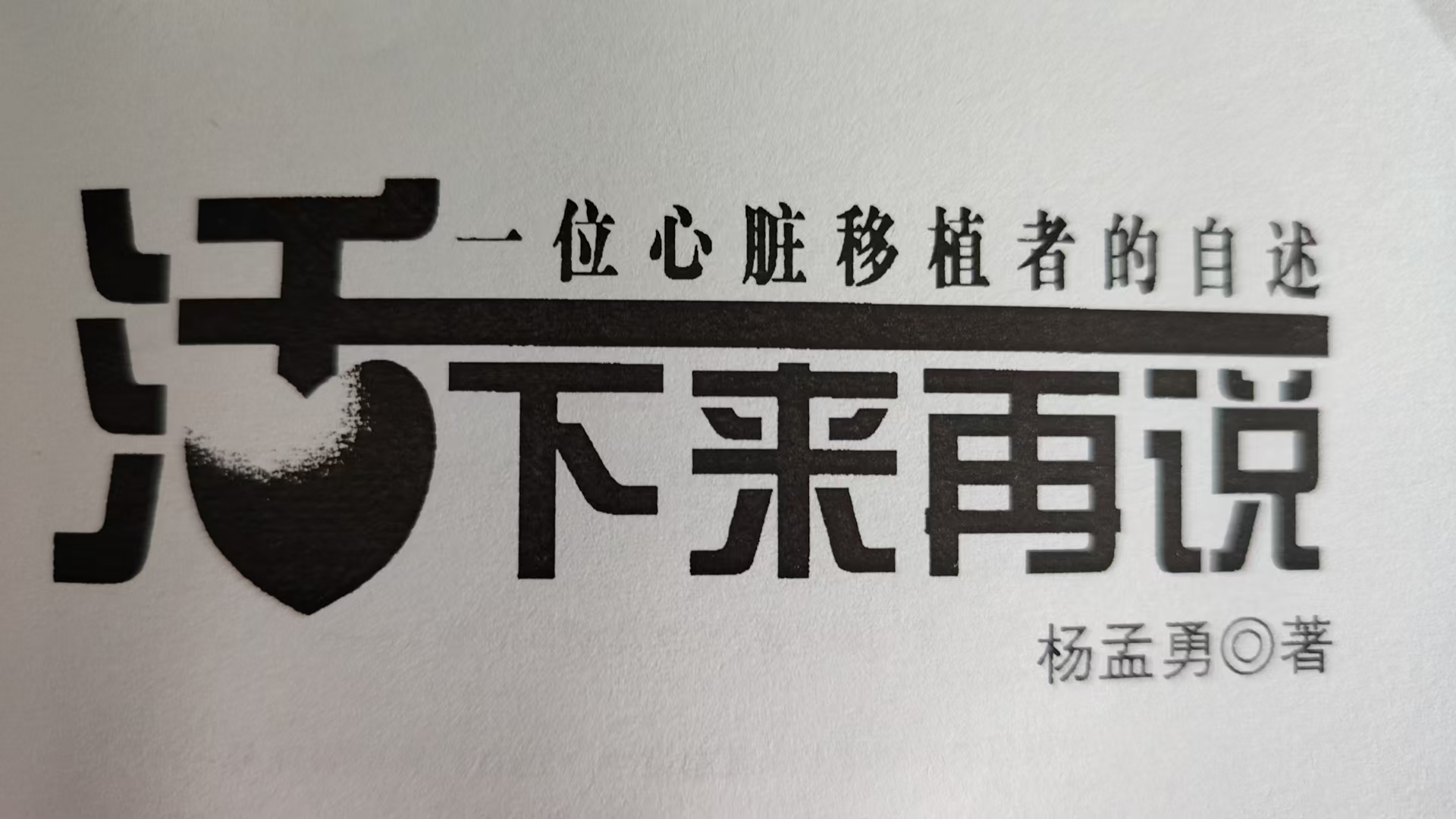
50、换心之后我变得年轻了吗
大勇是四叔家最小的男孩。那天夜里突然来了电话,告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我四叔病危!
这消息让我焦急不安。三叔于1995年病逝,四叔是我们家族里男性长辈中最后一个了。
大勇在电话里说:“大哥,本来不想告诉你,一想,不告诉你也不对。告诉你了,也不打算让你来,你做了大手术不久,身体需要恢复,再说,来一趟不容易,一千多里路呢。我们兄妹的意见,你就不要来啦。”
放下电话,我立即告诉妻说:“我四叔病危,正在医院里抢救。”
妻问我,怎么办?
我想去。我说我父亲死后,家里的地都是四叔种的,那几年真把四叔累得半死不活的。
"你一个人去可不行。”妻说,“我陪你一起去。我还记得,咱们结婚时四叔给的30尺布票呢,还打了白铁洗衣盆和豆油壶什么的,从老远的地方捎了来。我心里一直惦念咱四叔。"
7月上旬的天气,还不算酷热,火车在夜里行驶。
躺在卧铺上,妻坐在我身旁,车窗关上了,仍可听到夜行列车的隆隆声隐隐而来。
女列车员从车厢一头走来,为每一个旅客发放卧铺牌号。发到我这里时,女列车员好奇地看看妻子又看看我,对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十分有把握地说:“如果我没猜错,你们是娘儿俩吧?怎么能儿子睡卧铺,让你母亲坐着呢?”很显然,她有些抱打不平的味道。
妻却平静地说:“你这是啥眼神儿呢,怎么能把我们看成是娘儿俩。”
女列车员一脸的疑惑:“他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丈夫--”妻笑了,笑列车员的眼神不济。
“你可别生气啊!”女列车员解释,“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最爱观察人,也观察得相当准,说句实话,怎么看你们都像娘儿俩。”
“是吗?”妻附和着。
我真的担心,此时妻的自尊心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说不准会被激怒。我担心因为这件事她会与女列车员吵骂起来,惹得一身的气极败坏。而此时,妻却出奇的平静。
我以为这时列车员会知趣地走开。
但她没有,依旧坐在靠窗的坐椅上饶有兴致地说:“你可别生我的气啊,你们不像夫妻。”
妻问她:“你是不是看我的头发全白啦?"
“不是一一"女列车员说,“你头发不白也不像两口子,你看他的眼神儿多活呀,咋看咋不像60岁,就像娘儿俩。”
妻不做声。
我不能说什么。
此时不宜向女列车员有任何透露。她不会知道我一身二命,不知道在我胸腔里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正在有力地跳动。我那蓬勃的精神,旺盛的活力,都是我体内另一个生命力量所驱驶。
我身上的一切改变,都朝着年轻的方向迅速发展。
前些日子,我去医大二院开了三个月的免疫药品,院长签字,返回去划价,在窗口取了药装进兜子里,就像出门的媳妇回娘家一样,顺路来到监护中心。
只要到医院,每次都要回到监护室看孙晨光主任,看看陆护士长和护士们,仔细抚摸我曾躺过的病床。那一次我见到了当时看护过我的每一个护士,惟独不见杨波。
陆护士长说:“杨波休产假了,过些日子就能见到她啦——”
几个月后,去医院复查,测了血压,抽取了血样之后,我又一次走进监护室的走廊,迎面看见陆护士长,打了招呼,她用手一指说:“杨波来啦。"回头看去,只见她一身洁白的装束,天使般从走廊那头款款而来。
做了母亲的她,比那时的身材更加丰腴。
我喊了她一声:“杨波--"
她走了几步,在我面前站住了。疑惑地打量了我一下。“你是谁?"她问我。
“我是你看护了半个月的病人啊!杨波,你忘了吗?”
“你是哪一个病人?"她又问。
我知道自己的变化已经使她难以辨认了。那15个日日夜夜,她护理的是个年近60的老人,今天站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毛头小伙。两个不同时期的我,使杨波无法把他们联系起来。
她实在认不得我啦。
我有些着急地再次声明;“我是换了心的人哪--"
杨波皱起眉在回想,嘴里自语着:"换心?”
看起来,我必须说出我的名字啦。
“杨波-我是老杨,是杨孟勇啊!”
她依然疑惑:"你怎么是老杨?"
我大声说:“我就是,你真是不认得我了吗?”
"天哪-”杨波如梦方醒,“你变化得太大了,太吓人啦!”
我笑了起来,问她怎么变了。“简直成了两个人,你变得太年轻啦,变得让我不敢相信的那种年轻。走走走到监护室去,看看小温和小惠她们。”杨波拉着我进了护士值班室。
列车隆隆向前行驶。车厢里的灯光关闭了。
妻拉开毯子盖在我身上,仔细地在肩头掖了掖。
51、换心之后我变成球迷了吗
真的像母亲为我解梦时所说,我赶上了好运,在闽江小区住下来不到两年,我所供职的《北大荒文学》编辑部跟随农垦局,从边城佳木斯搬迁到了哈尔滨。虽然我提前办了退休手续,总还是有了几分依托感,心里踏实了许多,减轻了客居外地必然要产生的落寞与孤独。退了休的人,怕就怕这个。
我曾担心过,还打算在适当时机考虑一下回到佳木斯,这一次后顾之忧全部解除。农垦局的韩乃寅书记念及我的处境,将志勋安排在哈尔滨农垦电视台上班,这样,家里除了海光,又回来了志勋,一家人其乐融融。
志勋从佳木斯来时,把闲在家中的电视机带了来。东芝的牌子,虽不是原装,看起来依然蛮不错,尤其是荧光屏的色彩。
志勋这个年龄段的人,是看着足球长大的一代。先是国外球员的精彩射门集锦,然后是国内职业联赛,甲A甲B看了个够。足球之夜更是他每次不肯放过的看点。几年下来,家中第一个球迷产生了,我也成了继他之后的替补。当然,志勋是把我领进足球赛场的第一人。每每遇有重大赛事的现场直播,便成了我们父子俩的精神大餐。回顾起来,棒得很哩。
但现今的我,不比往昔,我是带着别人的心脏来观看这一场场赛事的。
志勋不免为我担心,小声劝我:“爸呀-你出院不久,不能太激动,激动起来对你的心脏不好---”
我深知孩子的好意,却反驳他说:“有什么不好?我原先不愿看足球,连越位和手球都不懂,还不是你边看边讲。什么皇家马德里、AC米兰、勒沃库森,什么罗纳尔多、马拉多纳、天才少年,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现在又不让我看。”
见我这样,志勋只好默不作声。
其实,在体育运动上,我并没有多少专长,能够参与的,也只有乒乓球一项。虽然从小就喜欢,因为缺少必要的天赋和身体素质等原因,一直是个初学者水平,而且极不规范。在农场读小学时,每到星期天,隔壁的志民就领我去木材厂学乒乓球。球案上没有网,用了一块长木板代替,球拍也是木板刻了个大概形状,谈不上什么正胶反胶,名副其实的光板子。
患了心脏病的这些年,几乎不摸一下球拍,兴趣的转变,使我只看足球。
世界杯外围赛开始后,电视机壳上贴了一张亚洲小组赛时间表。
我知道那是志勋从报纸上剪下来贴上的,在中国对卡塔尔那场比赛时间下用笔划出一条醒目的红线。他在关注那场赛事,我更关注。
终于到了那一天。
中国足球队在米卢的带领下,远赴卡塔尔客场作战。场地是卡塔尔惟一的足球场,在实况转播中,可以看到看台上寥寥无几的观众,到处都显示出卡塔尔并不看重这场比赛。
但我看重,心里早已紧张起来。
听志勋说,有一届世界杯小组赛上,中国队就败给小小的卡塔尔,小组都没能出线。应了冤家路窄那句话,这一次又在小组赛短兵相遇。而且形势即明朗又险峻。体育频道的主持人在开赛前也对这种势态作了更为深人的分析。
这是决定中国队命运的一场赛事。只要踢平,小组出线稳保。输球,冲不出亚洲,进军世界杯将又一次化为泡影。
比赛开始时,志勋又劝了我一次,他小声说:“爸--你睡吧,别看了,全场结束得下半夜两点,受得了吗?”
我一心想看这场关键性比赛,便不耐烦地说:“看你的吧,别管我。”
上半场在失利中结束了,卡塔尔1:0领先。
局势一下子险要起来。
下半场两国的队员拼了,卡塔尔要死保已经占领了的阵地,中国队必须攻下来。赛场上浓烟滚滚,气氛紧张。中国队竭尽全力,组织了多次进攻,仍不能破门。
志勋很着急。他着急时只是把眉头皱几下,再不就是从绷紧的嘴唇中冲出一句话,真臭!
我坐立不安,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长吁短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眼看无望。志勋渐渐失去信心,身心疲惫使得他倚在靠背椅上睡了过去。
我看到他把头歪向一边,两眼合闭,已经发出微微的鼾声。
我依然瞪大眼睛,吸用了毒品一样,精神百倍,不眨一眼地往下看。
我坐直了身子,把两手放在膝盖上,耳朵里满是裁判的哨声、运动员的呼叫声和解说员焦急的语言。
下半场就要结束!
我的双眼一直没离荧光屏。
还有三分钟就是全场结束的时刻,这是决定中国队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
满以为这次又无望,又上演了一幕兵败卡塔尔的旧戏。没想到机会竟然在即将结束时来临,李伟峰接过队友的一个妙传,猛地抬脚起射,正中卡塔尔大门。哇-
这一粒人球,子弹一样飞出,它带来的啸叫和热度,好像照直冲向我心窝,点燃了胸中满腔激情,我尖叫一声,从椅子上蹦起来,跺着脚喊:“进啦!进啦!”
睡熟的志勋被我的喊声和跺脚声惊醒。
他刚一睁开眼,我就向他喊:“快看!李伟峰进啦!”
志勋听到窗外响起同样的尖叫声。
我看了一下表,李伟峰进球,是下半夜1时47分。
窗外响起了鞭炮声。哈尔滨的球迷在庆祝小组出线。
志勋拖着疲惫的身子睡觉去了。我依然兴致勃勃。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觉不对。年龄上的不对。一个年近60,一个才26岁,看了近一夜的足球,困乏疲倦的,是谁才合情合理,该是不言而喻的。而昨夜的事实恰好相反,我捉摸不透,我何以能比得上一个朝气蓬勃精力旺盛的年轻人?而且是先于我成为球迷的儿子。
莫非我心脏的供体,也是个球迷?
52、换心之后为何爱吃小食品
对于吃,我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只顾利用,很少研究的。
北大荒有一种值得一提的美味,那就是马铃薯。黑黑的腐植土使秋天的马铃薯能长到半斤一个,个头大的可达一斤往上。新疆人家家有地窖,窖的是哈密瓜,北大荒也家家有地窖,窖的是马铃薯,两者都为的是在长达半年的冬天里慢慢受用。
我品尝马铃薯的方法是利用炉灰来烤。冬季里猫冬,实在无事可做,听到火炉中火在燃烧时发出火车奔跑般的轰响,就去找来几个马铃薯放在炉子落灰膛的最里面,等待带火星的红红的炉灰掉下来,一层层覆盖了马铃薯。必要时,用炉钩捅几下火炉,便有更多的红火炭纷纷落下来烘烤马铃薯。这样的吃法不能心急,要慢慢等,像傍晚俄罗斯人野外弄火烤马铃薯那样耐心地等待。估计 40多分钟以后,就可以扒出来,去了灰和烤焦的外皮,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喝!那才是真正的美味,真正的绿色食品呢!吃得兴起,会什么也不顾,弄得一嘴一脸的黑灰,手指更不必提。
三年灾害期间,我已走上独自谋生之路,住进厂子里的独身宿舍。那时的每个人都难逃饥饿的威胁,整天都在思考去哪里弄些食物充饥。有一天一个相处甚好的工友悄声跟我说,他发现了目标。于是我俩不露声色地带上口袋和撬棍偷偷摸到了很远的一栋猪舍旁边,靠近猪食槽的一个木箱里,是一箱冻成一团的马铃薯。看看周围没有看管的人,我们俩便放心地举棍子敲打。冻成坨的马铃薯被木棍打散开之后装进袋里,带回去在宿舍的炉火上炖了一大盆。没想到的是冻了的马铃薯煮熟了以后从里到外都变了质,像被墨染了一样的黑,还有一种冻了的怪味儿,但那时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了。
直到现在,炒土豆片,炝土豆丝,以及红烧土豆块,土豆条疙瘩汤等,仍是我不能舍弃的。近些年又出了风味土豆片,嗲得薯片,和麦当劳快餐中的炸薯条,当然还有土豆沙拉。
在我的饮食中,马铃薯是永远的,不会有什么比它显示出更为优越的品味来了。
让我自己也深感不解的是,换心之后的我,对马铃薯的味觉记忆正在一天天退化,取代的是另一类食品。尤其是那种鸡味圈。鸡味圈本是小食品之类,属于孩子们的零食,电视广告无一例外的由儿童来做。各个吃性十足,广告语大多离不了,哇!味道好极啦!一副小小美食家的样子。
与儿童小食品有瓜葛,这要怪罪于女儿云松。那一次云松来哈尔滨看我,随手给我带来一大包小食品,说是让我在家闲坐时吃一口,蛮香蛮脆的。没料到几包小食品吃下来,竟一发不可收。说起来确实有几分难为情,难就难在这种一发不可收出现的实在不是地方。
妻的态度分明:反对。
妻多年推上小车,到学校门口卖的正是这些。无论手里剩下多少,积压多少,都不吃一口的。那时的我也不曾如此迷恋,偶尔尝一尝,品味一下而已。小食品毕竟是孩子们的,无论如何,也不该我一个60岁的人感兴趣。
就在几个月之后,事情有变,势头的发展与变化呈现出戏剧性。每次妻与我走进超市,我必定要浏览一下小食品货架,出现在我眼前的可谓琳琅满目:咖啡粟米条、卡迪娜豌豆脆、咔洽脆、葱味香原味妙脆角、亲亲哈陆、日式鱿鱼味、太阳锅巴、北方锅巴、旺旺仙贝等等,应有尽有。我的首选往往是鸡味圈儿,带蔬菜的那种,中等包装,净含量48克,其中8克标明是赠送的。只要你一打开包装,那鲜美的鸡香味儿即刻冲进鼻子里,让你沉浸在不尽的幻想与回味中。
这时的妻已经选好了日用品,过来催我走。此时的我,已馋得不能自制,根本不想放下手中的鸡味圈儿。
妻说:“别吃那个,里面有添加剂。” 我仍不肯走。
妻又说:“不但有添加剂,报纸上说,有的小食品里还有激素,一个小女孩才9岁,就来了月经,多坑人。”
妻的这番话对我不起作用。无奈,她只好把鸡味圈装进方便袋里去交款。
走回家的路上,妻忽然想起了什么,回头问我:“你兜里的那些零钱是不是都买了小食品啦?”
我回答:“是。所有的牌子我都吃了个遍。”
妻大笑起来,笑得弯下了腰。她说:“你快成了咱家的小雯雯了。”小雯雯是我们的外孙女。
妻的这句话让我吃惊不小。
吃起小食品来,我几乎达到了品尝员的水平了(听说酒类评比有品酒员的),我常对照包装袋上标明的配料表,一颗颗细细咀嚼。像品酒师那样,端起杯,只抿一点点。而且不能太急,吃下一颗,再顷,又一颗。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享用其中的美味儿,品出该产品是否偷工减料,或者是黑加工点的假冒。那些产品到了我的嘴里,即刻露馅儿。
贪恋一口之食的人,要被划人没有出息一类的。看来,我是无可救药了。几天过去,若是不吃上一袋,如同吸毒者犯了瘾。食品面前,我已完全丧失了自制能力,完全倒向了鸡味圈的美味一边。
我曾试着分析过自己,打算向戒毒那样从此金盆洗手。可是不成,只要口袋里有了零钱,双脚就会自动地走向小区里的任何一家超市。怕妻发现,买一包,当场打开,吃完了之后若无其事地走出去。
为此,我常窃笑自己这一行为。
一个60岁的人,怎么在儿童小食品面前,竟失掉了应有的男人气了呢?
所幸妻不是那种饶舌之人,否则会有许多人知道我这一奢好。这个奢好会不会伴随我一生?
不用妻提醒,我也知道这是手术后的改变之一,究竟属于我的自身,还是来自供体,有待于慢慢观察。我很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多费些心思。
53、换了心脏就换了另一种脾气吗
谈不上心境,只是心情而已。而且是不怎么好的心情。心境实属于奥秘,且又难遇。在一个美丽的城市里,在租来的房子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细细观察着自己,品味着自己,看这个又长了一岁的换了心脏的人,于时光,于生活,是一个怎样的姿态,倒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一日三餐,家里屋外,自然是妻一手操办,看她风风雨雨,里外奔波,尤其那头白发,只要映入我的眼帘,心中顿时便会生出一些悲悯与内疚来。都是因了一个不省心的我呀。
妻是持家的里手,这是无疑了。我出院调养,远离原先的家,于人地两生的地方,立起一个临时生活场所,且又能让我无忧,实在不是件容易事。据说这女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建立起一个家的,或者说她自身就是家的象征。研究者发现,只有几岁的小女孩,就喜欢把布娃娃抱在怀里,预习一下怎样当好一个小主妇。眼前那些玩具,会被她看做是一件件美好的家具,不是吗?她自小生活在自己建立的家中。
女人给男人一个家。而男人有时浑然不知,如我,在不知何故坏了心情的时候,往往会干出些莽撞的事来。令自己后悔不迭。
妻拉上我一起看音乐喷泉,一起在花园里徜徉,或坐在大理石花圃的边沿,听晚风中京剧票友们的精彩选段。
尽管这样,我发觉自己很难获得一份心境,很难再有我们从前过的那种日子,到了休息日,她在家先忙洗衣,后忙炊事,把个休息日弄得红红火火。而我带上小时的志勋,来到水边,投下钓钩,静静地等待一番收获。现今被取代的是一股急躁。那无名的急躁常常会摧毁我的心情。
尽管妻反复说过,你什么也不要管,安心调养身子,尽管如此,我依然做不到全天候的保持好的心情。有时劣等的电视广告也会引发我一阵阵恼怒。
这时妻就好言相劝:“不愿看就不看,咱们去太阳岛转一转吧。”
这样好的提议,平时早就得到呼应了。现在却不然。我冷冷地板起脸,不去理睬她。妻如果在这时说上一句不怎么顺耳的话,我就会暴跳起来。
有时我想,是供体心脏在以强大的力量影响我吗?从前我曾有过年轻人通常有过的不成熟,但从未像现在。那个年轻人结过婚有过妻子吗?他是否每天向他心爱的妻子发起雷霆万钧的暴怒呢?是他把这火暴的脾气给了我,还是我曾经这样?
从前我没感到自己总是处于怒火的燃烧之中。
妻每天为我劳碌操心,我在她的服伺下每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却不满意,依然忍不下一丁点儿小事。
不知是否受了坏心情的影响,我那双眼睛也变得爱管闲事儿。
我看暖气片上一溜儿摆放着三瓶纯净水,暖气散发的热度使冰凉的纯净水渐渐加温。
我不知道妻为什么要这样做,以为她买给孩子们喝,她自己舍不得喝一口的。
可是没有人喝。
过了两天,三瓶纯净水依然在暖气片上。
我在猜测它的用途,却怎么也想不出。
我走过去,拿起一瓶,对着窗户,让冬天的阳光射透那个透明塑料包装,发现里面的水质不像几天前那样清彻,瓶子里的水已经微微发黄。
“水变质啦!”我向妻提示,“再烤几天,娃哈哈纯净水就要变成臭水!”
原来我有所不知,瓶子里并不是什么娃哈哈纯净水,妻为了洗衣服时不冰手,只是用了娃哈哈的空瓶子,重新装满,放在暖气上加温而已。妻正在一旁做什么,似乎应了一声,表示听到了。
我看她手中有活儿,就把几瓶水拿到窗台上。
第二天一早,那几瓶水又摆到暖气片上,我睁开眼问妻子:“那几瓶纯净水干什么用?”
“洗内衣用的,怎么了-”她的神态里有些不愿意回答的味道。
“怎么用纯净水洗?"我埋怨起来。
妻见我不高兴,小声说了句什么,却又没把事情说清。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时的我抓起一只瓶子摔在地上,吼了她一句"再烤一天,水里全是细菌!全是病毒!干净个屁!”
妻不情愿地拿走了剩下的两瓶。
我难以控制心中的火气,继续在屋里喊:“昨天就告诉你水变黄啦,你为什么不听?”非要烤到变臭吗?”
我大声吼叫的时候,妻已经悄悄下楼,屋里只有我自己。
吼叫过之后,是一阵极度疲乏,身上的力气都被叫喊声带走了,像一个喷射之后的礼花,只剩下仍在冒烟的外壳。
平时积在胸中的巨大压力也随之消失。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一次间歇,用不多久,激荡的浪潮就会扑过来,依然还会被某个细小情节所引发,导致又一次的爆发。
我害怕这种爆发,总想驾驭它。但它像一匹野马难以驯服。
有时我会在它来临之前,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不要生气,不要让那种爆发到来。那样,只能会伤害自己,伤害刚刚移植不久的心脏。
那颗心脏并不是我的。那颗心脏是那个年轻人的。
我一个60多岁的人,不该也不会有如此的爆发。到了这把年纪,如圣贤所云,早已知了天命,早就懂得了顺其自然的大道理,人老了,脾气本应变得绵软、柔和才对呀,怎么就因为这点小事而光火起来?
那个火气冲天的人是谁?
我无力地躺下来,伸出一只手为自己把脉,那颗心脏在剧烈地跳动,每分钟在 110次以上。我已经感到心慌,全身无力是心动过速引起的。我爬起来,吞下一片卡托普利,它是强药物。
又有一次,妻把水盆端在我面前,让我洗脚,转身去拿暖水瓶。盆里是温水,我把脚伸进去,感到清凉和舒爽,我说就别倒开水啦。
妻打开暖水瓶,她坚持说:“还是掺一些吧,全是凉水,怕你受不了。”
见妻要掺些开水,我抽出一只脚,让她在盆边倒暖水瓶里的水。倒了一点儿,我的脚已经感到了热,急忙制止说:“好了好了。”
妻嫌不够热,歪着暖水瓶继续倒。
我忍耐不住,忽然提高了声音说:“水都热啦,你怎么还倒?”
妻放下暖水瓶说:“这不是为你好吗?"
“水都烫脚啦,你还倒开水,这是为我好吗?"
妻见我火了,转身走出去。
她听到砰的一声响,立即返回屋里,看见地上一片水,空盆扣在地上。
妻望着我。
海光不知发生了什么,慌忙跑进来,看了一眼,全都明白了,什么话也没说,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事隔很久,海光和他的母亲共同回忆了那一幕场景。海光在回忆中,当着他母亲的面留下了痛苦的泪水。孩子不理解为什么我会变得一下子失去了理智。
我时常在内心告诫自己,遇事一定要心平气和,一定要压住火气。但我发现,这只是徒劳,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便会有场爆发。
夜深了。
我在写作。几天前妻与我去家具商店买回一张小学生用的学习桌,它比不上写字台,更不能与老板的办公桌相提并论。它窄小,却平整,一头有三个小抽屉,中间有两扇凹进去的门,留出的空当可供我放下两只脚。这张学习桌是我居在哈尔滨添置的第一件家具,它的价钱是我所能接受的,送回家120元。有了学习桌,免去了站立在窗台上写字之苦,直到夜半,我仍坐在桌前写下那段躺在手术台上的经历。海光睡在隔壁的屋子里,他半夜起来,发现一缕灯光从门缝透射出来,推开门,看到我正在写作,担心熬夜会对我正在恢复的身体不利,站在门口劝了我一句:“爸呀,都12点啦,你在写什么呢?--你刚出院,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呀。”
我抬头看见只穿一件裤头的海光,突然火了,向他吼了一声:“你睡你的觉!管我干什么!”
海光被我突发的怒火吓呆了,他疑惑地望望我,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屋里。我仍在无名的怒火中。
真的是太不应该了。难道我疯了不成?海光一直是我心中的骄傲,是我生命的另一个自己,我怎么可以这样?发火的那瞬间,真的就是我吗?如不是我所为,是谁在我心中引发了这把怒火?
妻被我的吼声惊醒,从床上坐起来,小声跟我说:“孩子好心好意,你怎么发火了呢?你应该好好告诉孩子。"
我看了妻一眼。
我说:“我想起了一些事情,必须马上写下来,明早就忘了。你先睡吧,我写下来立即就睡。"其实我也想好好说,但我无法做到妻所说的那样。
第二天,妻陪我在水上花园散步,替我分析昨天半夜那场冲突。
她试探着说:“是不是孩子小时候,你对他们太溺爱了,爱到了头,就产生了一种怨恨?”
我说不清。
我深深自责,父子情深啊。虽说父亲与儿子似乎很容易产生不快,理论起来,这一次自然是我这个做父亲的理亏,私下里我问自己:“还会发生第二次吗?但愿这是仅有的一次,下不为例。哦--该死的!”
那坏心情的来临,飘忽不定,又难以捉摸。有时原本好好的,一个事情出现,轻而易举地就翻了船。记得去北京,住在玉祥兄家时,快要返回东北的时候,想起要买一盆好一点的花留下来,作个纪念。我们走了,总会有一盆鲜花开放在他们心中。妻与我沿街散步,看到一家花店门口摆了几盆茶花。引得我和妻进了花店。
茶花是名贵的,北方不产。茶花小型张曾是中国集邮市场的珍品,真实的茶花同样娇美动人。我和妻一边走一走说。虽然爱花的男人曾经被时代蔑视过,我还是动心了。
花店的主人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见我在几盆茶花下驻足,主动打了招呼。我有心想买,但没定下来。
第二天,我和妻又去了一次。
花店主人说:“昨天你看好的那两盆,我一直给你留着,一盆40元,一盆25元,你挑哪盆都行。"
我想买 25元的那盆,妻说:“要论枝叶的形态,还是40元的那盆好,那盆全是花骨朵,能开一两个月呢。"
本来我想买25元的那盆,妻这么说,我犹豫了,最后听从了妻的选择,以37元的价格买了另外一盆。
第二天一早,妻就发现了问题。
妻的发现使她有些不安,花盆的泥土怎么都是新的?用手摇一下山茶的枝干,竟然是活动的。再一看,盆土的表面没有一棵草。
妻忙把我喊过去,把她的发现说了一遍。
我看了看,想起几年前听人说起过,现在卖的山茶花,都是南方的野生品种,从山坡上挖下来运到北方,这种花很难成活。
又过了一天,妻发现有几个叶片由墨绿变为黄褐。
她说:“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说:“咱们今天去花店商量一下,用这盆37元的,换那盆25元的。”
妻说:“试试看。”
进了花店,妻跟店主商量:“我大前天在你这买了一盆37元的山茶,想拿回来,换你这盆25 元的。”
店主一口回绝:“不行。卖出的花一概不退换。”
妻说:“你就给换一盆吧。”
店主提高了嗓门说:“鲜花鲜花,出门就不换。"
来时我们俩商量好的,为了避免我跟店主接触,容易出现差错磨擦出火气来,由她出面交涉。妻反复交待,她若不换就算,回去好好侍弄,我是土命,养什么花都活。
很显然,妻已觉察到一场难以避免的冲撞。
听店主人这么说,我猛地转过了身子,一声怒吼从嗓子里冲出:“凭什么不给换,上海的大商场卖出的货都给退换!凭什么?”
花店主人立即应战,阴沉着脸高声说:“就是不给你换!”
我冲上前,几乎把手伸到了她的鼻子底下:“你想不想开店啦?”
花店主人立即明白了我的话意,她高喊着:“怎么着?想砸店?我等着你呢?”
果然,一股热流冲上了头顶,来不及设想动手会发生什么,以及发生的后果。妻似乎有了预感和准备,一下抱住了我,用了很大力气才把我推走。
在回去的路上,妻向我不住地道歉:“孟勇,你别生气,都怪我,要是买了那盆25 元的,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跟店主叫喊时,我觉得心脏的跳动在急剧地加快,现在经妻的消气,有些平稳了。
我一边走一边自语:“我怎么变成这样啦?那天见到花店的女主人,感觉挺好的,像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妈妈,今天怎么只说了两句,就跟她吵起来了。”
“吵架时的你,怕不是原来的你啦。”妻说。
也许是这样。




玫瑰手绘折扇、玫瑰国画
订购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