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杨延斌推荐语:25年前,我亦师亦友的北大荒作家杨孟勇,创造了57岁做心脏移植的世界奇迹,并接续创造了心脏移植不久后停止服药、健康地存活了25年的人间神话。杨孟勇用一颗不正常的心脏,把生命的不可能活成了可能!他的神奇故事,曾经由中央电视台等几十家电视台制作专题广为传播。长篇纪实散文《活下来再说》,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推荐连载此书,意在引起读者对生命的尊重和感动,同时感受这个社会的优越和温暖。尤其要向给予杨孟勇二次生命的哈医大二院、及其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著/杨孟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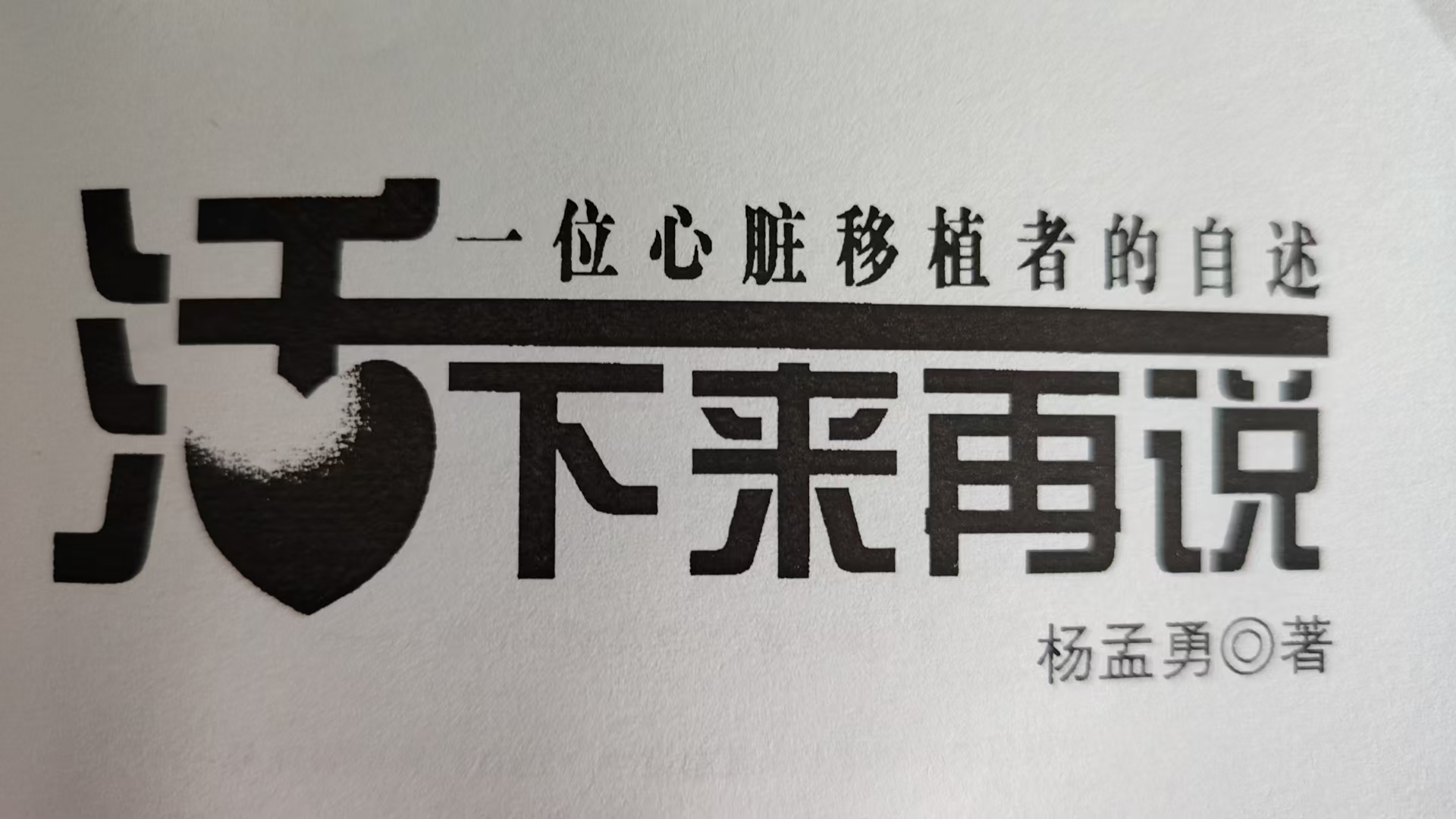
58、想念心脏
那天早晨5点钟,在手术室,她从我胸腔中被切割下来,医生们是如何处置她的?我曾经列出如下几种可能:随手甩掉,那是最令人惋惜的;做了病理切片,以便看个究竟,这也是不怎么如意的结局;因为还有保存价值,经过处理,浸泡在透明的福尔马林溶液中。恐怕还有第四种下场。但无论如何,对于我原来那颗心脏的下落,至今一无所知。
她毕竟是我以前57岁的生命中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如今,她身安何处?她的踪影在哪里?这种疑问几乎成了我每天必须认真思考的内容。有些日子,甚至为她的去向和下落寝食难安,坐卧不宁,以至达到牵肠挂肚的地步。
不可能不这样思念她。
后移植在我胸腔中的那颗心不可能不这样思念她。
据说婴儿在母腹中还没完全成形时,心脏就已经发育完整,并能一收一缩地跳动,传达出微微的心音,在有节奏的搏动中,向胎体源源不断地输送血液,胎儿才渐渐成长,一个小小的生命才算真正开始。看来,我那颗跳动了57年的心脏,我那颗被切掉的心脏,是先于我而存在的。她的发育与形成,是为了后来名叫杨孟勇的这个生命而存在的。按一般规律,移植手术没有诞生之前,我们不可能分离,要么同生,要么同死。如所有的人一样,一起来到这个人间、经历过风风雨雨,在岁月中慢慢地衰老,再一起消亡,像一对形影不离的恩爱鸟,白头偕老,直到最后时刻的来临。在57岁这一年,我们却被迫身心两处,天各一方,相互不知道音讯,从此不再共同拥有一个命运了。
在她被切割下来之后,我曾为这种结局产生过深深的内疚与不安,常常一个人独坐静处或者躲在一旁仔细回想。我深深地懂得,一切都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一意孤行的结果。每次我带上病体去看医生,诊查之后,医生们都会皱起眉头,一脸严肃却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可要注意保护心脏啊。”有的医生会在我离去之后,拿起电话告知我的家人和单位领导,说我的心脏已病人膏肓,一定不要让我单独出门,也不要让我过于疲劳。但在我这里,医生们的警告和家人的劝阻,如微风过耳,实在没有当回事。到了打猎的日子,照样背上枪就走,从清晨两点到天黑,整天都在雪原上追逐猎物;到了钓鱼季节,整夜蹲在河边,风餐露宿。这样饱受风寒的生活,明知对心脏不利,却乐此不疲。每次钓鱼回来,脸也不洗,衣服也不换,吃几口饭就开始记录当天钓鱼所发生的事情。那个厚笔记本记满了,又买了一个。我把它命名为《钓鱼笔记》。这大概受了《猎人日记》的影响吧。后来又找来一个本子,记载每次打猎的经过,只记了一次就从此中断。那时我的心脏已不允许,每打一次猎,都累得像个死人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全身酸软,不想再动一下。狩猎笔记就这样有始无终,成为一件憾事。
记得有一次住进医院,医生就在我的心脏上听出了房颤。其实房颤已是心衰的前奏了,我却依旧我行我素不理不睬。
真的难以想象,我那颗心脏付出了何等代价陪我走过57年的历程。严重时,心肌扩张、冠心病、房颤、早搏等六七种疾患集于她一身。而她,充其量只有拳头大小。我那颗心脏,实在是可以敬佩的,头脑累了,可以在睡眠中得以休息;眼睛乏了,可以闭自静养;筋骨疲劳了,伸展四肢躺上一会儿就可以缓解。各种器官都在夜晚休息,连肺都放慢了呼吸,而我那颗心脏仍在一收一缩地顶动,把血液和营养灌注至每一条毛细血管。她就这样患上了疾病。在20年的病史中,逐年加重,最终她衰弱得像个风烛残年的老者,咳嗽着,喘息着,背负我沉重的身子,一步一步,吃力地爬行在生命坡道上。有时,我在上肢动脉上找到她,并用手指去触摸她的跳动,发现她几乎要气尽力绝,几乎奄奄一息了。我曾为此担心,她能就此扔下我不管吗?没有。她始终没将我遗弃,而是我在无奈中作出将她切除的决定。
躺在手术台上那一刻,一种悔意与悲哀油然而生,那颗心脏将与我永远地分离了,这是我的不忍。就是切除了,也要与她见一面。
记得出院前,姚主任到病房看我,我曾小心地问过他:“我那颗心脏还在吗?如果还在,我想看看她。”
姚主任答应与病理科联系一下,但始终没有如愿。后来几次碰上匆匆而过的姚主任,都没有机会开口重提。凭直觉,我那颗57岁的心脏还在,在一个大广口瓶里,瓶子上或许贴有标签,上面不是我的名字,而是一串标本的编号。
现在我活了下来,而她却死在一个标本的容器里。
呜呼。
59、回忆10号病房
病重的时候,带着求生的急切,匆匆住进病房,那时生死未卜,加上心脏病频频发作,没有心思对周围的环境作十分细致的观察。手术成功,活了下来,却能在闲暇时清晰地回忆起10号病房的每一位病友的音容笑貌和他们的一举一动,令我自己也颇感惊奇。
10号病房住了4个人,清一色等待心脏手术的病人。
1号床星文,40岁,室间隔缺损,已经影响了正常生活。他的病只要开刀,在缺损处缝上两针即可。缺损大的,作一下修补。
在这样的医院里,做这样简单的手术,比普通医院做阑尾炎切除还常见。
即使这样简单的手术,星文也害怕。
他比我早一天住院。陪同他的妻子说,星文这是第二次住院了。第一次只住了几天,没结账就偷偷跑回了家。他害怕上手术台。第二次住院依旧疑虑重重。
我能理解他的恐惧。
他怕万一发生不测,在手术中丢掉生命。
只有生命才是宝贵的。
二号床是个来自林区的10岁男孩儿。做教师的父亲搂着男孩儿,两人挤在一张床上。早晨穿衣服时,我看见男孩儿扁平的胸部被一道道白纱布缠绕,那是刚刚做过心脏手术的证明。
紧挨我的4床,是个不到50的胖汉。他躺在床上向我述说了他的怪病。感到不适才几年,发作时却凶猛得很。每发作一次就要昏死一次。他带上怪病走了好几家大医院,最终毫无结果。有的医院甚至说他心脏很正常,根本没有病。他的自我感觉,病根儿就在心脏上,发作起来心前区像压了块厚厚的冰。
胖汉姓袁,胖袁来到医院的当天便到门诊心动彩超室作了检查。诊断结果是右心室里长了个东西。他的病在这个医院属于史无前例的怪病。可以参照的病例一个也没有,每年要做1000多例心脏手术的医院,第一次与这种病相遇。资料透露,右心室异物多半是恶性,言下之意可能是癌。心脏长癌的这个隐情只有他家里人知道,胖袁本人毫无所知,依然与同室的病友谈笑风生。胖袁以为,凭这家医院的名气和医疗水平,只要诊出了病,就能治好的。
医院却迟迟不下手术预定书。医生反复论证,看人命比天还大。胖袁兄弟姊妹10个,一齐上阵向医生求情。家人一来就能把走廊塞满。在家人的一再请求下,手术的日子终于定了下来。
我到的第二天,胖袁进了手术室。
2床的男孩出院了。2床走后,护士把我调到空位上去。
这次我可以挨近1床的星文。星文是个健谈的人,向我诉说了一生的身世,说了他4岁死了母亲的凄惨。他说最疼他的一个姐姐比他大一岁,她对他就像母亲一样。
我想起有天早晨7点多钟,一个身穿大衣头戴厚毛线围巾,把整个头部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推门进来的情景。“是昨天送饭的人吗?”我问他。
“是一-"他点点头,"你没看见她进门时眼圈都是红的?姐姐一定在路上为我哭过,进屋之前才擦了擦。”
听说我要换心脏,星文先替我担忧起来。他见我大口地吃着左弘带来的纸皮核桃,大口地喝下左弘买的柠檬汁,就问我:“看你能吃能喝的样子,难道心里不害怕?"我冲他笑了笑继续吃核桃,继续品尝柠檬汁。过了一会儿,星文又说:“杨大哥,你不怕,我怕。”
换到2床的当天夜里,被一阵阵嘀嘀嘀的声音惊醒。睡在我身边的妻子也坐了起来。我看见星文推了推身旁还没醒来的妻子说:“快--传呼,我的传呼响了!”
星文妻子急忙去拉床头柜上的抽屉,拿出传呼机时,嘀嘀的叫声已经停止。
她按了一下传呼上的键钮,几行文字出现在有光亮的屏幕上:爸爸,男子汉是坚强的人,一定要挺得住。儿子祝您早日康复。
他妻子用了很低的声音在给他念,星文在听。
他们夫妻悄悄说了一阵话也渐渐睡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一辆手术车无声地出现在10号病房门口。
身穿湖绿色服装的手术室护士像秘密行动小组一样,站在门口向里看了一眼,随后喊了一声:“星文-"声音清晰地传到病房,当时我面对房门,看见那辆车缓缓而来,最后停在走廊上。
星文听到喊他的名字,内心的恐惧使他不由得发出妈呀一声。
音不高,却被我捕捉到了。那不是星文发出的惧怕和担心。分明是星文的生命在此刻感受到了什么。
也许他自己都没在意,也不会记得那一声喊。那是一个生命不由自主的独白。
这让我想起今天是他上台儿的日子。
昨天晚饭后,星文妻子打来一盆热水,上上下下为他擦洗。我想起自己已是灰垢满身了,严重的心肌扩张使我没有力气洗澡,更害怕在洗澡时患上感冒。
我望了一下星文,发现他胸襟上有几滴水珠,眼圈也湿湿的。
那是一个男人落泪的痕迹。
他脸色煞白,两只脚抖动着穿鞋下地,妻子也开始一阵忙乱。送亲人上台儿几乎都是这般狼狈。
我看到星文迈步向外走,妻子挂着苍白的脸跟了出去。
星文在车前站住了。
他手扶车边涂了漆的白色铁管,抬起一条腿想自己迈上去,但怎么也抬不到应该达到的高度,几次用力都失败了,没把那条腿跨上去。很明显,他的双腿在关键时刻打颤了。
跟在他身后的妻子分明是看到了,上前抱起他的一条腿用力把他抬上去。
星文被车推走。妻子傻傻地愣在走廊上。
又有一个病友上了手术台。
我以为星文的妻子能挺住,不会像胖袁的女人那样。但送走星文,她返回病房时,坐在空空的床上,依然双手捂住脸哭了。
60、回忆 13号病房
在13号病房住了不到3天,留在我心中的,却如失去了手足一般的惋惜与疼痛。
13号病房里,住着一位珍宝岛老兵。
1月10日那天,星文、胖袁先后出院了,病房里只留下我们一家人。满以为那个夜晚可以一人一张床,可以伸开双腿睡个舒服觉了。高兴之下,妻甚至充当了卫生员的角色,整理了床铺,打扫千净屋地,长长出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候,护士来了,要我搬到13号去。
妻的美梦化作泡影。
换房这类事,自然不用我动手。一切都是妻和志勋。包括搬运杂物等等。
我一个人空手走进13号,躺在指定给我的2号病床上。
3号病床就是那个珍宝岛老兵。
老兵的情况不太好,僵直地躺在那儿,两眼不睁,像停止了呼吸似的那样令人担忧。
4号床空缺。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蹲在两张床之间的暗影里,正在无声地做着什么。后来看清楚,是用一个小电炉子熬粥。她怕护士长发现。
医生领着一个护士进屋,直奔老兵而来。
护士把手术器械盘放在床头柜上,器械盘发出的声响使他睁开眼,自己伸手慢慢把上衣解开,露出瘦骨嶙峋的胸部,知道医生要为自己清洗刀口。
盘子响动了一下,医生拿起长镊子夹一块药棉,在他前胸费烂的刀口周围擦了擦,再夹起一块白纱布延开裂的刀口向里搅动。然后把纱布慢慢地拽出来,扔在旁边的垃圾袋里。
不知他溃烂的刀口有多深,里面淤下多少血水,这样的清理反复了多次。当夹起药纱布的镊子伸进刀口的那一刻,屋子里的空气就会紧张起来,从他鼻腔里发出的呻吟声随着疼痛的程度变化得忽高忽低。
第一次清洗结束时,他出了一头汗,汗珠在他灰白的面颊和鼻尖上不断滚动,脸色更加惨白。
医生护士走出房间,他无力地躺在床上,一口一口地喘息。我在一旁体会着他那难以忍受的煎熬与苦痛。
直到傍晚,他的呼吸才平息了一些。老伴把饭端过来,他支撑着坐起来,并没有喝多少粥,饭后只是有了些精神。
好奇心使我想了解他的一切。
“你这是怎么了?”我低声向。
他开始说话了。声音喑哑。断断续续告诉我说:“先是风心病,做了手术,换了两个进口瓣膜,花了8万。那时就有糖尿病,没想到手术后,刀口总也封不死,淌血淌水。”
"你少说点吧!"始终背对他坐的老伴提醒他,又回头跟我低声说,“脾气太犟,钱花了,罪也受了,唉--"听口气,老伴始终不理解他的苦痛。
我发现老兵的脸色忽然恼怒,嘴角一阵抽搐。怕他与老伴争执起来,病重之人最怕动了火气的。我急忙把话题岔开:“咱们说点别的吧。你退了吗?”
他似乎没有多少气力与老伴争个高低,把脸侧过来跟我说:“退三年了一”然后说起他的经历。当兵、转业、得病、手术,一件件按顺序讲下去。
珍宝岛发生战事时,他是某部排长,驻守在赫赫有名的五林洞。
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与他的营长顶撞起来。他说那一次把他气得暴跳如雷。还说了战斗英雄杨林、冷鹏飞怎么用火箭筒连续打掉来犯的几辆坦克的故事。我与他说起我的经历,说我曾在兵团二师汽车连,边境紧张时,我们连的汽车往珍宝岛送炮弹。
说到这里,他像见到多年前的战友那样亲切地问我,你开过车吗?要是送过炮弹,咱们有可能在珍宝岛见过面呢。
我告诉他,我从没开过车,更没上过前线,只是在修理间做一名车工而已。即使这样,我俩仍然谈得十分投机。
夜很深了,我们依然在聊。
本来,我俩都属于重症病人,不适宜说太多的话,话说得太多,生命能量流失,会加重病情的。当得知我们两个不但是同龄人,而且又是同月,他仅比我大了十几天以后,亲兄弟般的情意油然而生,在57年的经历中,这是遇到的第二个与我同年同月的人。由此产生的兴奋使我们忘乎所以,顺着话题,一路谈了下去。
谈他转业到地方,怎么不适应,怎么看不惯,怎么和那些官僚作风顶着干,最后气出了一身病。
我们说话期间,他老伴几次加以制止,他都不理不睬。半夜12点了,我首先打住了话头,并且意识到了将要引起的后果。
不出所料,第二天下午,老兵病情加重。医生护士们已不把我当回事,一切的重心都移向了他。几个小时后,老兵转人病危。
13号病房成了急救室,护士们出出进进都是一溜小跑儿。
我开始悔恨。在内心里早已把全部责任承担了下来,不与他谈话那么投机,那么投入,老兵不会把用于抵御病魔的最后一点点生命力全部用在交谈上的,如果保存下了那点生命力,就不会出现目前的病危局面了。
真的不应该呀!
如果老兵能转危为安,如果我一路顺利换了心脏,我已与他约好,替他写一篇短文,配上他手头上现有的在珍宝岛拍下的纪念照,刊发在杂志上,题名已打好了腹稿,就叫《珍宝岛勇士今何在?》因为他与头缠纱布、肩扛40火箭筒的英雄杨林同属一个团。
现在,这一切都保不准了。
一夜过去了,老兵仍昏迷不醒。
第二天一早,我换到了4号病房,13号只留老兵一人。
我几次想闯进去,几次都被拒之门外。无计可施,只有站立在门外,透过门口的一小条玻璃,遥望老兵模糊的身影。
我被手术车推向手术台,路过13号病房门口时,还是放心不下,扭头望了望。屋子里的氛围依然很紧张,老兵生死难料。
那天,妻到监护室看望我,我忽然想起了老兵,忙问妻:“13号怎么样了?”
老兵在我进手术室那天下午,咽下最后一口气,走了。
妻不想在我还没脱离危险时提及此事,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你就别问这些了。”
妻的这句话,等于告诉我:我永远见不到他了。
时常还能想起那个老兵,我的同龄人,我亲亲的兄弟,你临婆前向我说的话,我永远记下了。此刻,我正在想念你。
61、病友姜山
3月12日那天早上,被寒冷逼迫得只能在走廊上踱步的我,听到一个消息,说心脏内科4号病房的一个病人憋得喘不上气来。心脏内科十多个病房,单间除外,一般的大病房总要住上十个八个的。如此多的病患,出现个把紧急情况,不足为奇。在这样的医院里,更为司空见惯。心脏内科的病人,喘气困难,大多是心衰引起。我虽已摆脱了心衰,走上康复之路,依然对心衰存有后怕,典型的心有余悸。
我带着听来的这个坏消息继续向前走,来到4号病房门口,两脚不由地站住了,产生了进去看一看的念头。那念头既坚定又强烈。
妻不让我与别的病人接触,管理严格的医院,也不允许病人乱串病房。那天我把这一切全抛到脑后,推门进去了。于是认识了姜山。憋得喘不上气的,正是他。
姜山,33岁,亚布力山沟的农民。亚布力出产的烟叶,曾经为抗日的赵尚志将军所青睐。姜山同样是个不同一般的小伙,两只大大的眼睛比女孩的都美。尤其在闪动时。我看到他那天,已经黯然了许多。
凑巧的是,姜山的病与我一模一样,都是心肌扩张。从看见他的第一眼,便有了同病相怜的那种体验。他就是不久前的我。一个正处于挣扎中,一个生死未卜的人。
恐怕这就是那天我鬼使神差非要去看望素不相识的姜山说也说不清的原因。
医院动员他做心脏移植,费用可以降至5万,他顶多能拿出两万。送他来住院的父亲,办理完手续之后回去凑钱,临走时到11号来看我这个换心成功的人。我希望老人看了我,心中能产生一些希望。
老人心里明镜似的,钱一准儿凑不齐,只好打贷款的主意。农业贷款每年要播种之前才发放,山沟的雪4月份才化完。北方的农事来得格外迟。
妻发现姜山的父亲脚上那双破旧不堪的鞋上沾有厚厚的干泥巴,指定是去年秋天在田野中劳动时留下的。便把原本为我买的一双新毡底棉鞋和一件短大衣送给他,姜山的父亲千恩万谢地收下了。
妻的这一举动,正中我意。
过了几天,姜山好转一些,带上一脸的笑容来到我的病房。11号是个单间,没有别人打扰,我希望他常来常往。
姜山的父亲比我大三岁,他一口一个杨叔地叫着。
姜山家的村头有一条河,他怀疑那条河水出了问题。根据是:他们哥三个,其中两个患上心肌扩张,而这种病的病因之一恰好与水土有关。姜山的大哥病逝于四年前,现在轮到他了。家中剩下一个小弟,且不知今后如何。
姜山一家人的境遇,使我对那条河水也不安起来。那河水之中,究竟出了什么妖魔鬼怪?
与我当初的情形一样,医院在为姜山心脏移植作前期准备。第一件要做的是心肌活检和测量肺动脉压力。
姜山被推入介人治疗室。姜山的媳妇这个期间从家里赶来。
3月22 日午饭后,我睡了一觉,一点多起床散步,走廊北头气窗打开了,风吹进来,挺柔和。看见姜山拿把椅子坐在窗前,身边立着的年轻女人,想必那就是他媳妇了。
姜山今天的状态很好,不喘,也不恶心,很愿意与我说一会儿话。他告诉我,检验报告出来了,肺动脉压力过高,怕是最近做不成心脏移植。医生说给他用降压药试一试。
我鼓励他说:“不要紧张,当初我的肺动脉压也高,不要失去信心。”
我又问他:“这几天吃饭怎么样?”
他说:“买饭的钱是同室病友出院时留给他的500元,这一次家里捎来了哈什蚂和小鱼,河上的冰化开了。"他还发出了邀请,邀我夏天去他家做客,去河上钓鱼。
几天后的傍晚,我又一次散步到了4号病房前,进去时见姜山正在吃饭,一只手用勺子,另一只手挂吊瓶。他告诉我一个不愿听到的消息,他的肺动脉压降不下来,比别人高好几倍,要做,只能做心肺联合移植了。
心脏移植的失败风险为20%。
心肺联合移植是一个世界级难题,风险远比这要大得多。
姜山的下一步是什么?我心里暗暗为这个年轻人担忧。
姜山的父亲从家里赶来,这一次不用为2万元钱发愁,医院免去了所有费用,只要在手术预订单上签字就可以了。
明天是姜山上手术台的日子。与我一样,也是早晨5点。天黑时,我去了他的病房坐了三五分钟。去时本想说点什么,越到这种时刻,我越说不出什么,只在临走时说了几句祝他顺利、祝他成功的话。内心里一片茫然。
一大早,姜山准时上了手术台。
天气有变,外面下起了不小的雨。中雨。 一直挨到下午5点,还没有姜山的消息。我坐立不安,吃了几
口饭就到了三楼。几天前,他已经调到了心脏外科病房,走到一半,听到一片哭声,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很怕是姜山出了事,便加快步伐向哭声走去。近了一看,原来是另外一家人死去了条人所发出的悲痛。
姜山一家都坐在屋子里,个个茫然,面带焦虑。
早晨5点,到下午5点,12个小时过去了。成败与否,仍不见分晓。我只好返身回11号病房。
7点半钟,姜山媳妇忽然跑来,报告了一个大好消息:手术成功!走出手术室的医生个个面带笑意,说是某个部位粘连,否则用不了 13个半小时。
姜山有望了。
姜山有望与我一样获得一个暂新的生命。
这一夜睡了个好觉。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依然是惦记姜山,第一个夜晚是第一道险关,他怎么样?熬过来了吗?与他相比,我差多了,我仅仅换了个拳头大的心脏而已,他是连肺带心一起切除,再一针一线缝合上另外一副心肺。这种手术才是空前绝后的。许多国家都在为此而攻坚。33岁的姜山,亚布力山沟里走出来的小伙子,挺得住吗?
已经熬过了第二个夜晚,但不知详情。这种时刻最怕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再熬几个夜晚,度过7天急性排异反应最厉害的阶段,相对要好一些。但愿姜山能安然度过,别发生像我那样的情况。
终于到了风险难测的第7天,无意中听一个医生说姜山的状况很好。这是最大的好消息。我很喜欢姜山,从第一次看到他时就由衷地喜欢,假如我俩同在一个村子,我们之间的友情定会达到令别人妒嫉的地步。
上午妻陪我去医院旁边的菜市场转了一圈,买了些青菜,准备中午自己用小电锅熬汤。回来时发现门被推开,屋里没人。估计是姜山媳妇来过。过了一会儿,果然她又来了,我忙问她这几天的情况。她说昨天天黑后,监护中心通知她去看姜山。只见姜山闭着眼,让他睁开他不肯睁。医生说你媳妇来了,他立即睁开,但嘴里插着呼吸机的管子,不能说话。媳妇挽着他的手问他:“你哪儿难受?我说的话你听得到吗?"姜山只能动动手指,媳妇知道他听到了。
他不能说话,医生就给他一支笔,让他写哪里不舒服。他媳妇没有看见纸上出现什么字迹。姜山是念了几年书的,会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他不写。处于苦痛中的人,又无法道出。无法说出的苦,才是真正的苦。
打手术台走了一趟,打监护室走了一趟,有资格说自己是过来人了,那种滋味只有亲身体验一下才能知道。
能为姜山做些什么?在这节骨眼上。
去监护室探望,怕得不到允许。我在监护室时,除了妻与孩子,别人是不可能进入的。医生进去为我检查,也要穿上消了毒的隔离服,触摸我之前,双手要在消毒液里泡过的。想了想,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一行字:
姜山,咬牙挺住! --你的杨权
此时此刻,也只能如此。
我把纸条交给姜山的媳妇,吩咐他下次去监护室带给姜山,我希望那张小纸条,能给他带来些勇气和力量。平时,他总是羡慕我的成功。
第二天,妻去饭厅打饭,遇上姜山媳妇。她说去了监护室,把我写的纸条念给他听,没见到什么反应,把纸条拿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反应。
姜山媳妇说:“这次去,看到他气管被切开了,脖子上插了个什么东西。"
情况紧急了。
是否这是采取的最后措施?
姜山媳妇又去了监护室,10元钱买了个西瓜,只喂了一口,刚刚吞下去,就从切开的气管处漏了出来。他的嘴干,用酒精棉球给他擦,被他一口咬住不放。问他是不是口渴,他点点头。情形与当时我在监护室里苦熬一模一样。他比我熬得还苦。
昨天是姜山心肺联合移植的第14天。他存活的每一天,都具有医学史上的重大意义。当天的《哈尔滨日报》新闻图片上方,是四个特大号字的标题:挑战峰巅。手拿报纸,发觉自己的手在一阵阵颤抖。真的希望眼前出现这样的场景:33岁的姜山,从峰巅之上一路风光地走下来,走向他自己那得之不易的辉煌。
第二天下午,我端坐窗前,望着外面忽而之间又飘起的雪花,开始纳闷:不是青草都绿了吗?
一幅标准的乍暖还寒的画面,北方人常见的那种。画面的一角出现一辆医院专用蒙着白被单的推车,正在缓缓走动。不是急救,是向太平间推去的运尸车。车后只有一个女人跟着,飞雪弥漫,看不清面目。
又有一个人走了。
在医院里,最为常见的事,就是生命的结束,就是有人踏上了不归路。
慢慢走,慢慢走啊--
妻也看见了这一幕,我们谁都没往别处想。因为姜山跟我说过,如果手术成功,他就不回亚布力山沟了,留在哈尔滨,做个小买卖什么的……
姜山,你的杨叔在等待你。姜山,我的好兄弟。
62、生命属于谁(后记)
这次生命已不属于我,连同这本描写心脏移植的书在内。本该是个命绝之人,却又奇迹般活了过来,活了下来。我活的每一天都是生命奇迹。
我活的每一天,既属于我自己,又不属于我自己。从前的我在手术台上死去了,今天的我在手术台上站立起来。
我活着的时候,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不是我一个人在活着,我那躯体和精神都在不断提醒,还有另外一个人在我的身体内部活着。活着的是个年轻人。
这次生命属于时代,属于21世纪的昌盛文明,属于日益进步的医学科技。属于那张手术台和为挽救我生命的白衣天使们。
生命,看起来似乎具有个体性,独立性。我现在的生命,是在一个生命的大链条上的其中一个环节。我现在的生命具有显然的二元性,尽管只是在心理层面上才能觉察到的。
生命属于时间,属于蓬勃向上的大自然,属于生命深处的奥秘。
我那 57岁以前的生命与缔造她的父母有关。今天的生命与人类卓越的科技发展紧紧相连。
生命是用爱缔造的。是父母的爱,专家教授们的爱,每一个医生护士的爱,是一方水土及掌管一方水土的领导者的爱,是亲人和朋友,是一切关爱生命的人们所缔造的。
生命是民族的,是人类的。
在活下来的日日夜夜里,我无时不在感激这上苍布施的恩德,感激这日月光辉,感激这国运民运和我这来之不易的生命之运。感激上苍的宽厚,感激日月星辰的照耀,感激国运民运亨通的岁月恰好被我的生命赶上了。感激每天恩赐于我的空气、水和食物。
也许,死比生更基本。
也许,生是短暂的,死却是永恒。
这些只能对别人而言,对于一个活在来世的人,对于一个获得第二次生命的人来说,上述的哲学界限统统都被打破。
我生命的本身既是生命,同时又是一个生命的挑战者。
站立于生命的潮头看生命,站立于生命的前沿看生命,站立于生命的内部看生命,既看不到生,也看不见死。
前面只是茫茫宇宙,或许还有霍金正在论述的大爆炸,那正是生命源头。
从前,我曾经以为,生命只属于自己。这一次,才清楚地知道,自己错了。在生命之中,向来是找不到自己的。
当你真的发现找到了一个所谓的自己时,生命已走到了尽头。她只能让你在弥留之际,恍惚朦胧地感觉一下而已。瞬间,那个所谓的自己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生命属于谁?属于虚无吗?
当然不是。
她也不像古希腊人所认为的,属于A和Ω这两个庄重神圣的字母。那只代表生死过程中必然经过的两个点。
生命从来不是刻在石碑上的字母。我没有生命。有生命的只是细胞。
我的生命属于每一个细胞。从父母身上遗传来的,从另一个生命那儿移植来的。
努力工作的细胞死去了,崭新的细胞便会诞生。细胞的生命才是永恒。
那些被认为是死寂的空间,总会有细胞存在的。总会有生命存在的可能。
生命属于谁?
生命只属于生命本身。
属于即将过去的2004年,属于即将到来的2005年。
屈指算来,我这次生命,在这个空间中,已经存在了5个365天了,这是一种意识在告知。用先哲的话说:我思故我在。
仔细想一下,也只是我在而已。
当我想起,这本书就要与读者见面的时候,心里思索的还是一个生命的存在。但很快又被否认,生命不只是存在。
她还有更多更多。
如此时的我心中所思,却又一时说不完整的那些。请原谅我手中这支笔的笨拙。
2004.10.31于哈尔滨龙房小区




玫瑰手绘折扇、玫瑰国画
订购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