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血粮》:
发掘莫言作品的人民性内涵
程小源

文学评论家李恒昌先生继完成“当代著名作家创作评传系列”的前四部《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大地上的歌吟:赵德发创作评传》《大地上的星光:铁凝创作评传》和《大地上的泪光:桑恒昌创作评传》之后,新近又完成了第五部《大地上的血粮:莫言创作评传》。捧读这部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让我们着实为之感到惊叹。一是感叹他强烈的责任意识,那种想通过自己的系统性研究和写作,介入当代文学发展,为促进当代文学发展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的责任意识。二是感叹他研究的宽度、速度和深度,简直可以用惊人来形容。要知道恒昌先生做文学研究并非他的主业,而是一种业余爱好。
《大地上的血粮:莫言创作评传》(以下简称《血粮》)是一部呈系统性、全息性、开放性且非常生动的学术之书。一看书名便给人一种既炙热又冷峻、既辽远又亲近的感受。“血粮”这个有着极强视觉和心理冲击力的物象——意象,确实有“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蕴味。通读了文本,才会品咂体悟到“血粮”的意蕴:带着生命的脐血深深扎入了脚下的大地,指向了家国历史命运的深远云空;深情地探索了“血粮”的来路,诗意地叩问了“血粮”的去路。在这里,血粱,作为一个物象,即“指故意从胃里抠出来,带着血丝、喂养别人的粮食。这一情节,莫言小说中曾三次提到”;这更是一个极富诗的意象的能指和所指,那就是赋予了血粱以生命及其思想精神动力意义,这种动力从更加形而上的意义来讲,当然有着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作用出来的原发的那种神秘力量,更是将这种力量不断衍射到历史、民族、体制的深入思考上。可以说,“血粱”这一崭新命名,既是莫言与其他作家作品区别开来的显著标志,又是对莫言作为“高密东北乡王国”名副其实的缔造者和国王、作为世界文学大家崇高地位的再次确认。
就这部著作的当下意义而言,最独特的价值一个在于凸显出了一种“纠偏”的功能,即纠正了当下存在的来自莫言接受的种种偏见。“有人说,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他的作品写得多么好,多么优秀,而是因为他暴露了我们的愚昧、落后和黑暗,而且迎合了西方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持这种说法的人,恐怕大多数人没有真正读过或读懂他的作品,没有走进他深沉而博大的文学世界,更多的是道听途说、望文生义,或人云亦云,或以点带面,或以偏概全。因为,只有认真深入地阅读他的作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才能全面深刻准确地理解他的思想、精神和情怀,才能真正领悟和把握他文学的要义、真谛和价值,才能真正摸清其文学创作所坚持的道路和方向。”(《血粮》)另一个是具有“掘金”功能。即面对当下某些文学批评善于从理论和概念出发,疏离作品本身而作理论连环套的流弊,他积极探索了学术研究如何走出象牙塔的独特路径,坚持从作品出发,善于在作者创造的文学宝库中掘进,从而挖出“真金”。在莫言研究以顽强的生命力终成显学的今天,《血粮》这个具有“纠偏”和“掘金”功能的文本无疑是值得珍视和研究的。

恒昌先生在第一章以《诗学王国》为题,探究了莫言创作的生发、分析了莫言创作思想精神的丰富内涵及属于莫言的独特内质。开篇即引用著名作家张炜的一首诗《从诗经出发》,这在整部著作中有着特别的意涵和意义。“从诗经出发/除了民歌什么也不怕”,在这里,民歌无疑是指《诗经》中“风”的内容。诗经中唯有“风”真实再现了古代最广大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画卷;抒写出了那个时代人民的爱恨情仇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也正是这样一种抒写,才使得“风”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芒滥觞,与屈原浪漫主义的“骚”并峙成为吟诵千年而愈发闪烁出文学经典的光辉。而“除了民歌什么都不怕”,则进一步表明了最广大最底层的人民才是令人尊重,让人敬畏的,因而只有为人民而歌而写作才具有崇高神圣的意义,也才能为确立文学经典提供可能。君不见《诗经》中的那些所谓的文人生活的“雅”、那些为神灵和君王而作的“颂”则是不足畏的,随着时代的流变几近灰飞烟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从这一点看,《血粮》无疑发掘到和确定了莫言的创作从出发点到落脚点无不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血粮》中所列举、分析的每一个人物、每一处场景乃至人物经历、情感精神,都深深打上了人民的印记。正是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人物命运才构成了家国的宏大主题,正所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身为土匪,在外族入侵的关头,毅然举义,一个身怀民族大义的人物形象霍然而出。在这里,余占鳌是为人民的,也是为家国的,因为没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就无所谓国家民族了。
“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就莫言这一创作理念,恒昌分析到:“这是莫言关于典型塑造的一个重要观点,也可以说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理论。这一观点,表面看仅仅是一个人物塑造问题,实际上是文艺如何更全面更立体更丰满更深刻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这一观点的提出和实践,有助于减少和防止人物塑造的片面性、单一性、扁平化、绝对化等问题,也有助于克服传统人物塑造‘假大全’‘黑白分明’等问题。由于‘把好人当坏人写’,所以‘好人’不再没有缺点,不再是‘高大全’,因此更加符合实际,也更令人信服。由于‘把坏人当好人写’,所以坏人也总能体现人性光辉的一面,有可取的一面,不再是单一的坏人,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人,因此也就更加客观,更加真实,也更有力量。由于‘把自己当罪人写’自己虽然站在独特的‘制高点’上,但总有一种负罪感,也总有一种忏悔意识和赎罪意识,因此也就更加深刻,更加尖锐,甚至直抵灵魂深处。”莫言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有瑕疵和缺憾的,透过魔幻色彩,更彰显出莫言作品强大的真实力量。正如著名电影导演贾樟柯先生在论及电影艺术的正能量时所言:“所谓正能量,首先要真实,真实是最大的正能量”。恒昌先生在《血粱》中,从创作、作品、接受方面,全面系统分析了莫言的人民性的深刻意涵。创作主体的民间立场和平民化视角,更具有亲和大众的人民性。“为什么要强调不能仅仅提倡‘为人民写作、为老百姓写作’,而是要提倡‘作为老百姓写作’呢?因为,这是一个写作立场和视角站位问题。在莫言看来,仅仅‘为人民写作、为老百姓写作’,有种把自己置身人民、置身老百姓之外的意思,也有一种人为的隔阂,甚至‘恩赐’的意思;而只有作为老百姓写作,才能真正把自己融入人民、融入老百姓之中,也才能真正懂得普通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求,也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立场,也才能真正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服务’。他在苏州大学演讲时指出,‘为老百姓写作’听起来是一个很谦虚的口号,听起来有为人民做牛马的意思,但深究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恒昌的这段论述,说明了莫言的人民性具有两重积极意义,因而他的作品所凸显的人民性就具有更加真实的力量。人民性的时代性。通过恒昌的精道分析,再回到莫言的作品,会深刻感受到莫言的人民性抒写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所标识的人民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内涵是不同的。无论是兵荒马乱的年代、贫穷饥馑的年代、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的年代及至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莫言始终站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坐标点上,抒写着人民“当时”的生存存状态、爱恨情仇和对未来生活的祈盼憧憬。恒昌在两个层面上对人民性的真实性做了分析: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概念是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反映出来的。莫言既放大了人的美好质素的光芒,也深刻发露了与文明相悖的人的丑陋;而更多的则是展示了最广泛“不好也不坏”人物群体。从逻辑上看,只有“多数”才构成“人民”这一概念的外延。真正的坏人是少数,真正的英雄模范人物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处在“中间”的人物。文学作品如果仅仅塑造或反映好人或坏人或只在好人坏人的对比中凸高好人,就会流于空洞的符号化和标签化,势必消解文学作品反映社会人生普遍性的真实力量,就莫言而言,也就无法解释其作品凸显的广泛的人民性、民族性、民主性特征了。“事实上,他的很多小说,很多故事,都具有多义性,也都实现了这种哲学上的突破。”恒昌说的这种哲学上的“多义性”正是莫言作品人民性丰富内涵的折射反映。
读恒昌先生这部著作,感觉他真的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他为大众真正走进莫言开出了一条布满宁静芬芳的便捷路径。那鲜活生动的叙述语言、学术机理的骨感张力、逻辑自洽的充分论证、旁征博引的新知,更有经过高度浓缩、脉络明晰、精准还原的莫言故事,让无暇眷顾莫言浩如烟海作品的读者,走进一个莫言魔幻的现实世界,见识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体悟他们的情感焦灼、共鸣他们的生命精神和人民性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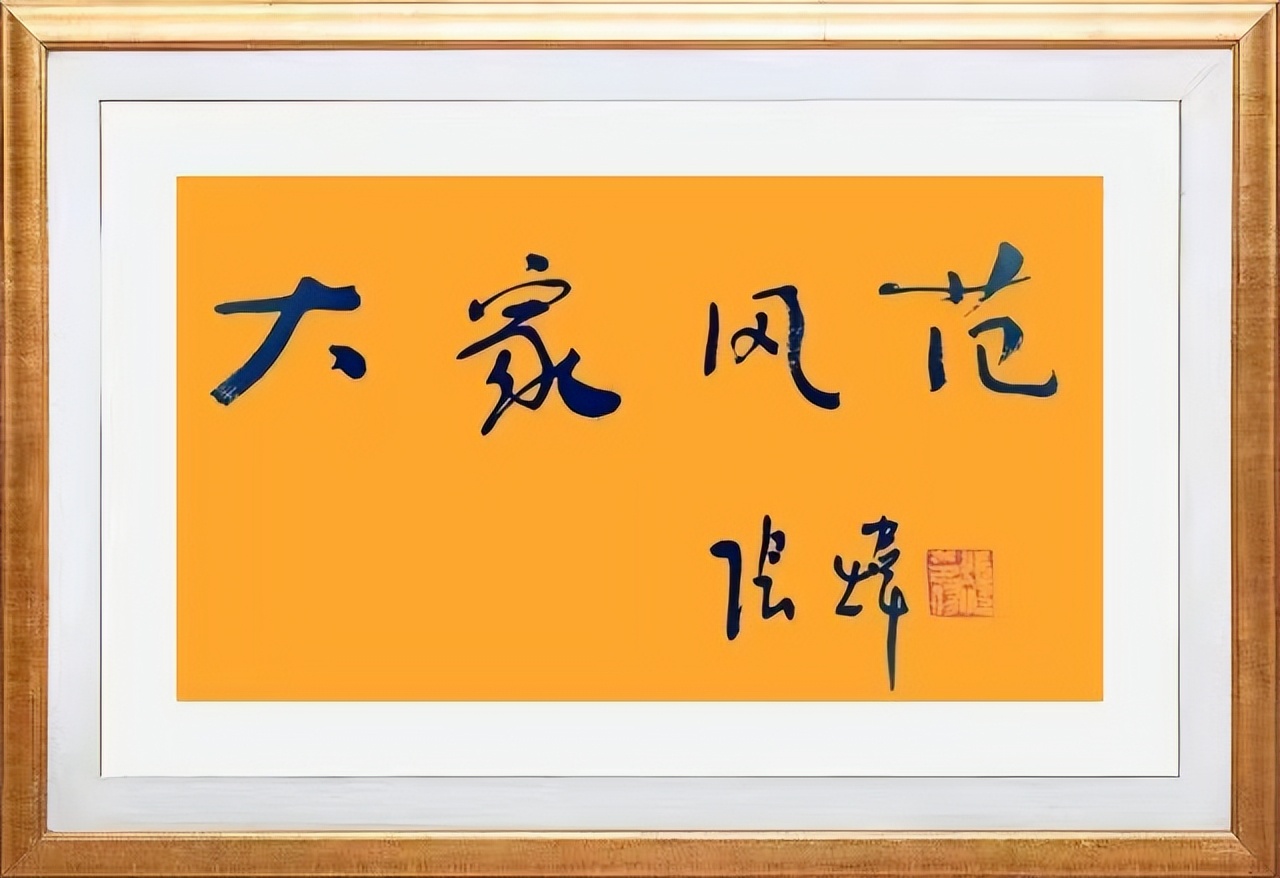
图书出版
文学、论文专著、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
国内单书号、丛书号、电子音像号、
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出版、印刷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家风范文库·诗词十六家》
《大家风范文库·散文十六家》
征稿进行中
13325115197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