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25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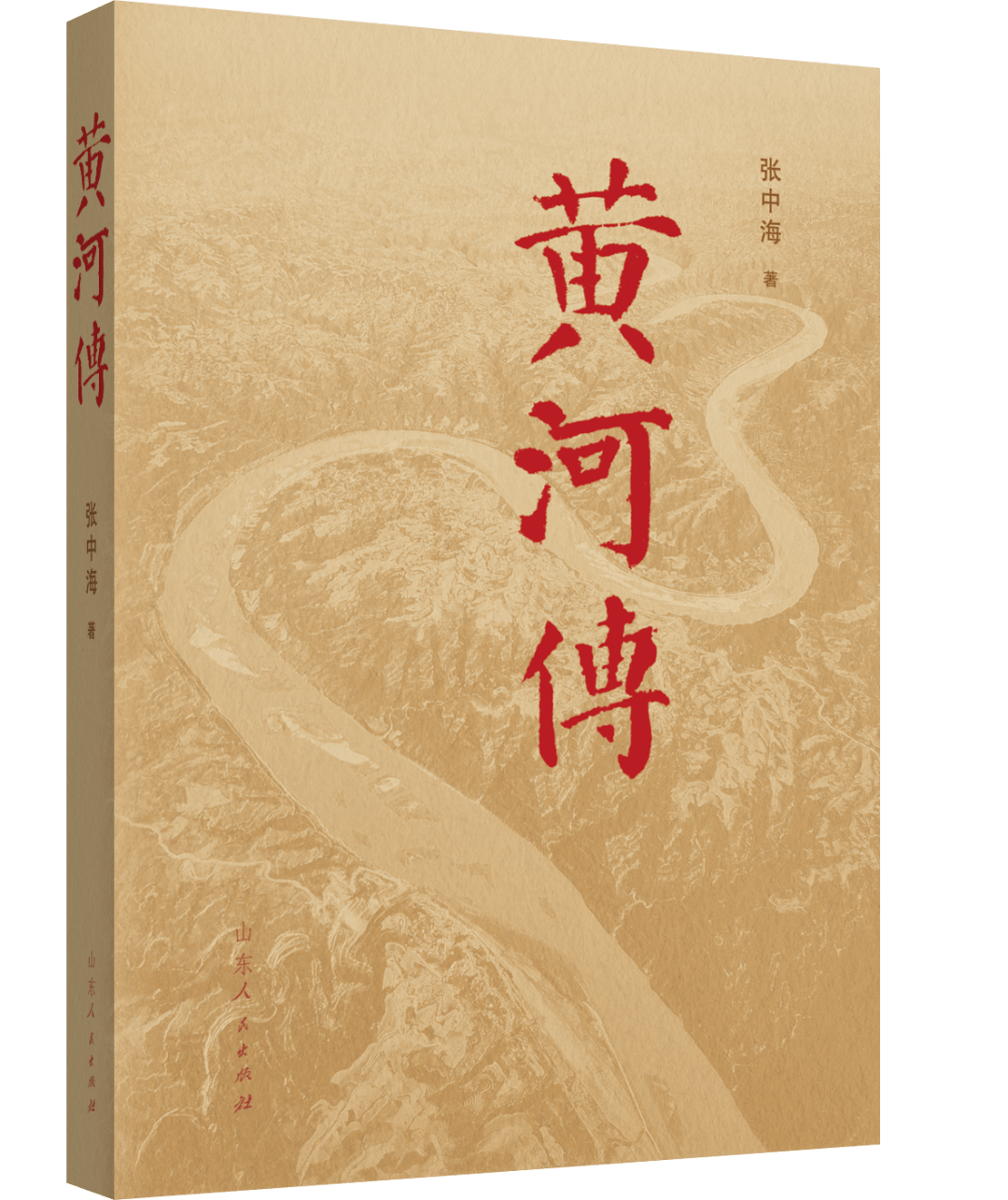
第六章 表里山河(山西)(四)
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祖先来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里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鹳窝。
一首流传大半个中国的民谣,让多少中华儿女,包括流转海外的华人,生出多少无尽的乡愁!
洪洞大槐树植于汉代,《洪洞县志》载,“树身数围,荫遮数亩”,以至繁衍生息于汾河滩的老鸹,在树上筑满了巢穴,方圆百里内,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棵奇树。
大槐树西,就是当时殿宇巍峨、香客络绎的广济寺。大槐树下是阳关道,明初大将徐达的行辕兵站就设在洪洞。正是有此诸多因素,才使大槐树成为移民文化的一个象征,也成为无数从大槐树走向神州各地移民后代们的集体记忆。
秦、汉、唐、宋包括西晋,都有大量人口移居中原,清代又迁两湖人移居四川,又开放东北封禁地移冀鲁人出关,人数都超过百万,但由于这些移民没有一棵老槐树,所以随着时光的消逝,这些移民就失去了记忆。
唯有老槐树,让人记着了家乡,记着了时光。
元朝末年,中原腹地战乱频仍,再加旱、洪、蝗、疫,尤其是黄淮二河屡屡决口,村庄城邑多成荒芜。中原诸州,元末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见。朱元璋推翻元朝得天下后,采纳他人建议,作出向中原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决策,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洪武大移民”。
明太祖朱元璋后,“ 靖南之役”连续九年,从北京打到南京,让冀、鲁、豫、皖、苏等地雪上加霜。于是,朱棣在夺取皇位移都北京后,又效仿朱元璋开始第二次移民,即“永乐大移民”,前后两次,历时五十年。
明朝两次中国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移民为何选在山西,又为何选在洪洞县这棵古老的大槐树下呢?
请看有着“表里山河”之称的山河形胜:太行山位于山西之东侧,吕梁山居山西之西;汾河中流横贯,而秦晋峡谷、黄河又以700余公里的跨度成为陕西与山西的天险屏障,虽然地处黄土高坡,却也有着两河及数不清的支流浇灌,这就使它即便天灾不断也还大多时候都旱涝无虞。正当中原地区连遭战火瘟疫之时,山西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物阜年丰,人丁兴旺。加之相邻各省难民源源不断落荒山西,山西成为明初人口最稠密之地。《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河南人口为189万余人,河北189.3万,而山西却达到403.454万。在山西,人口稠密又首推晋南汾河平原,仅平阳(今临汾)一府就有165万人之多。晋南又以地处交通要冲的洪洞为最。安土重迁的国人谁会轻易抛离生养自己的故土而情愿到荒芜陌生的地方?人口迁移不可能少数,也不可能依靠时人觉悟。既然是国家行为,强制那就离不开刀把子、枪杆子,明大将徐达的兵站就在洪洞,而洪洞又正合洪武一统天下之谐音,无论哪方面考量,都注定了明朝中央将洪洞定为移民集散地的首选。
为迁徙顺利,中央政府在当时人口稠密的汾州府、辽州府、沁州府、潞州府和平阳府县衙张贴告示:不愿移民者,限三日之内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领免迁证;愿移民者可在家等候。于是,成千上万的百姓披星戴月、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赶到大槐树下,八日之内,就云集了十几万人。老实的庄稼人还未等喘过一口气,便被官兵团团围住,这才知道上了官家的当,愿移也得移,不愿移也得移。为此,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立了专门移民机构,委派官员驻守,集中扣押移民,“凭照川资”,整编遣送。移民被绑拴成长队,像犯人一样,分别向全国一百多个府县解押。
至今各地方言中有许多地方都通用“解手”一词,还有走路背手的习惯性动作,移民后人解释,这是由于移民在押解途中手被绑到身后,要大小便就得向押解官禀报:“请解手。”如此三番五次,“解手”就这样流行起来。
小时候伙伴们在一起玩水,稍大一点的孩子往往都神秘兮兮让你看小脚趾头的指甲是不是两瓣,如果是,那就是祖上从山西洪洞老槐树底下来的。结果所有小孩子小脚指甲都是这个样子,因此知道,虽然东邻西舍不同姓、不同族,但是来路却都一样。也有传说这是人们在移民途中想以后难免各自东西,怎样才能确认自己身份,便把小脚指甲剪为两瓣。还有说是当时官员怕移民在途中逃跑而把移民小脚趾砸裂而留下的畸形。
沧桑岁月,移民的后代无论走到哪里,都知道山西大槐树是老家。因此无论走到哪,都先在门前栽一棵槐树。仅作者出生的小庄,几百年的老槐树不下五棵之多。只是由于村民一开始没放在心上,以后新村规划、再以后所谓“棚户区”改造,至今一棵也没留下。
作为历史见证,大槐树昭示着世事沧桑,也荫庇了无数生灵。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新任巡抚张锡銮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当浩浩荡荡的队伍开近汾河,准备血洗洪洞县城时,部队士兵看到了大槐树,这时,奇迹发生了,无论冀还是鲁还是豫籍的官兵,纷纷丢盔弃械奔于大槐树下,折槐为香,五体投地,久久不肯起身,说是终于回到大槐树老家了。无论首长怎么发号施令,也无法使队伍集合起来。因一棵民心所向的大槐树,晋地数十万百姓免于一场血灾。后来,为感激大槐树功德,后人在旁边建起一座牌坊,题刻“荫庇九州”四字。后来又修了碑亭,石碑正面镌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书大字,背面刻有叙述移民事略的碑文。
迄今五百年过去了,昔日僧侣济济的广济寺早已风流云散,当年那棵古大槐树也已不见,绿荫成盖的是古槐的二代、三代孙。
“黄土坬聚湫”与“瀵泉”与盐池
“聚湫”是黄土高原沟壑两岸山体滑动偃塞聚水拦泥形成的淤积地,地方性名词,自然形成的淤地坝。位于陕北子洲县裴家湾黄土坬村的“黄土坬聚湫”,形成于 1569 年,即明朝隆庆三年,旧志记“黄土坬山崩地成湫”。湫坝高62米,集水面积2.72平方公里。四百年来淤地800亩,坝地土质肥沃,粮食单产每亩1000斤以上。
“湫”内平时无水,遇大雨来洪,水位迅速上涨,然后又渗入地下,不知渗入何处。据黄河史志资料文员王建华调查,1977年一次大暴雨,“湫”内积水50万立方米,然而不到20分钟,全部渗完,这一高原奇观之谜至今尚未解开。
村民介绍,坬湫神奇有五。一是四面环山形似阔叶的湫滩山洪不溢,坝不存水,高出地面两米的坝堰随淤地增高,从没有人培筑。二是每逢大雨,积水总从一个地方渗漏,呈漩涡状,再次大雨后,积水则从另外地方渗,从不重复。三是每夏秋季,村民常闻牛叫,或大或小,或远或近,但不见牛的影子。四是湫滩南端有一泉水,旱不降,涝不溢,泉水取走后很快又恢复原水位。其他沟叉泉水则经常干枯。五是坝内芦苇叶包的棕子,七八天后还新鲜如初,其他地方苇叶包的,则三两天就变酸。
自五十年代以来,不少从事水土保持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前往“黄土坬聚湫”考察,一些专家根据其四百年来“ 不满不溢”,将洪水泥沙“吃光”的实际,通过系统分析,提出淤地坝的“相对平衡理论”。即一个小流域,当坝地面积占到集水面积的三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一时,坡面所产泥沙,坝地可全部消化,达到相对平衡。
而裴家湾的“ 黄土坬聚湫”,聚水面积与坡地面积的比例为十五分之一。
与此“聚湫”遥相呼应的是小北干流右岸的渭南“瀵泉”。《水经注》
曰:“河水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阴县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开源,濆泉上涌,大几如轮,深则不测,俗呼之为瀵魁。”称瀵泉,是由于地下水受土壤、岩石性质影响,上升泉水含相当数量的硫态氮而形成瀵水,即肥水。现合阳县东部黄河西岸东王乡夏阳、王村一带仍有分布,呈南北或北东向排列,出露于黄河浸滩和河心滩上,因河道游移而时出时没。《合阳县全志》载:“以瀵名者,他邑所罕见也,而合阳旧有五。”《太平寰宇记》曰:“瀵水,总名,发源于黄河西岸平地。”
随着黄河河道游移,或淹没或出露,至1994年底,渭南小北干流仍有天然瀵泉7个,总流量为每日83665.2立方米。其中之一的洽川“处女泉”大小泉眼无数,人入水不沉,泉涌沙动,如绸拂身,相传洽川女子婚前都要到此沐浴。
实际上,泉涌如流是因为渭南小北干流地下水丰富,并多层分布。水文人告诉我们,这里浅层地下水埋深3—6米,深层地下水埋深40米。潼关黄河河漫滩及渭河一级阶地为极强富水带,水埋深2—6米,水层厚43—69米,最大涌水量每小时50—300立方米。二级阶地水层厚达57.6米,单井最大涌水量每日318.8—584立方米。
地下潜水丰厚主要是沿河河水补给;再是自上古以来,这里本来就是古湖。
或许,上述“黄土坬聚湫”积水转瞬不见,以济水“三伏三见”之理论解释,“坬聚湫”之水,最终是从黄土深处渗透至早已淤平的古湖底?而最终出露于“瀵泉”?
只是如此丰厚的地下水宝藏,至今也所剩无几了吧?
大同古湖、汾渭古湖被黄河贯通成为黄河河道后,大小湖泊找到自己入海的归宿终消逝不见,解州盐池就成为那时古湖唯一的遗迹而留在人间,存之现代。
运城盐池东至安邑,西至解州,南依中条山,周长60公里,是运城盆地的最低处。池面海拔320米,水深0.2—2米,为天然内陆盐湖。盐池有东池、西池之分,历史上制盐主要依靠东池。
盐不必开花结果,就成为人类生命的源泉。人类征战最初的原因之一也源于盐。历史烟云深处,1482年威尼斯与热那亚间的费拉拉之战,被称为“盐战”。在廷巴克图驼队沉甸甸驮着的板盐中,一种通透、明锐、删繁就简还能刺激人胃口大开的物什,在太阳照耀下,散发着极品的玫瑰色晶体肌理。四川大学诗人向以鲜先生考证,它还是光的源头之一种,巴基斯坦就用它制成盐灯。它更是肴馔之髓—攘除病菌与不洁,涤净脏腑中瘀滞的尘世腥膻。这里就不说它所给人、给牲畜以支撑的不肯弯腰屈膝的骨头、骨头的钙,甚或思想的穿透力、目光的烧灼与滚烫了。
在炎黄子孙发展史上,远比15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间盐战还要壮阔也还要久远的,自然是黄帝战蚩尤于解州了—名副其实的盐战。黄帝与蚩尤争夺的就是盐池—谁拥有了盐,谁就有了无往不胜的战旅,有了税赋,有了富有钙质的精气神,甚至有了号令天下的权力。所以解州盐池在这里已不仅仅是盐,更重要的是它的见证意义。
不仅见证华夏先祖的盐战,还有汾渭古湖、大同古湖或许还有多少年之后青海湖的百年孤独?
揭河底:大河之奇观,大自然之欣悦
静。出奇的平静。河面上树枝、杂草漂浮,一股浓浓的泥腥气息,像是从深窖、百多世纪前的地底涌出,在辽阔河面上弥漫。间或三两只羔羊或一棵树从峡谷里飘来,平静中显露出不祥的意味……
这是黄河晋陕大峡谷出口龙门之下,在高含沙洪峰起涨之前,1977年7月的一天。顷刻间,黄河咆哮了,沉雷一般,低沉而短促。先是浓稠的泥浆冒出水面,接着,如房子一样巨大的泥块,难以想象地从刚刚还平滑如镜的河面竖着挺起—不是平着、浮着,而是竖着、站着—由于河面漂浮物急湍流走,在河流漂浮物的映衬下,如在急速行驶的列车上,我们看到村庄、山河、树林,都是往车后头奔驰,这前呼后拥、泥垒耸然的浪峰不是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一时浊浪排空,泥墙被水流推动,气势磅礴。前面轰然倒下,后面次第崛起,低者几可盈尺,高者竟达丈余,此起彼伏……
在潼关至龙门间 100 多公里的河段上,排开了俨然万马奔腾的战列……
“……行数里,巨浪排山而来。中有神人突起,高二丈许,伸两巨手摆泥沙,战战而倒,如是者数十处……”
此为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汴梁水灾时候补知府邹鸣鹤率文武百官乘舟前往决口三十一堡时所见异象。时人蒋湘南著《辛丑河决大梁守城书事》记:“水中巨人数十,掀巨浪翻滚,舟人惊呼,水怪!……往时黄河中曾有之。”
清人蒋湘南所记道光年间“水怪”,发生地为河南开封。
以上怪异水文现象,被黄河两岸人们称之为“揭河底”,是中游河洪爆发时不经常见的现象,而在禹门至潼关一带河段却时有发生。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小北干流水文资料记载的“揭河底”出现9次,一次一般为17—22小时,最短者是1969年仅6小时,最长者是1954年68小时。龙门河段河床冲刷深度为2—4米,1970年达9米。冲刷距离最短者40公里,1951、1954年两次冲刷距离最长达潼关132公里。
被美国人塔德1933年惊呼“世界河流之奇观”的“揭河底”,是黄河干流上独有的一种狂暴,或曰大自然自我调整过程中难得一回的欣悦。以1977年揭河底为例,《黄河报》王梅枝总编引1994年7月31日记者追述给我们以详尽描述。
伴随河道的剧烈冲刷,沉睡经年的河底淤积被整块掀起,被掷上岸,沙石、树干,还有大小不等的黑色炭块,让人惊叹的竟然还有从黄河壶口龙门辿冲下、被泥沙密封淤存多少年的大若写字台的冰坨!
霎时,河底如恶蛟潜行,河面如巨龙腾飞……一片迷蒙……
专家介绍,揭河底冲刷是高含沙洪水巨大能量与河床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水与沙的双重作用下,揭河底能使河槽刷深缩窄,滩地淤高变宽,槽滩高差增大,一般10个小时后,这股不可遏制的神力,就在河床掘开一条数米深的河槽,原来攻城略地般疯涨的水位骤然下降,浩荡大河顿时束水归槽,晾出两边像刚刚耕过的滩地……
后来统计资料表明,1977年7月揭河底时,龙门水文站所测最大流量为14500立方米每秒,来自黄土高原各支流的暴雨洪流冲垮了14000多座拦淤坝库,含沙量高达每立方米821公斤。
揭河底的第二天,山西万荣县一老农到淤滩上拣拾煤块,淤柴间,发现一俯卧的赤身裸体的姑娘。老汉小心翼翼地抠出姑娘鼻孔、眼睛和嘴里的泥沙,发现她青春的脉搏还有微弱的跳动。姑娘被救活以后人们才得知,这是一位北京下乡知识青年,是在龙门以上山坡放羊被山洪卷入黄河的。
如此现象,我在采风过程中还遇几例。就这河段龙门水文站上,一位技术员在滔天巨浪中取观测数据时,从船上被风浪打下去,水文站同事寻找无果,已通报家人,也找出了技术员衣冠准备办后事时,技术员回来了。也像这女知青一样,被水后拾炭老乡救了出来。河南封丘滩地顺河街村一位岳姓村民,看高粱睡窝棚里,半夜被来洪冲走,一开始他还记的是抓住了一根漂浮的檩条顺水漂流,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三天后,他被人救出并送回村,见胡同口一干人马披麻戴孝,他才知道,那是族人正给他送葬……
和世界及海内另外一些大河比,黄河洪水自有她暴谑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善、和,不伤人。滩区村民这样说。
黄河小北干流“揭河底”最早起于哪朝哪年?据《潼关县志》载,“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十月,夜大风,声如雷吼,河水暴涨,泥沙俱下,潼关城倾倒。”类似现象,《朝邑县志》也有“地啼”的记载,但那时还没有“揭河底”一词。
最早一次揭河底记述文献是1933年美国人塔德和挪威人安立森合署论文《黄河问题》。该文记载,1933年8月1日龙门发生“揭河底”,最大日平均流量8500立方米每秒,龙门河床剧烈冲刷12小时,在龙门附近1公里范围内冲刷深度9米左右,龙门上下游50公里范围内河床平均刷深4.5米,冲起泥沙约2亿立方米,其中一部分淤积在潼关以上。潼关一直到陕州附近刷深1.0—1.2米。
也就是在这次大揭底冲刷之后,龙门附近河岸岩石上古代埋置的拉船用的铁环,被淤埋多年后又再度被冲刷暴露出来。
“揭河底”是游荡性河道剧烈的自然冲刷现象,是在一定条件下,即行河道老化后河道的自然调整。遭遇揭河底后,河槽又回淤抬高,长的时间需2—3年,短的则当年淤回,河槽复变宽浅,河势游荡加剧。这一水文周期循环和河道往复性演变,周而复始。1978年前,人们普遍认为揭河底应具备三个条件,即“流势乱;水上万;沙过半”。“流势乱”指河床淤积到一定高程后出现“滚河”;“水上万”指洪峰流量超过1万立方米每秒;“沙过半”指来水含沙量超过500公斤每立方米。总之,它的产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是水流含沙浓度高,持续时间长;其次是洪峰流量大,洪峰与沙峰过程一致;第三是河床边界条件—当河床横断面形态和纵比调整到一定程度,且河床淤积物具一定厚度、固结度。这样,高含沙洪水水流能量才能作用于河床,使其深水切应力异乎寻常地增大,从而带动或掀起巨量泥沙,形成“揭河底”。
龙门水文站自1933年建站后,直到1950年未观测到揭河底。从1951年至1977年,则观测到7次。分别是1951、1964、1966、1969、1970和1977,其中,1954年8月9月,1977年7月8月,分别两次。1978年至2011年,没发生一次“ 揭河底”。而此时,河床高程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1988年、1994年、1996年均发生了上万流量的洪水,1988年含沙量还达到500公斤每立方米,但揭河底现象还是没有发生。相反,1993年、1995年流量不大,含沙量也不足500公斤每立方米,却发现有少量泥块被掀出水面,类似揭河底,但规模却远远不够,也没形成高滩深槽。所以,至今对揭河底成因没有富于说服力的结论,因而愈让人感觉到大河的神秘。
2012年7月28日,就在我重整旗鼓准备再启黄河源之行时,黄河小北干流的龙门以下河段,又发生一次自1977年再也没发生过的“揭河底”。
河务水文人员有视频录制,那前呼后拥、立在水头、隆隆向前的阵势让人不由地心惊肉跳。
一样的雨,不一样的祈最早看到“扎马嚼”,是在黄河上游的纳顿会上。纳顿会是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地区土族特有的传统节日,喜庆丰收的狂欢。诸多仪式中,其中有“跳法拉”,即有威望的老人把铜钎插过腮,表示此部落对丰收希望的虔诚。
运城学者郭瑞倩考证,上游纳顿会上“跳法拉”,是以下游小北干流临猗、临晋一带祈雨中的“上口钎”传至上游的。
农耕社会靠天吃饭,有雨等雨,无雨便求,这也仅是祈求者的一厢情愿。所有农村出身的人,大约对祈雨场面都不陌生,跪、拜、供、求:老天,可怜可怜我们吧,庄稼干了,地里的蛤蟆也都跑到外地逃荒去了,你挤下点眼泪水就是我们的好日子,你干瞪起眼,我们就只有等死。其泣哭哀号的有两种结果,让铁石心肠的所谓鬼神也为之动容,或无动于衷。
仪式更隆重的除了摆供桌、烧纸香之外,还请来女巫或由酋长率领,在白花花太阳底下光着膀子长跪不起,谓之“曝”。自虐。
“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周礼·巫》如此记载。
“ 求”,即是祈的全部形式和内容。本来就是弱者,这次就更有准确的身份定位,在大自然面前,在大自然的化身“老天爷”“龙王”面前,虔诚,毕恭毕敬—绝对不能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大不敬”—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但在这里,在河出龙门的山陕峡谷左岸临猗县一带,同样是祈,却绝对没有如此窝囊。
先是“扎马嚼”。就是由一精壮男子将筷子一般粗也一般长的钢纤从嘴里刺穿面颊,类似给马、驴嘴里戴的“嚼子”。马驴戴的“嚼子”也只是起一个“勒”的作用,不伤大雅也不伤皮肉。而汉子的“扎马嚼”则是直接扎穿,决绝的一扎一穿,龙王爷就知道碰上不好惹的茬了。
传说“扎马嚼”仪式起源于圣尧率众祈雨,巫师纵马绕城,一气驰骋数十圈,为激发马力,一次,巫师把平时只带在马嘴里的嚼子以铜钎插入,只差一圈时,马体力不支。就在前功尽弃之际,尧王情急之下,将铜钎从自己面颊扎过,代马驮巫师跑完最后一圈。刚跑完,天空就阴云密布,接着大雨如注。从此,附近子民开始效仿尧王“扎马嚼”以祈雨。
“扎马嚼”分上马、逗马、回马三个阶段,时间持续三两小时。为防止血液与钢钎凝结,隔个把小时,被扎者还要嘴含冷水,将钢钎抽动几下,而绝不是虚晃一枪,仅做个样子。
对此,郭瑞倩有记:
逗马、回马到了一定时辰,接下来就要去黄河取水了。事先选定的属龙的青年,此时已着龙袍,挂龙须,扮成了龙王模样。“马嚼”大鞭一辉,指向黄河,“龙王”还有些怠慢,如辫起的长串蒜头一样粗的马鞭已抽向“龙王”,而此时,“龙王”已被剥了衣衫。打着赤脚的“龙王”扛着锁链,抱着瓷瓶,无可奈何,可怜兮兮,像被押解的囚犯或苦役……
在“马嚼”的胁迫下,“龙王”很不情愿地向河边颠颠地小跑而去,就在这时,火铳响起。前有火铳开道,后有子民簇集,一路上,“ 马嚼”还不时对“龙王”进行语言呵斥和行动恫吓,“龙王”则唯唯诺诺,唯马首是瞻。其间,人群中难免有戴草帽什么的不识时务者,“马嚼”见了,自然火不打一处来,挥鞭就抽—“龙王”都被我折腾得服服帖帖,为的就是让雨来得更猛更大一些,你居然还遮雨防雨,不抽你个皮开肉绽又待何时?到了河边,“ 马嚼”喝令“ 龙王”将瓷瓶灌满水,背在背上,再在瓶口插上柳枝,呼啸返回。这时,“龙王”和宝瓶便成了“一级保护动物”。
都在一个天底下营生,大旱不雨不会是一村一户,所以,沿途村庄抢水的肯定会有,已经红了眼的“马嚼”大鞭正好有了用场,抢水的邻村人纷纷被抽得抱头鼠窜,等到了自己地界,又是全村男女老少的盛大欢迎仪式,等水徐徐“流进”地干苗枯的田间,“龙王”才恢复了些许做龙王的尊严。
一样的雨,不一样的祈,这就是小北干流黄河儿女的做派。
先天的地貌地形制约着大河流动,大河的冲刷又反过来塑造着河岸地形,也塑造着两岸人的性格。或静水流深,或随波逐流,或桀骜不驯,或迂回蛇曲,你如见证了小北干流独有的揭河底的摧枯拉朽,你就知道了什么是河东人中河津之耿、荣河之直,抑或是临晋之执、风陵之烈。你就知道这种爆发或沉郁,都是黄河式的自我疏导与修复,是地理地缘使然,是大自然之难得一回的“欣悦”。
《民国临晋县志》总结其本土民习性云:“尚气节、黜浮华”,“惟劳苦忍耐”,想我黄河子孙之倔之执之烈,在河出龙门的山陕峡谷,自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吧?否则,这些能将长河都染上血色的诸如“扎马嚼”“背冰”“亮膘”等重口味的民俗社火,怎么会如此集中产生沿袭在这黄河中游的河谷地带呢?无论是从上游还是下游流传至此,都已被这里的激浪或泥沙打磨得更炫目多彩。
不烧一炷香,不磕一个头,不上一点供。如此的祈雨哪里是祈?简直就是揭竿而起,一场男女老少齐上阵的造反。再看他们的《祈雨歌》,估计普天之下也仅独此一家:
龙王爷,请你哩,不过三天要雨哩。
厦上瓦儿晒红啦,屋檐骨朵火着啦。
锄田哥哥渴死啦,八十婆婆饿死啦。
金刀子,银刀子,下雨就在今早起。
金香炉,银香炉,下雨就在今晌午。
金柜桌,银柜桌,下雨就在今后晌。
金灯盏,银灯盏,下雨就在今黑间。
金板车,银板车,下雨就在今半夜。
一点一马勺,两点一池泊,三点一黄河。
下他个,七天八夜九后晌,第二早起再续上。
井水要和井口平,池泊不满你别停。
雨水能渗三尺地,我给你唱上三天戏。
龙王爷,你听着,你不下雨小心着,
拔你胡子扳你角,要你龙王做什么!
“拔你胡子扳你角,要你龙王做什么!”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图书出版、文学、论文专著、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出版、印刷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家风范文库·诗词十六家》
《大家风范文库·散文十六家》
征稿进行中
13325115197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