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早谢的花朵
——忆吕荧先生
张 杰

吕荧先生在抗战时期曾写文章,高度评价革命诗人艾青与田间,称赞他们为“人的花朵”。
我想,作为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美学家的吕荧先生难道不也是“人的花朵”吗?
然而,这枝盛开的花朵,却过早地凋谢了,飘零了,这是令人感到十分惋惜的!
一
我喜爱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我特别喜爱吕荧先生的译本,那美丽而隽永的诗行,曾经激动过我年轻的心灵。我敬仰吕荧先生!
我从朋友那里知道,吕荧先生不仅是一位翻译家,还是一位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是位学识渊博的教授,我希望能目睹一下他的风采。
1951年3月,我终于跨进了山东大学的门槛,有机会见到了吕荧先生。
当时,吕荧先生是我们中文系的主任,他还给我们讲授文艺学。我首次见到他是在文艺学的课堂上。
上课铃一响,吕荧先生缓缓地走上讲坛。他,消瘦的面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当时已是初春的天气了,他仍然是全副冬装。从那装束看,从那舒缓的动作看,他颇象位老者,但那时他实际上不过30多岁。他走上讲坛,不做自我介绍,也不说与讲课内容无关的话,打开讲稿,便开始讲课。
当时,我们这些青年人有一种偏见,总觉得凡是从延安来的,从老解放区来的老干部,经过锻炼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总比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高一些。
吕荧先生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然而他上课时开宗明义第一章却说了这样的话:文艺是战斗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工具!这使我们十分震惊,也十分佩服。他又说,革命不仅需要飞机大炮,也需要步枪手榴弹。就文艺来说,革命不仅需要长篇巨著,也需要犀利的杂文和短小优秀的诗歌。
这些观点,今天看来确是一些平凡的真理,然而,在当时,对初学文艺的青年来说却是何等新鲜啊!
吕荧先生的课,很像他的文章,观点新颖而深刻,逻辑严密,例证精当,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量。他一上讲坛就一直讲下去,课堂上静得只听到唰、唰、唰记笔记的声音。大家不愿漏下一句话,一个字。下课铃一响,他拿起备课本就走。这时,同学们才活动一下身体,因为一个小时的紧张记录也够疲劳了。
吕荧先生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和同学们也很少接触,他虽然身负系主任的重任,却似乎很少过问系行政的工作,或者他不热心于此道。在我的记忆里,他似乎很少或者没有以系主任的身份给我们讲过话。系里大量的思想政治与行政事务工作多由系里的其他领导和行政秘书去完成的。他是一位典型的教授、学者。
二
1951 年秋天,《文艺报》上发表了批评吕荧先生的文艺学教学脱离实际,有教条主义倾向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同学们很大的思想震动。但文艺学这门课到底应该怎么教,怎么学,大家都很惘然。
当时,山大的校长是华岗同志。华校长在山大的教职员工及广大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一向尊重爱护知识分子。我们听说,华校长曾劝吕荧先生作点自我批评就行了。但吕荧先生执意不肯,最后竞是拂袖而去。好在当时“左”得还不够厉害,还没有对吕荧先生进行“声讨”与“清算”。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吕荧先生。
我的同班同学李希凡在谈到这段令人难忘的往事时说:“······那时在文艺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教务主义的态度’ (当时整个学术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刚刚开始),而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观,还在占据讲台,继续传播。恰恰相反的是,能系统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教学,在当时的教师当中还是很少见的。因而,即使这样的教学,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缺点,它都应该是得到鼓励、扶植、支持和帮助,而不该是被批判的对象”。 “事情过去了32年,这场我们所独有的‘运动’,似乎也可以看清楚了,即它显然也反映了十七年文艺思潮中的‘左’的倾向,或者也可以叫做‘左’的倾向的萌芽”。(《回忆与悼念》)
我觉得希凡的这个分析是客观的,公允的,因而是令人信服的。
我还觉得,五十年代初期,我们的党风社会风气还算是比较好的,整个国家朝气蓬勃。然而,也不可否认,在某些方面,某些部门,甚至某些政策有“左”的倾向,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上就是这样,这是应该永远引以为戒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严肃认真地纠正了过去的许多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面的一些失误和教训,这是令人感奋的事。
三
那么,吕荧先生从山大出走以后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同学们以一种失落感议论他,记挂他。后来听说,他到了北京,到北京干什么,仍然不清楚。有时看到报刊上发表他的文章。后来又听说,1955 年在席卷全国的“反胡风”运动中,他受了牵连。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的联席扩大会议上,他在发言时提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 思想意识领域的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这个观点今天看来是个平凡的真理,然而,他却被当场赶下台,继而被隔离审查了一年之久。1957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美是什么》的论文,并加了编者按,大意是说吕荧只是受了胡风思想的影响但不是胡风分子,欢迎他参加美学的讨论等等,这是为他公开平反的信号。
但是,吕荧先生到底在北京哪个单位工作?后来情况怎么样?同学们见面谈起来,谁也说不清。粉碎“四人帮”以后,报刊上披露了他晚年的信息,然而,是个悲惨的信息:
原来,吕荧先生离开山大到北京以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只是由冯雪峰同志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聘请他为特约翻译员,每月酬金二百元,后来又减为一百元,有段时间,人民日报文艺部还聘请他为社外顾问。
吕荧先生的晚年十分凄凉,他不仅生活孤寂,而且在政治上十分坎坷。在十年浩劫期间,他被发配到农场进行监督劳动,去农场时还背着打字机和蜡烛,准备在那里写作。他也实在太天真了。在农场里,他受着人间难以容忍的屈辱,挨着饥饿,1969年3月5日,戴着老牌反革命分子和胡风骨干分子两顶帽子,屈死在农场里的一间阴湿的炕头上。当时,年仅 54岁!
四
关于吕荧先生的生平,我知道得很少,最近翻阅了有限的几份资料,仅知道:
他原名何佶,吕荧是他的笔名,意思是象荧火虫一样,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他是安徽省天长县人,1919 年生。他从中学时代起就爱好文学,开始散文与诗歌的写作。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进步文艺团体“浪花社”,创办文艺刊物《浪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七七“事变后,去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9年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复学,1941 年大学毕业后在四川任中学教师并从事写作。1944年出版了论文集《人的花朵》。1946年任贵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与友人创办《时代周报》,宣传民主,抨击独裁。1947 年到台湾师范学院任教。1949年4月到北京,同年7月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后到大连了解工人文艺运动情况,写成《关于工人文艺》一书。他对方兴未艾的工人文艺给予热情的支持和积极的肯定。1950 年到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主任等职。
从1958 年冬天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翻译员;从“反胡风”到“文革”都受到审查和迫害。1979年5月公安部为他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他的著译有:《人的花朵》、《关于工人文艺》、《艺术的理解》、《美学抒怀》、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列宁论作家》、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等约数百万字。
吕荧先生是位才华横溢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有突出成就的翻译家,著名的美学家。
他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他怀着满腔的悲愤,带着遍体鳞伤,默默地离开了人间!
吕荧先生是朵正在盛开的花,那罪恶的寒风却使他过早地调谢了,飘零了,这是令人感到十分惋借、十分悲哀的!
1990年4月11日初稿
2023年5月1日泉城定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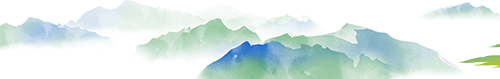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