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我的劳模之路(一)
邵祺昌
(1)难忘二中
自从1992年8月来到周村二中,到2011年10月退休,我在二中正式工作20年。退休之后,我一直是周村区关工委的五老志愿者,现在还是周村二中的关工委常务主任,算起来已经30余年了。只要我身体允许,还会继续干下去,因为二中给我的太多太多,不忍心和她挥手再见。
在90年代,老师们时兴从学校的锅炉房往家带热水,有个带挂钩的白铁水桶,放学的时候装满热水往自行车后座上一挂就回家做饭用了,很是方便。记得我在灌热水的时候说:“吃的是二中饭,喝的是二中水;生为二中人,死为二中鬼。”看来这句话,我要兑现了。
关于二中的话题,以前写了不少。如《我的学生我的儿》《我的学生我的爱》《我的学生我的天》等系列,还有《周村二中的大雪糕》《周村二中的兴华电器厂》《周村二中有个晨曦文学社》等文章。这里不再重复,就把在二中的有关生活琐事写一写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是1992年来周村二中的,1993年《周村报》上刊登了我的事迹,1994年被评为淄博市中小学模范班主任,1995年被授予淄博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短短三年,送了一届毕业班就获此殊荣,是不是有点早啊。当然荣誉不是白给的,劳模的称号不容玷污,从此我在劳模之路上昂首向前。
凡是读过书的人大概都知道司马迁写《史记》,但是知道司马迁因为写《史记》而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割掉命根子)的人却不多,我不想当司马迁第二,更谈不上忍辱负重。还有因为清初皇帝大兴文字狱,搞得汉族文人不敢触碰朝廷的红线而纷纷去考证秦汉唐宋或更早的历史,因而兴起了“考据学”。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可重蹈覆辙。
年龄在老化,记性逐渐衰退,忘性不断增长,二中当时的一些事已经记不准说不清,所以大是大非问题不敢妄论,但是生活琐事说来无妨。
其实,我写的《民办教师之路》看似鸡毛蒜皮,但是数年之后就是后人眼中的历史。同样今天写的二中生活琐事,也会成为后人研究二中的历史资料之一。但愿吧,仅此而已。
9月27日下午,我去二中参加活动,再一次审视了二中的校园。整洁的校容校貌,新建的教学楼,宽敞的操场,东西院墙上的铁篱笆,昔日拳头粗的小白杨已经成为参天大树……今非昔比,感慨万千。
30年,弹指一挥间。
(2)二中就是我的家
1992年暑假后来二中工作后,学校给我安排了住处。记得先是住在东院学生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学生宿舍里,和同时从王村镇中学调过来的张世海老师住在一起;不久又搬到东院实验楼一楼的一间门房里,和张辉老师住在一起。后来搬到紧挨着阶梯教室的一楼大教室里,我们五六个老师住在里面,其中有江鳴、傅道海、张世海等青年老师。
1993年,学校在东院宿舍楼西头加盖了一座三层小楼,其中二楼用于单身老师宿舍,其余一楼、三楼住高三学生,四人一间,算是照顾高三毕业班了。其实那是一座东楼,夏天的西晒日头,晚上很热,难以入睡;冬天很潮(无暖气),躺在床上冻得打“牙巴骨”,瑟瑟发抖,但是老师、学生都认为是享受了学校的照顾(现在这个小西楼早已拆除),很是满足。
在分配宿舍的时候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领导让我先挑,我就挑了最南边的一间。这间宿舍南边开个窗户,朝阳、明亮,只是那个铁楼梯,老师们来回上下楼咚咚作响,很不安静。起初我和闫永老师住在里面,后来和贺峰老师也住过。
直到1994年秋后,因为我送毕业班,周六、周日加班很少回家,向领导提出了带家属的申请,学校才给我在学生宿舍楼二楼安排了一间宿舍,算是有了稳定的宿舍。记得当时一楼、二楼共有12家老师住在这样的学生宿舍里(现在这栋宿舍楼早已闲置多年)。
有了属于自己的宿舍,种完小麦,我把老婆孩子接过来。我们夫妻俩和儿子住一起,女儿那时候在山东丝绸工业学校(当时叫丝校,现在是山东轻工职业学院)读中专,平时住在丝校里,偶尔过来就住在高三女生宿舍里。
记得搬家的那个周六下午,我让一名学生家长用大头车从家里把锅碗瓢勺等餐具和简单的被褥、还有一个液化气灶拉了过来。因为去的时候从周村蜂窝煤厂给我二哥捎了半车蜂窝煤,蜂窝煤厂的生产很慢,等了大半下午才算装完,所以回来时就昏天地黑了,司机也没吃饭就走了。本来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事情,结果耽误了人家整整一下午,真不好意思了,至今还觉得心中有愧。
虽然有了锅碗瓢勺,但是还缺少碗橱、面板、铁炉子等生活必需品。因为这一级的学生我都去家访过,所以对学生的家庭情况比较了解。凭着我的老师身份和家长的良好关系,我安排两名学生家长分别给我做了一块面板和一张小碗橱(免费,至今还用着)。小碗橱上边可以切菜,下面可以放碗筷,很是方便。液化气灶就放在门外的走廊里,随时用随时打火,就感觉进入了小康康时代。
冬天来临,我又让城区的一名学生家长给我焊制了一个铁炉子,从此我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现在想起来,多亏了领导和学生家长的支持,吃水不忘打井人,从心底里感激他们。
人心都是肉长的,有了领导和学生家长的全力支持,我只有用更好的教学成绩来报答他们。从此,我“为师如父爱生如子”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二中就是我的家,学生就是我的娃!
(3)雨雪上班路
在学校分给我宿舍前两年的时间里,我都是周六下午两节课以后回家,周日下午回来上晚自习,除非农忙季节,很少周一早晨回校。
那时候,我骑一辆破旧自行车上班,内胎容易被扎坏。在校时间坏了就去铸钢厂门口的修车点去修,在家里坏了就找哥哥或弟弟给修,反正我是不会补胎的。记得一次从家里要走的时候才发现需要补胎,正好哥哥弟弟都不在家,怎么办?只有自己动手补胎,折腾了半天,费了很大力气,总算是补胎成功!谢天谢地,没耽误了上班。
从我们王村镇大史村到周村二中,大约40里路,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除了从中央村到我们村有2里路的土路外,其余全是柏油路,算是路途平坦,但是摊上雨雪天,那可就麻烦了。
记得有一年夏秋之交,老天是瓢泼大雨,我披着杨古联中发的那件军用雨衣,冒雨回校。到了大临池一带,雷声大作,霎时变作倾盆大雨,实在是寸步难行,正好路边有一排建设中的房屋,就想进去先躲避一会儿再走。结果我前脚刚进屋,后脚就是一个炸雷,感觉那炸雷紧贴着我的后身滑了过去,惊吓之余就是后怕,如果我不进屋避雨,后果不堪设想。
大概是1993年的冬季吧,那年早早地下了一场冰雪,天特别冷,路特别滑。也是我从家里返校,别说骑车赶路,就是推车前行也容易摔倒。记得在平坦地方,我就战战兢兢地骑上自行车,直到摔倒为止。上下破路就推着前行,特别是下坡路,根本不敢骑车,唯恐连人带车栽了跟头。记不得一路摔了几次跟头,用了两个多小时总算到校了,但是浑身上下疼了好几天。
记得是我住小楼的那年国庆节,我骑车回家时顺便把用不着的蚊帐摘下来带回家。那是杨古联中老师们从广州邮寄买来的尼龙蚊帐,价值40元,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蔚蓝色,既密实,又透风,很时髦。我把蚊帐折了几折就顺手夹在了自行车后座上。由于是尼龙蚊帐,自然就蓬松着,我也没在意,就骑车往家里赶。大约在大临池一带,有个向我问路的,我就下车为人家指路,然后上车继续前行。走了几十米之后,感觉上车时用腿扫了蚊帐一下,就下意识地回头一看,才发现蚊帐丢了。向远处看,蚊帐就在公路中间,就赶紧骑车向回走,结果还没到,来了一辆汽车超过我去了,那辆汽车行到蚊帐处,司机停下车来捡起蚊帐就风驰电掣而去了,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的捡走了蚊帐,很无奈,后懊悔。
一辈子牢记父母的教诲:早起三光晚起三慌。我做事总是向前赶,不想拖后。即使农忙季节,周一我5点多钟从家里走,也得在学校升国旗仪式前赶回学校。看到有个别家住周村的老师总是耽误了升国旗,心里就很纳闷,为啥不能早来一会儿?
(4)我家的责任田
在没有农村教师补助费之前,农村的老师们都有个进城的梦想,我虽然借着淄博师专毕业分配和二中急需要高中历史老师的机会进了城,但是除了风雨雪天要赶班之外,家里4口人的责任田也成了我的一大难题。
那些年,妻子的间质性肺炎控制得不好,除了维持着一家人的吃饭穿衣之外,地里的活儿基本干不了。那时候还没实行双休,只有周天时间属于我自己的,农闲时好说,可是到了过秋过麦的时段,还真让我首尾难顾。记得我写过一篇《课堂·雨·麦场》的文章(附后),就是风雨中我人在课堂心里却惦记着麦场的亲身感受。记得那次下课时,我问学生“老师心里想的是什么?”学生们齐声回答:“麦子!”知我者,学生也!我含着泪花走出了教室。
记得那年秋天,我周六回家到地里一看,大豆熟过了火,白天根本没法收割,一割豆粒就爆落在地里了。没办法,我只好半夜里趁着有露水去割豆子。深更半夜,我一个人在漫天遍野的玉米地里(玉米与大豆间作)摸索着割豆子,顾不上担惊受怕。割了半宿明天了,正好四哥往他责任田运肥料,帮我把豆子捎回到我的小场院里。
还有一年,我把课程调了一下,和考勤员老师说请一天假回家忙着种麦子。可是到月底发考勤费的时候却扣了我30元。等到高三庆功会上,我委屈地和校长说了扣钱的事,校长说如果当时去找他可以不用扣钱,家在农村的高三老师有照顾。但是我不知道啊,那30元再也没有给我补上。
还有班里的胡斌同学在星期天的时候,从萌水骑自行车去帮我割麦子,下午连饭也没吃就饿着肚子回校上课去了,很是感激。那年,麦收是妻子生病最厉害的时候,看我一个人在地里割麦子,就强挺着身子去地里帮我割,但一上午也割不了十来米,还嫌我不让她回家。至今说起来这事来,老伴还埋怨我心太狠!
记得1996年麦收时节,我周日忙着上课没有回家。俗话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麦子熟了妻子急眼,就找亲戚们帮忙把小麦收割并连夜脱粒后,让妻侄用汽车把十几袋麦子拉到二中来了。我一看,来不及责怪妻子,就赶紧把小麦晒在有水泥地的篮球场上,下午装好袋子放到体育器械室里,第二天再搬出来晒。一连三天晒干了,就委托毕利群老师找朋友送到了周村面粉厂。面粉厂给了一个小本子,以后拿这个本子就可以去领面粉,几年后才吃完。
在校园里晒麦子,也只有我才能干得出来,校长也没怪我。但是这责任田我实在是没法种了,正好侄子结婚后生了孩子,就把我家的责任田转让给他了。从此,我终于不身在曹营心在汉了,可以安心教学了。
附录:课堂•雨•麦场
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
刚才还骄阳似火,半节课的功夫,那风……那雷……那雨……我那颗心……
三秋不如一麦忙,麦收季节,忙煞人。调到城里任教后,四十里路来回赶班,更是忙上加忙。妻子又常年患病,真是雪上加霜。
趁星期天的空儿,一个人,一把镰,一辆小土车,死拖硬拽地把一亩多地的小麦收到场里,连夜脱粒……白胖胖的麦粒摊满了场,才风风火火地赶回了学校,迈进了课堂……
震天响的雷吓得女生们捂住了耳朵,暴虐的风吹折了校园里的白杨树,发狂的雨越过走廊,钻过门窗,窜入教室……只听见,风,忽忽地响;只看见,雨,一片白茫茫……
透过四十里风和雨,借着雷火电光,我看见那体弱多病的妻子挣扎在麦场上,一个人,一个患病的女人,在和风神赛跑,在和雨公争抢……我的两眼模糊了……
风停了,雨住了,下课了。
我木然地走出了教室。
一场麦子不见了,只有妻子瘫倒在麦场上……(已收录《与共和国一块成长》)
(5)没有资格吃油条
我刚来二中的时候,习惯于周日从家里带煎饼来吃。1993年女儿考上山东丝绸工业学校(丝校)之后,妻子就给她打一些菜火烧带着,记得周天返校时,我们爷俩抢着从家里带火烧。但是吃完了从家里带来的煎饼、火烧,总得吃食堂。
食堂里的早饭有火烧、油条、馒头、玉米面稀饭。学生们大都是吃火烧或油条,而我坚持每天早晨一碗稀饭和一个馒头;中午饭除了两个馒头之外,不管是什么菜一般都是打两毛钱的。只有食堂里有蒸包(每周一次)的时候,我才舍得花6毛钱买3个蒸包。
记得食堂职工胡师傅和我聊起话来,问我早晨为什么不吃火烧和油条?我说家里有个病老婆和两个孩子,一家人指望我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我“没有资格吃油条”!胡师傅听了之后很是感慨,她没想到我家里竟如此困难。以后我再去食堂里打菜,总感觉胡师傅明里暗里地照顾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胡师傅的关照!
还有,我来到二中之后,由于女儿考上了丝校,王村的一些老乡亲就托我的关系来周村学美术考丝校。记得有两个学生中午来二中跟着我吃饭,我除了给他们买馒头之外,就是我们三个人打两份菜。两个学生都很懂事,从来也没有怨言。
那时候,我们办公室里老师们还有个“抓大头”小游戏,就是天气不好老师们中午不能回家吃饭的时候,就会用“抓大头”的办法来热闹一番。我们6个老师,事先写好白吃、跑腿、5毛、一块、两块等不同数额的条子,做好阄之后,一人拿着让老师们抓阄,抓着什么就是什么,然后按照抓到的钱数凑起来让跑腿的老师去买些瓜子或糖块来,老师们边吃边聊就度过了愉快的午休时间。但是这样的游戏我从来不参加,不管老师们怎么苦口婆心地劝说,我就是不参加,人家也拿我没办法,我自己去食堂吃饭。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自己的肠子有多长不用别人量。即使这块儿八毛的钱我也舍不得花,所以至今我也没有养成嗑瓜子的习惯。
直到1994年种上麦子以后,老婆孩子跟着我来二中住下了,才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不管吃好吃坏,回家总能吃上妻子做的热饭。儿子那时在丝绸路小学读三年级,偶尔早饭花买5毛钱给他买一个火烧,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坚决反对因爱面子、讲排场而大吃大喝造成的浪费。每逢看到酒桌上杯盘狼藉剩下很多菜,心里总是有一种犯罪感。俗话说吃了不疼瞎了疼,为了面子浪费饭菜就是对劳动者的最大不尊重!
(6)晚自习的烛光
90年代,不知啥原因,记得二中的晚自习时有停电。那时候,每天有三节晚自习(通校生上两节可以回家),不管上到那儿,只要一停电,学生们就跑出来在走廊里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甚至有的学生背着书包回家、回宿舍,即使又来电了,班里也往往是少了学生。
为了保证晚自习质量,确保学生的学习时间,只要停电,我就让学生们去校门口的小卖部买蜡烛,点亮蜡烛继续学习。一而再、再而三,学生们都习惯了,都买下蜡烛放在抽屉里,只要一停电,立即拿出蜡烛点亮继续学习,临时去买蜡烛的学生很少。所以不管是否停电,我们班的晚自习是照常上,这一点复读生刁爱玲同学体会最深刻,至今聊起来还忘不了点着蜡烛上自习的情景。
晚自习的烛光,照亮了学生的人生之路。
我老家在王村镇,所以每天都住在学校里,因为两节晚自习之后,看自习的老师就下班了,第三节晚自习我都会靠在班里,甚至一直陪着他们学到深夜11点多。10点钟晚自习结束后,10点半静校,传达员关大门。那时候,二中的宿舍区和教学区是两个院子,住校生回宿舍睡觉要从学校大门出去再进入宿舍区大门。只要超过了11点传达员熄了灯,就不好意思叫人家再起来开门了。这时候,学生们就要爬墙进入宿舍区,我这个班主任有时候也和学生们一块爬墙。
因为天天如此,不知道学生们咋样,我是感觉很疲劳。记得有一次早自习,课前我在班里后面的一个空位上坐着,等自习铃声响了,看早自习的张世海老师来了,我还不知道,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张老师见此状况和学生们说:“你们的班主任太累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要想学习好,就要刻苦努力,古代有头悬梁锥刺股和凿壁借光的故事。要想学习好,就要惜时如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如此三年下来,我班的同学就争取了不少的学习时间,学习成绩自然就提高。
习惯成自然。直到现在,我还是保持着早晨5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的习惯。从外面回到家,只要还有半小时的时间,我就会打开电脑写东西。一天三顿饭,都是妻子做好饭盛到桌子上喊我吃饭,我才拖拖拉拉不甘情愿地去吃饭。早饭10分钟,午饭半小时、晚饭10分钟,其余时间就坐在电脑前工作。争分夺秒、惜时如金,害怕哪一天一头栽倒,完不成自己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
(7)带钥匙的班主任
从小就知道一句俗语:小老婆带钥匙,当家不主事。可是我这个班主任既带钥匙又主事。
教室里的钥匙,大多数班级都是让班长拿着或者是值日组长轮流拿着。拿着教室钥匙就是一种责任,要早来开门,不能耽误了学生上课。但是学生就是学生,有时候睡过了头或者忘了就来晚了,所以经常看到上课铃响了,有的班的同学们还聚集在教室门口等着——拿钥匙的同学没来!或许三分钟五分钟,带钥匙的同学才姗姗来迟。
我们班教室的钥匙,除了学生带一把之外,我必须打一把,一是大权不能放,二是生怕学生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记得父母教导我们:“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因而一辈子我养成了凡事赶早的习惯,所以我们班的教室大多是我早来开门。不管是早晨、下午还是晚上,我开了门先从讲桌下面拿出板凳来坐在讲台上,学生来了看到老师在,自然就立即投入学习,很少有在班里打打闹闹的情况。一直到上课的老师来了,我才回办公室。别小看这课前几分钟,日积月累那就是一大把时间啊!
还有在安排值日生方面,一般是按学生座次的横排或竖列来划分值日组,而我是根据平时的观察,公布6名认真负责的值日组长,由值日组长自由组阁双向选择,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劳动积极性,也增强了集体意识。我们还实行值日组承包的办法,就是一组的值日生一干就是一周,包括周五的大扫除,也是落实到人。学校进行卫生评比的时候,哪个组丢了分拖了班里的后退自然是清清楚楚,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荣誉感。
细节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命运。一个学生是否成才,是否养成好的品格,都在这潜移默化的日常行为中。
事必亲躬,心系学生。记得有一次,班里的十来个学生组织起来利用星期天的时间要去萌山水库郊游(那时候还没有文昌湖旅游度假区)。虽然是高中生,但是我也不放心啊。周日早晨,我从王村镇老家骑自行车往萌山水库赶,可是刚刚到了小尚村,自行车就扎胎了。怎么办?看到公路边有一家修车铺,就推车过去让师傅修,可师傅手头上正忙着修另一辆车,还需一些时间。我等不得啊。就和师傅商量着,我骑着他的自行车先走,等下周六来换。因为都是邻村的,师傅见我实诚,竟然同意了。就这样,我骑着师傅的自行车,平生第一次从彭阳、道开村,一路打听着来到萌山水库,陪着同学们郊游。直到周六下午回家的时候,才到小尚村和修车师傅换过自行车来。
班主任工作,责任重大,安全工作更是重中之重。只有心系学生,把学生放在心上,才能做好班主任工作。
(8)囊括演讲比赛前三名
学校就是一个培养学生集体意识的场所,上过幼儿园和不上幼儿园由家长带大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在二中当班主任这些年,我带的班级不论是在体育、文艺等活动中还是在学生会组织方面,我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唯旗是夺,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记得是在1993年学校团委组织高二年级学生进行“一二·九”运动演讲比赛。每班可报1-3名学生参加,我们班就报了3名同学。我首先让学生自己写出演讲稿,然后经我修改后定稿。为了锻炼学生的能力和提升演讲水平,我利用课外活动时间至少在班里练习了两次,结果在正式的演讲比赛时,我们班的董娜、崔玲和李文同学分获全校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名。这一下可轰动了二中,都认为我这个班主任很专业,其实至今我也不会朗诵,只是把这次比赛当做大事来抓,督促学生多演练了几遍而已。自那以后,每年的朗诵或演讲比赛,我都理所当然的成为评委,以“专家”自居。
记得在每年的春节和秋季运动会上,我们班的学生也不甘落后,全能选手陈新、短跑健将袁训强等同学都是运动会上的风云人物。因为我没当过体育委员,所以对于体育项目几乎一窍不通,一切全由班长和体育委员安排,我乐意当个甩手掌柜。记得每届运动会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从来也没当过殿军。
我们二中还有老师们自由选报项目的教工运动会,记得在1992年的秋季运动会上我第一次参加二中的教工运动会,按年龄我报的是老年组100米跑,本来不擅长跑步的我比着校长年轻了10来岁,结果最后撞线的时候我紧跑了几步超过了校长,当时感到很亢奋。回到办公室之后,老师们教育我说你怎么能超过校长呢?我才恍然大悟。
二中的学生会组织也是由各班派出优秀学生参加学校的竞选,我都鼓励学生们去竞争。记得我们班的李文同学曾当选第三届学生会主席,下一级的宋慧琳同学也是学生会主席,98级的胡业镇同学也是学生会主席。其他级的同学是否是学生会主席我记不清了,但是学生会干部每次都少不了,记得孙新桥同学担任过学生会的体育部长。
那时候,省、市级优秀班干部在高考时还能加分,记得是省级加10分,市级加5分。由于我们班的同学平时表现比较好,所以在每届毕业班中,大多数时候我们班都能争取到省级或市级优秀班干部名额。得到荣誉的学生也很争气,都能考入理想的大学为学校争光,真正做到了学校提出的“今天我以二中为荣,明天二中以我为荣”。
(9)晨曦文学社有传承
我虽然不会文艺和体育,但是我喜欢写文章,经常把自己的生活小故事和人生感悟写出来贴在教室里让同学们看。每次贴出一篇文章,学生们都是先睹为快,有的干脆揭下来带到宿舍里去读。从这些小文章里,我看到了教育的契机,认为可以通过文学形式来教育学生,于是就产生了创办文学社的想法。
大概是从高一的下学期开始吧,我们班创立了周村二中有史以来第一个文学社——晨曦文学社。名字是班长、文学社社长李文起的,报头是美术老师吴承洲画的,画面是一轮光芒四射的朝阳,金光闪闪,朝气蓬勃。每期更换的时候只换内容,不换报头。
有了文学社,我就发动学生们投稿。学生们写出文稿后,再由我批改润色,并用方格稿纸抄写好张贴在宣传板上,最后用毛笔蘸着红、蓝色墨水勾出花边,周一早晨放到学校门厅一侧,老师们学生们就会抢着看,影响很好,受到师生们称赞。
晨曦文学社不仅给我们班增光添彩,也使学生们的写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有的学生的作品还被《中学生报》刊用,并且还有三元两元的稿费,每次领到稿费都很高兴。记得我们的晨曦文学社还和淄博十九中的绿豌豆文学社、淄博六中的绿野文学社进行联络交流,相互推动,共同进步。这个文学社到了高三就停办了,大约刊出10多期作品。
退休之后,我担任周村二中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在一次活动中,我和王校长聊起了晨曦文学社的故事,王校长很感兴趣,决定复建晨曦文学社。2021年4月28日,周村村二中新的晨曦文学社成立仪式在周村二中会议室举行,我和我的学生晨曦文学社老会员袁训强应邀出席了仪式,王校长,袁训强、文学社指导教师、新社员先后讲话。记得袁训强的讲话很有味道,他说:“祝贺周村二中晨曦文学社再次成立,这是一粒文学种子的再次萌芽,这是一棵文学大树的再度开花。”他希望:“把大家心底里文学的种子唤醒,一粒种子是一棵大树,一棵棵大树就是一片森林。”他说:“把情感用文字宣泄,必定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若此,文字也就不再是诗辞,不再是散文、小说,而是一种智慧、一种生活、一份美好!”
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传承中持续发展的,希望周村村二中晨曦文学社的同学们能够在写作中成长,得到快乐,把晨曦文学社越办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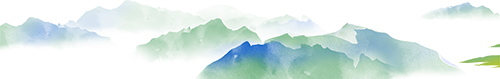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