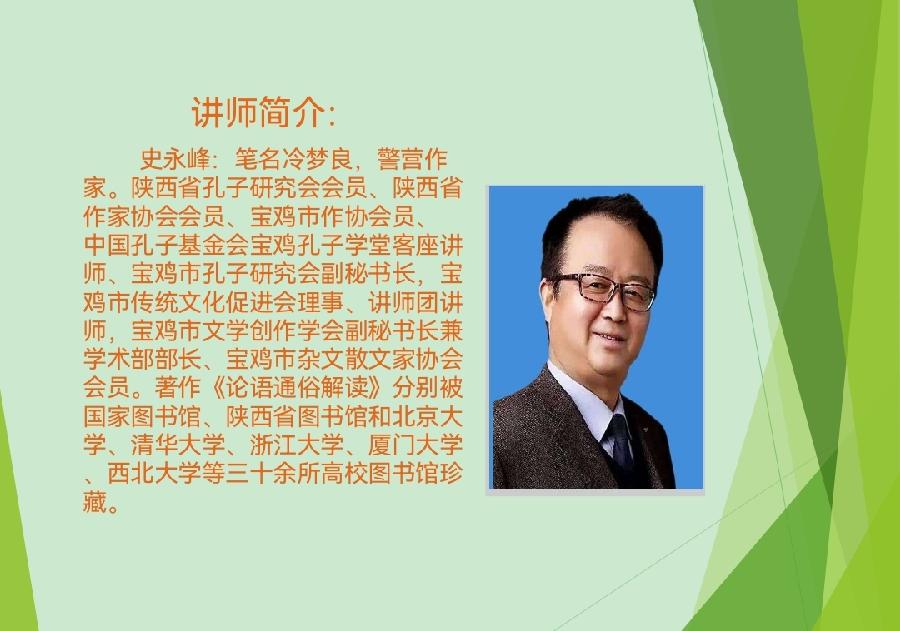第十四篇 宪 问(5)
第十四篇 宪 问(5)
人贵自知
【原文14·10】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贫”与“富”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贫”既指物质财富上的不足,也指事业与精神上的欠缺,社会地位不尽如意也为贫。同样,“富”也包涵物质财富上的富有和事业精神上的满足。孔子这句话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人在贫困不得志时能做到心无怨恨、达观淡定是很难的,相对而言,在富贵时做到不骄傲到容易一些。
为什么人会“贫而无怨难”?因为人都有欲望,不但希望自己物质上富有,而且能有所作为获得一定的身份地位,但却很少有人能客观全面的认识自己的学识与才智,评价自己的身份价值,找准合适的社会位置,这就是人的自负。所以,当人的欲望难以满足时,很难反省自己,往往把原因归咎于时运不济、怀才不遇而怨天尤人,甚至会自暴自弃,很难做到面对现实,达观淡定。这就是说,人,要客观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克服盲目自负的性格弱点。唯如此,才能抛却不切实际的幻想,安贫乐道,使自己生活得达观自如——这同样是君子的修养。有人批评“安贫乐道、知足常乐”是不思进取的消极生活态度,其实是歪曲了儒家学说的本意。“安贫乐道”强调的是克服个人对生活的欲望,这与儒家一贯所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鼓舞人树立远大志向和奋斗精神的观念并不矛盾,不可以偏概全而混淆。
接下来的一章,就以孟公绰为例,说明人贵自知:
【原文14·11】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鲁国从宣公起,公室日渐衰微,朝政由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操纵把持。“三桓”即孟氏、叔孙氏和季氏,他们是鲁桓公庶长子庆父(孟)(嫡长子同即鲁庄公)、三子牙(叔)和四子友(季)的后代,公室贵族。孟公绰就是孟氏后代中的人。当时,三桓强势,架空了公室,但孟公绰却廉正低调,没有政治野心,表现得清心寡欲,很受孔子敬重。
在这一章,孔子说孟公绰要是做晋国赵氏、魏氏两大家的家臣老大,那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不能去做象滕国、薛国这种小国的做大夫。为什么呢?朱熹的解释是,其虽然廉静寡欲,有好品德,但短于才智,所以难以胜任。果真如此吗?愚以为,不尽其然。
关于孟公绰的生平事迹史料上记录很少,有无真才实学难见分晓,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是二十五年春,齐国崔杼以报鲁国孟孝伯二十四年帮助晋国攻打齐国之仇为名,举兵侵犯鲁国北部边界,鲁襄公很着急害怕,就派使者向晋国告急求救。孟公绰却说,崔杼正在谋划一件大事,并没有把鲁国当作心头大患放在心上,很快就会撤兵,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并说,齐兵这次到了边界后,没有掠夺,对百姓也不残酷,意欲争取民心,这和以往的做法不一样,足以证明其在国内必有重大政治动作,侵扰鲁国,不过一个政治幌子罢了。结果,正如孟公绰所言,崔杼在鲁国边界虚晃一枪,很快就撤兵了,不久就在其国内发动政变,杀了齐庄公,扶其弟齐景公上台。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孟公绰是有智慧和眼光的,并非是有德而才欠之人。更何况,人的才智是多方面的,只有在适合于自己的领域才能显现出来而有所作为,仅凭孔子此段话就说孟公绰短于才智,似乎偏颇,肯定不是孔子的本意。
至于孟公绰是否离开过鲁国到晋国做过赵氏或魏氏的家臣,或者到滕国或薛国做过大夫,史无记载,我想,大概没有。可能是赵、巍两家和滕、薛两国慕孟公绰之名,有意请之,才引孔子发出了这一段议论吧?总之,其绝非所谓有德短才之人,否则,德何以彰显?充其量是个好人,何以受孔子敬重?
其实,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以孟公绰的道德才智和性格,若去做象晋国赵、魏这样的大家里的家臣,在家臣中做个德高望重的首脑,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当个高级参谋、顾问,那是绰绰有余的,却不适合做即使象滕、薛这样的小国大夫,主政一方。原因是,其可能是个战略家却不一定就是战术家,可能是智囊型人物,却不一定就是个实干家,等等,这是由才智和性格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并非简单的才足才欠能述清的。孔子以孟公绰为例,其目的就是强调人贵自知的道理。当然,也同时告诉我们,对于人才,要量才使用,方可人尽其才,这也是用人难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