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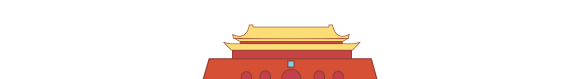

李铁匠的敲锤声
文/侯家赋
“叮叮”、“当当”……,一阵阵错落有致、欢快悦耳的锤子敲打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梦中又听到了久违了的当年李铁匠打铁时的敲打声。
眼下,“三秋”大忙季节又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忙“三秋”用得最多的工具就是犁、耙、镢、铣等农具。可这些农机具的修理、打造、淬火,可离不开走村串乡的“小炉匠”。
记得有一首儿歌是这样唱的:“三秋里分外忙,社员盼望李铁匠。铁匠来了修犁耙,大镢铁锨要加钢。修好家什忙三秋,省劲省力喜洋洋”。
我家的门外是一片空场,空场的东南角有一棵大榆树。榆树枝繁叶茂,像一把巨伞,能够遮阳蔽日,还能遮挡零星小雨,形成了一个“天然凉棚”,很适合铁匠在那里“安营扎寨”。每年秋季到来之际,那里就是李铁匠理想的支炉、生火、锻打之地。
李铁匠是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那可是远近闻名的铁匠之乡,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祖传了五代的铁匠手艺。他那张黑黝黝、带着古铜色的脸上衬托着一双不大的眼睛,却犀利有神,透着刚毅,一双沾满煤灰的双手,露着暴突的青筋,让人一看就是一位能工巧匠。他还带有一位徒弟,年龄也就是十八九岁,专门给他拉风箱、抡大锤,稚嫩的脸上被沾满炭黑的双手抓的露出道道黑印,两只胳膊凸显出核桃般大小的肌肉疙瘩,让人一看就是抡大锤、拉风箱锻炼而成的,他胸前还挂着一张油布做成的围裙,是防备打铁时火星会烫伤皮肤而特意穿戴的。
正当每年秋季人们盼望铁匠的时候,李铁匠将会如期而至。他们师徒俩首先在空场的榆树下,支好用一个三脚架支撑的铁砧子,再从地排车上卸下打铁用的风箱、钳子、大锤。然后,徒弟忙着生炉点火,师傅则一手拿着一把扁锤,一手拿着一把小锤,敲了起来。那错落有致、和谐悦耳的锤声立刻传遍全村的山川旷野、家家户户。
听到李铁匠的锤声,社员们纷纷从各自的家里拿来铁锨、大镢、锄头、镰刀等需要加工、淬火的农具,来到大树下,争先恐后的让铁匠先给自己加工。生产队里则需要修理耙丁、犁铧等中型农机具。只见李铁匠手握铁钳,把一件件农具放进炉火里,然后有铁铲在农具的上面培上几铲煤,徒弟用力拉着风箱,火炉里顿时穿起道道火光。阳光透过树枝,飘洒在炉面、铁砧上,如落下的道道瀑布,反衬着耀眼的火光。等放进炉火里的农具快要烧红了,李铁匠会眯缝着眼,看看火候和农具被烧的程度,然后把烧红的铁块用钳子夹起,安放在铁砧上,用小锤敲打一下,小铁匠很快停下风箱,抡起大锤,跟着师傅落在小锤击打的地方,李铁匠敲一下铁砧,小铁匠心领神会地在铁块原处再打一锤。小锤叮叮,大锤当当,弧线变幻,串起一朵朵耀眼的铁花,向四周乱窜。铁坯由红变黑,李铁匠的小锤在铁砧上连敲了几下,锻打停下来。李铁匠再把铁坯放入火炉,随手添一铲炭,小铁匠又呼呼地拉起了风箱,火苗再次蹿起,映的二人脸上一片红光。活路多了、时间长了,二人干脆把上衣脱掉,赤着膀子干活,胸前只扎着块遮挡火星的围裙。
需要进行修理、加工农具的人们忙着挨号排队修理工具,没有工具修理的大人和孩子,则围在铁匠的炉子周围看热闹。只见那一块块铁坯,经过烈火一次次的烧炼和锤子的锻打,一件件器物锻造成型。李铁匠左手握着一把火钳,右手用锤子敲打着烧红了的铁块和砧子。刚从炉中取出的铁块,浑身被烧得通红通红,还滴答着一滴滴火红滚烫的铁水。随着师徒二人配合默契的锤子下落,顿时火花四溅,把围观的大人和孩子惊得四处躲闪。坚硬的铁块,在他们手里,好似揉面团一样。经过几遍的反复烘烧、敲打,各种农具的雏形已经形成。等雏形成型后,李铁匠便把它浸入水槽淬火,一股股白烟霎时弥漫在空中,铁器还发出“嗞啦啦”的声音,李铁匠好似忙碌在云山雾罩之中。最后,李铁匠再次进行最后细致的锻打、打磨,没有丝毫的怠慢。经过火与水的锻炼砥砺,还融入了手艺人的智慧和感情,原来灰头土脸的粗铁器,随之出落得婀娜多姿。镰刀成了一弯新月,铁锨闪着寒光,锄头板上拱成半个圆弧,镢刃变得又薄又快……总之,每一件铁器的弧度、线条、厚度都体现着实用、精巧的匠心和工艺。
李 铁匠师徒二人吃饭、喝水是很不讲究的。做饭时,他们师徒俩就在炉火上放上一口4印的耳锅,徒弟淘些小米放在锅里,用烧铁的炉火加温,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米饭做熟了,师徒二人有时席地而坐,有时则则用支起的铁砧子当饭桌。烧水则是用一把大铁皮壶装满水,放在炉子上面烧,每人一把大搪瓷茶缸,口渴时,就随时喝上几口。徒弟因为整天抡大锤、拉风箱,饭量很大,一顿能吃四五碗米饭。吃菜更是简易单调,有时到集上买上二斤猪肉,炼炼油,和茄子、白菜、萝卜放在一起,就是一顿菜。看着师徒二人勤苦而恬淡的生活,围观的社员们不时地发出不同的议论声。
夜晚,李铁匠为了不耽误社员们用工具,就加班加点修理工具。熊熊的炉火把整个空场照得通红通红,溅起的火花,和天上的星星交相映辉。清脆的“叮叮当当”的锤子敲打声,更是响彻在乡村的原野上空,传得很远、很远……
李铁匠人缘挺好,特别是和我爷爷关系更非同一般。他管我爷爷叫大叔。每年的春天和秋天,李铁匠要来时,我爷爷就搓好三四斤旱烟叶,装到一个布袋里,让李铁匠来了吸烟。我父亲是教师,就把学生考试用过的卷子,拿给李铁匠卷烟用,每次都拿好多好多,够李铁匠用好几个月的。有时到了夜晚,我爷爷还邀请李铁匠到我家吃顿饭。爷俩一边喝着小酒,一遍拉着家常,形同亲生父子一样,关系融洽。李铁匠也是知恩图报的人,他每次来时,都给我爷爷带点章丘特产。我家的锄镰撅锨,都是他免费送给我爷爷的。至今我家的老屋子里还放着一张李铁匠送给我爷爷的大撅。
李铁匠每年要在我们村待上三、五天。等到家家户户社员们的的工具修理、加工的差不多了,李铁匠就开始收摊,再到别的村庄继续生炉、干活。临走时,他会把整个场地打扫的一干二净,场地上散落的铁屑,他送给有治腰疼、腿疼的社员,或者是养铁树的人家,煤渣清理后则倒进沟里。最后,他再在铁砧子和扁锤上空敲几下,作为向乡亲们告别的回礼。
听铁匠的敲锤声是一种音乐的享受,更是一种乡愁。如今,农业的耕种都实现了机械化,原始的锄、镰、镢、铣已经排不上了用场,加工、修理农具的铁匠的手艺也无人从事,铁匠的敲锤声也渐行渐远。但儿时李铁匠的打铁时敲打的“叮叮当当”锤声,永远是我记忆中的定格。

作者简介:
侯家赋,男,现年66岁,大专文化,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人,退休干部,中共党员。现为平阴县老干部联络员,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协会会员。
第八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入选作品会择优在《品诗》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芙蓉国文汇》一书。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八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0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2篇以内 微小说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