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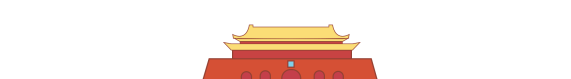

寒冬
文/黄益
还未入壬寅年时,冬便初见了影子,江南宋城的冬却是不似北方的雪来的纷纷扬扬,记忆中的冬时而阳光和煦温暖,时而小雨湿寒不断,在爆竹声中,沾染了极多的烟火气,寒冬中却也有着各自的相聚与喜庆。一月初归乡后,雨水倒是一年一岁地如约而至,也冷得刺骨,路边桃树干瘦乌黑的枝丫稀稀拉拉地向四周伸开,也是在等待度过这一场寒,每年的欢庆却也因为冬精灵到来的凛冽,给人更有了安放在记忆深处的情意。
在家挨了几天的雨声后,按捺不住便动身前往祖父家中长住了,一个面朝蓉江的小村子。许多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天边灰蒙蒙的雾总是遮挡着,每日都是昏昏暗暗的。凌晨只有一些些亮光的时候,我总是能听到一些声音,比如最先开始的总是灶前传来的轻微的盆和盘子相互碰撞的声音,哐啷哐啷的,还有下了一夜的雨后,从树叶上滑落下来滴在门前水泥板上的滴答声,水鞋在地板上行走而发出的拖拉声,这里和外头是不一样的。我裹紧了袄,走到门前,不停得在兜里搓着手,冷气从脖子领里一股一股的进,感觉全身都被提拉起来了,直冲脑门,听老人们讲,今年的冬天和零八年那场大雪有的一比,只不过今年寒的是这场不断的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原先老房子隔壁那家姓李的老人,也没能熬过这一年的冬天,前两天在祠堂办了法事,这场水席在年前办的是恰巧,正逢上春运日子,在外工作的人们归家,村里大多数都是年迈的老人,还有些在较远一点镇上念初中的学生也住在这里,加上最近几年,许多年轻人都已经回来了工作,说是村里在致力于减少留守儿童和老人的问题,也同时在帮助年轻人工作问题,因此来吃席的人便也比往常多了许多。
因早去了些时候,便刚好碰上跪送礼,边上坐着一群敲锣吹唢呐的人,一人负责吆喝的站在前头,余下的一些便是李家的子孙,身上披着一条白帽子的白布披风,腰间用腰带束着,由最年长的儿子的人领着跪拜,除了吆喝声,身旁的人都没了话语,连那正是调皮年纪的小孙子,也紧跟在父母身后,不知是冻得还是拽得紧的缘故,一双小手通红,抓着着他母亲的衣角,磕磕绊绊的,嘴里直哈白气。大约是雨一直没能停,直到开席,气氛才缓和了些,他家的人早已脱下了那身白布,正正的在门口迎着来往的宾客,天空上云层压得极低,水席上空用一大片塑料薄纸用来挡着小雨,在摇晃中渐渐扬起了边角,却是一片交谈欢笑声。
天气一寒,便总想着往人多的地方凑,雨稍微一停,镇上一条从头到尾的小商铺便开始大声吆喝,往日这种时候,我大概是最不愿意来的,没得看头,又闲着无聊,祖母同那些卖东西的妇人们总是爱唠嗑几句,谁家的孩子读书怎么样,谁家的萝卜个头最大,坐在人家店里头,烤着火,听得我直犯困,从街头唠嗑到尾,唠一天下来也不为过。由于街道整治,比往日整齐了许多,小摊子归在一个地,店铺也安上了玻璃制门,皆装上了制暖的,从最靠石桥边的店铺到街尾,为彰显喜庆,不止是卖年画的铺子亮起了灯笼,连卖喜果子的门口都挂了几个通红的大中国结,祖母叮嘱我去买些自个爱吃的,我嫌的这些麻烦,便顺手提着袋子。我们走在街边右侧,最为熟悉的就是用一把红色大棚伞,伞沿上挂着一幅幅写好的示例春联,将整把伞围了起来,最外层罩了一层防水的塑料布,像冰糖葫芦的烧糖,甜甜腻腻的,看了也甚是觉得喜庆,像是一个红屋子,要是下点雪或许就更加有意境了,红配白便是新年了。伞中间里头设了一张大桌子,桌上都是一块块红纸,一群人围得水泄不通的,更有出来张罗的,却嫌外头不如家中暖和,往人多的地方凑,便手中抓着一把瓜子,探着个脑袋往里面瞅,竖起耳朵听里头,这幅字应不应景,也要和旁边提着菜来凑热闹的人说上几句,“今年做几碗菜”,亦或是“家中豆腐做得老了或是嫩了”。这条街还未过半,天色就已经要开始暗下来了,街上的装饰灯笼也一个个开了,人又渐渐多了起来,但大多都是些年轻人,老话说的日落而息,到现在却成了晚上出门,夜市的文化也在小村里生根了,街上弥漫着烤串的香味,窜起来的火苗像是活了一般,一飘一闪的,像是给黑夜蒙上了一层橙红色的纱。顺着走下去,便能看见好几家粉面店,来一碗二两热滚滚的抄手,加上一勺油辣子,一勺醋,像是一片澄澈的湖面,刚刚融化,还带有些寒气,被天边落日的余辉染红,顿时带来的便是习习的暖意,便最是提精神了,一个又一个的抄手在汤中翻滚,露出白肚皮,染上一层橙色的外衣,更加有了滋味。逛到街尾便有广场,广场上许多人在跳着舞,一排又一排,整整齐齐的,一群孩子聚在一起,尖叫着追逐。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只有一盏大灯在旁边屋檐上,光透过黑夜里,薄薄的微雨似的,直直的照射在旁边的石桌石凳上,布满了小水滴,一颗颗显得亮晶晶的,在黑夜里显得弥足珍贵,透亮纯净的。穿过这些店铺后,便能进到专门摆摊的地方了,他们大多数都是用竹子编制的背篓和筐子,更为大一些的地方,就是用竹子编的铺上去,形成一个平台,边上用木板围着,里头的柑橘和苹果摞成一座小山,暖黄色的灯光下,像是一个小灯笼,散发着喜庆,叶子的加持更是给嫩添上了一笔,梨子的黄更是在夜中,有着月亮似的淡雅的美感,冬风微微起时,更是给来往的人冻红的脸,增加了一点俏。
这年一过,年味也渐渐散去了,凉飕飕的时候更没有热热闹闹的欢庆年,便也只剩下干巴巴的冻。这下了一个多月的雨了,天公仿佛是故意一般,始终没能放晴,那种坐在庭院里的躺椅上,沐浴着冬日暖阳的想法也落空了,我要回家准备去外地读书,母亲已经来电话催促多次了,祖母给我收拾收拾,叮嘱我戴上那双绒毛手套,便准备回去了。
老人家说什么也要送我过车站去。门前原先是一条窄小泥巴路,路中凹陷不平,有各种车轮子经过后遗留下来的车轱辘印,还有被溅起来的的泥水,将路边屋檐下的石板布满泥点,而两旁伸展出来的美人蕉却在风中生长的鲜活自在,也许有着雨水的冲洗,蕉叶格外纯净的翠。日复一日的,现如今这些都只存活在了记忆里,现今只有一条宽阔的灰白水泥路从一户户的人家中穿过,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没有泥水浸没的冰凉,只有从远处吹来无声的风。那天归家,祖父嘴上叼着烟,嘴上嘟嘟囔囔地絮叨着,双手背在身后,却怎么也立不起腰,左脚踏出去,身体也随着左偏,身影一左一右的,嘴唇上烟头的烟气熏得他眯起了眼睛,我有时经常怀疑他到底能不能看得清,我便总想着伸手去扶着他,他总是笑着摇头,头顶的帽子上面的毛飘飘扬扬的,似乎在格外努力的在寒风中颤抖,想要留在他的头顶,等到车子发动走了,他们在来来往往的人里逐渐消失,再没了痕迹,一片雾蒙蒙当中,我只看见了那顶结着水珠的帽子。
回来没有多少天,睡到半夜,听见雨又淅淅沥沥得下了起来,忽急促、忽缓慢、忽刺耳、忽轻缓,不得起床关了窗子,外头的风微微的呼呼声,隐隐约约好似还能听到不远的唢呐吆喝声,不知道这一个寒冬,是否能预知来年春天的光景。

作者简介:
黄益,一名学习影视文学方向的文字爱好者,尤其偏爱朱自清的散文,更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的流水账,从中挖掘一些细腻的情感。
第八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入选作品会择优在《品诗》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芙蓉国文汇》一书。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八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0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2篇以内
微小说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
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到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