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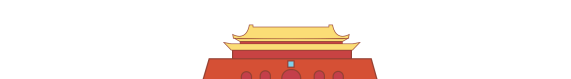

梦里故人归
文/慕之
昏黄的灯光泼洒在爷爷灰白的面庞,阴影描摹出每一条皱纹蜿蜒的形状。爷爷的眼紧紧闭着,眉间僵硬发灰的皮肤依旧保持紧皱的模样。他还有什么遗憾吗?她几乎快要认不出他来。他的身体异常瘦小,就像一块被烈日晒干的海绵。全身干枯斑驳的皮肤绷紧了用力地贴近细长的骨骼,似乎想用这样的方式挽留他的灵魂。爷爷的身上隐约传来血肉腐败的气味,不知是久未挪动所生的背疮腐烂的气味,还是可怖的癌症使他从内部腐坏了。
她没能见爷爷最后一面。这突然的噩耗使她的思维有些混沌,在悲戚的哀哭声中,她无法遏制地想起爷爷生前鲜活的样子。
年轻时,爷爷亲手用一框框红石与一担担青瓦砌成了一间可供全家八口人栖息的土屋,他粗粝的双手抚摸过老屋每一块苍老的岩石。老屋的前门正对着一片繁茂的田野,屋后是一座生长茅草和红浆果的小山包。白天,爷爷的鸡散养在这里,黄昏时分,鸡们就扭着身子不紧不慢地走进老屋休息。老屋里的空气常年湿润清新,弥漫着植物和泥土淡绿的馨香。她出生时,爷爷的鬓角飞白,腰背弯曲,已经不能再干农活。但老屋中的农具并没有荒废,屋旁种上了芬芳的紫苏薄荷,还有一排鲜红的凤仙花。每隔一段时间,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爷爷会穿上单薄的白布背心,坐在高高的青石门槛上打磨镰刀和耙锄。爷爷裸露出肌肉萎缩的细瘦手臂,那长着大点褐色老人斑的蜡黄皮肤耷拉下来,已经有了许多褶皱。爷爷一会儿喘着气磨得很快,一会儿磨得很慢,一会儿又停下来,眯起眼对着明亮的阳光久久地细看镰刀锋利的刀口。那时她还不懂,如今想来,爷爷或许是在追忆青春的峥嵘。
在她小学一年级的某个日子,奶奶突然借邻居家的电话给做医生的大伯打了电话。爷爷这几天连续发着低烧,并且感到肾脏有些疼痛,尿液竟然变成了血红色。叔伯们马上把爷爷带到省医院检查,几天后,结果下来了——癌症。爷爷那年已年逾古稀,医院建议保守治疗。爷爷并不愿留在医院,大半辈子连重话都不曾说过的他罕见地冲大伯发了大火。
“我不回家,还能到哪去!”
爷爷逼着他们让他回老家。
“人哪,落叶归根啊!”
他在医院绝食了三天,滴水未进。医生无奈,只能为他输液维持生命。到了第三天傍晚,叔伯被他磨得没办法,只好保证明天就带他回老家,爷爷这才喝了一小碗米粥。
爷爷果然回到老家去。她没感觉爷爷与以前有什么不同。爷爷依旧清晨便从那张黑漆斑驳的老木床上起来,洗漱时依旧顺便用煤炉烧上一壶开水。爷爷依旧饲养他的小鸡,依旧坐在前厅散发竹子清香的躺椅上读书,依旧挑一个太阳高挂的下午磨磨镰刀与耙锄。唯一不同的是,爷爷突然变得更爱散步串门了。爷爷常在周六的清晨步行三四里地到村镇交界的集市赶集,偶尔买些往常舍不得买的新奇小物件——磨豆子的青色小石磨啦,钢制的小锄头啦,常常给她带一小袋麦芽糖子或是核桃柿子之类的小零食。就是平时,吃完晚饭后,爷爷也常常拄起一根红漆剥落的硬木拐杖,慢悠悠地在田埂上漫步,有时遇到还在田间劳作或是聊天的村里人,便亲热地打声招呼。清晨,爷爷偶尔会顺着田间小道往山上走去,迈过层层叠叠的梯田,越过高低起伏的丘陵,爷爷从不用别人搀扶,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七十年,虽然眼睛已经浑浊迷蒙,但山中每一条奔腾的溪流,每一块长满青苔的岩石,每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都牢牢地生长在他的记忆里,恒久不变。走到小山山顶那块平整土地的时候,爷爷停下来,他的眼睛看不清,他的耳朵听不见,但他的灵魂端详着这片土地,这是他为自己选定的归处。他的孩子们说,这里正好能看见他们的老屋,他很满意。虽然他早已看不清老屋的模样,但他能想象出从这块土地鸟瞰是什么样的景象。他很满意。
半年后再去复查,这癌来得惊心,却竟仓促的痊愈了。好的结果令人欢欣,但爷爷的生活自然平静,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
那之后的几年里,老家镇上新建了一家造纸厂,老家的许多田地也被农业公司承包了。工厂生产起来后,看不出颜色的污水汹涌澎湃,如怪兽一般嘶吼着闯入溪流。山中的水流不再那么清澈,小鱼小虾和螃蟹渐渐消失,山间的小溪池塘臭烘烘的,水底常常飘着黏糊糊鸡屎一样黄色绿色的藻荇。土地被承包以后,每到春夏种植庄稼和青菜的时节,总能闻到田野里飘来浓郁的呛嗓子的甜腻农药味。喜爱在水田的淤泥里打洞嘻戏的泥鳅黄鳝不见了踪影,虫鸟少了,连青蛙也变得罕见,田野渐渐死一般的寂静。
爷爷的儿女们散布在天南海北,各行各业,他们过年时都要聚在老家吃团圆饭。她清楚的记得,那年是他们回老家的最后一年。他们在田野里走了一圈,大伯看着山中的水,无奈地摇了摇头。爸爸也皱起眉毛,大概在心里咒骂。他们在散发着霉味鸡屎味的老屋里头碰头地商量了一阵,爷爷奶奶就这样在那一年开春搬到了城里。
爷爷想念他的老屋,他年轻时亲手砌起红褐的石墙,他粗糙如砂砾的手抚摸过老屋每一块苍老的岩石。她看出爷爷在光怪陆离的嘈杂都市无所适从。爷爷习惯的木板床变成了柔软的席梦思,家里不需要他再早起烧炉子烧水,再没有那些叽叽喳喳的小生灵与他作伴,家里没有土地,不见了镰刀与耙锄。楼房的住户互不相识,爷爷甚至无法在晚饭时端着碗到邻居家聊聊天。爷爷只能拄着拐杖坐电梯下楼,在楼下嘈杂的小公园里缓慢踱步。爷爷在踱步中想念他的家乡,想起他年轻时候种下的李树,现在枝头应该已经挂满细小的白花了吧?再过几个月,到满山树叶在第一缕秋风到来前炫耀它的繁茂时,小小的青色脆李便被采摘下来,装进水桶里沉进冰凉的井水,只待晚上一家人在庭院里聊天时享用。爷爷想起他年轻时耕种的肥沃土地,他会把家中所有人的粪便收集起来,发酵了用扁担担去山上的菜地施肥。他是种地的好手,所有在他田中生长出来的菜蔬都多产而肥嫩。他用一畦一畦的菜苗稻谷与养得健康肥美的猪养活了全家八口人。
爷爷想念他的老屋,他年轻时亲手砌起的红褐的石墙,他粗糙如砂砾的手抚摸过的每一块苍老的岩石,每一片平整的青瓦。爷爷想念他的老屋,可是他再也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了。
爷爷的癌症在他九十一岁的春节突然复发,这次,他没能挺过这年暑假。
谁又能断言,爷爷癌症的复发与他身体和灵魂故乡的长久断联毫无关系呢?
爷爷瘫痪前搬到了离老家最近的叔叔家里,与老家同在一个镇上,离那儿只有半小时车程。那时她才了解到,老家的年轻人常常生病,于是早早搬离了村庄,现在老家只有几户年老的老人还在居住,村庄已经变为名副其实的荒村。叔叔告诉她,造纸厂已经被查封,逮捕了一批贪污官员。农业公司还没有撤走,仍然偷偷地违规施用农药。这些年镇上患癌人数渐渐增加,他的工厂里去年就有两名工人确诊癌症和肿瘤。这里的很多工厂主和他一样,觉得这里污染太严重,后劲不足,已经决定迁厂了。
楼下打棺材的木匠已经开始工作,钉钉子的当当声拉回她的思绪。叔伯们本想将爷爷的棺材停回老屋,可是他们回到老家只闻到了扑鼻的土腥和水臭。好在爷爷的坟墓已经建造好,就在爷爷生前停留的那座小山上,从墓地上鸟瞰,爷爷就能见到被农田和小山包裹住的他的老屋。
可惜,爷爷再也回不到那个洁净芬芳的老家了。
夜晚,他们在棺材前点上两支白蜡烛,她坐在桌旁小凳上给爷爷守灵。夜深了,她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的感觉自己变得轻盈,好像要飘起来一样。恍惚间,她听见田野里鸟兽青蛙的声响渐渐微弱下去,闻到夏夜田野里飘扬的草木与湿润泥土的香气。她好像听见爷爷在土屋的房间里踱步的声音。她相信,等到某天孟夏的晚风叩响老屋那扇灰黄的旧木门的时候,爷爷会拄起那根红漆剥落的硬木拐杖,在吱呀声中跟随泥土和稻花的香气走向最初的田野。
会吗?
会吧。

作者简介:
李思语,笔名:慕之。2005年生。家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现于江苏省扬州市求学。爱好国画书法,获江苏省大学生艺术比赛省三等奖,多次入展区级展览,现为区美术家协会会员。
第八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入选作品会择优在《品诗》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芙蓉国文汇》一书。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八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0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2篇以内 微小说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 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到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