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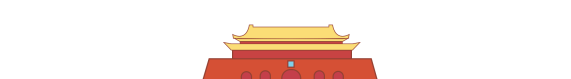

辣子
文/于金鑫
大概四五年前,我回老家去,和李老太一个胡同的邻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家里住李老太和李老爷子两口,带着孙女旦旦。我奶说这小妮子泼辣的很,闹起来十里八乡都能听见她尖嗓门的动静,和“凤辣子”比起来应当也是不差的,我奶当然不晓得“凤辣子”是哪个,这是我略显夸张的杜撰。我以此比喻并期待看见真人真事,以在两个辣子里分出高低。
行至胡同口,没见着人先有一声尖锐嘹亮的叫声扎进来,如果对面有人,应当能看到我的耳朵像动画片里演的一个样儿上下摆动,开启“自我保护机关”。两个小妮儿你追我赶从我行李箱旁边窜过去,后头那个拿着一根细长的柳条,胳膊举过头顶,蓄满了力往前抽,没一下能抽的到,分不清是谁发出的不间断的尖叫,莫名其妙的游戏竟叫我看出几分乐趣。“就那个,抽人的,死妮子吃不了亏”,我奶嘴角撇着,下巴有规律地抽动起来往出送,可能是出于礼貌,用下巴代替手指人的习惯,我们这儿的人都这样。终于见着旦旦的真面貌,已经是第二天,一出门就见着她,还没到上学的年纪,除了在胡同里来回地疯玩,也没有更好的归宿。丹凤眼,蒜头鼻,长得并没有什么特别,要非说有什么能留下印象的地方,约莫是鼻尖一颗圆润饱满的黑痣,不是很大,但胜在黑的标准,在一张算不上白净的小脸上格外醒目。
斜对门不过十米的路程,又不像要养家的每日起早贪黑,我和旦旦整日里碰面,一来二去的不熟也熟了。她的具体年岁没仔细问过,只凭借并不精湛的眼力猜测四五岁的样子。白天吃了饭她就来找我,其实也没事可做,就在一处坐着,或者扯出一根毛线估量着长度剪开来翻花绳,因此练就了我熟练的翻花绳的功力。我笑眯眯地称她为我的“忘年交”。有时候吃过晚饭,她会专门来带上我去村口的路上转转,路过一大片的绿油油的麦田,没熟透的麦子已经抽出长长的饱饱的穗,选一支熟的刚好的,揪下来放在手里轻轻地搓,把麦皮都吹去,留下青绿的软乎乎的籽,攒成一把放在手心闷进嘴里,麦籽在嘴里爆开,混合着青草的清香和粮食的浑厚,留下再难忘的味道。要注意的是必得准确找出熟的刚好的,过一点太硬,浅了在手心一搓就变成绿色的带着白浆的麦泥儿,我和旦旦比赛谁找出来的这样的更多,摘得多了就用砖头垒出一个小炉台,这事她最拿手,放点树枝麦秆烧出木灰煨熟了,也别有一番风味。
关于“辣子”,跟旦旦相处下来我倒有些不一样的看法。她每次过来只是很规矩的坐着,我是没什么哄小孩的经验的,招呼一句,就自顾自地看书,按我认知中小孩的闹性她呆不久,自己走就走了。但她一坐就是一上午,也不说话,我递给她一本书,她就翻开看看,也不晓得到底能不能看得懂。后来慢慢熟了,她才往我靠着的塌上爬,也还是不会出声打扰,让我几天来担忧她失控吵闹的焦虑渐渐平了。在包里翻出以前放进去的零食坚果,全当学着哄孩子,开始和她慢慢的聊,是很舒心的聊天,不用费心寻找话题,不用斟酌哪句得罪人的话,也不用陪着笑脸,说道哪里停到哪里全凭心意。
我们俩已经变得很熟悉,旦旦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里去,我左右也没什么事情做,索性跟着她走。过了门廊,有一面整的瓷砖贴出来的墙画,有山有水有树有鹤,很是素雅,看起来怪好的,不过是应当有个名字,可惜我并不是个爱深究的,大概叫山林垂鹤图也是行,这样的墙画我们这儿每户都有,我们管这叫“门迎”,年三十贴对联的时候把最大的一张福字贴正中间,不管是谁进来一眼保准就能看得见,沾染一年的喜气儿和好运。院子并没有开的很大,拐个弯走几步就能进去堂屋,屋门旁边很近的还有间旁屋,开出来侧门对上堂屋的门正好呈九十度的夹角。铝合金的钢管围个框架,再用透明的硬塑料壳整个的包起来,跟屋顶连着,冬天在屋里烧个炉子,热气儿是一丝也不会叫散出去,堂屋和旁屋建出来的夹角正好在里头出来一个窄窄的走廊,这是这两年才兴起来的装修样式。旦旦走到前面,又回来拉着我再往里走,走到这还没见着李老太和李老爷子,那应当是不在家里的。做了一路的心理建设和背过了的叫人的礼貌也没有用武之地。我找了个话头说起来,“旦旦,你爸妈为啥给你起名叫旦旦?”问出来又觉得是当真好奇。“大姐姐叫旦妮,我妈说叫我二旦,我爸觉得太难听,后来就叫旦旦”,我还是没懂,父母给起名要么按家里的中字排下去,要么有寓意有期望,总归是应当有点“来头”才行,想开口又觉得旦旦不一定听得懂,为了避免解释上几遍的麻烦,我只是点头,“不错,是不错”。
我是要走,要回去上学,打了顺风车到村口,有一段需要步行的路,旦旦就在后头跟着,盯着脚尖走,也不抬头,“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她问一句,声音很小,但我听得清楚,“很快,下次放假,我肯定要回来”,“那是什么时候?”她才抬起头,直勾勾地盯着人看,“很快的,就是很快的”,她过来拉住我的衣角,一定要把我送到车上。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许多的事,总是不得闲,匆匆地回去,又匆匆地回来,也见过旦旦几面。
如今再见,倒是叫我生出很大的意外。这样大的变化,是根本不可能认得出的程度。小脸白白净净,还有点肉乎的形儿,鼻尖上的那颗痣没有变化,只不这么显眼了,和小小的五官搭配起来倒是相得益彰,别有一番特色。穿着的校服白的光亮,在阳光底下一寸一寸仔细找也绝不可能找见一个油点子,红领巾系地板正,和城里精贵的温柔的姑娘并没有什么两样。
回到家里,我奶正在她那一小片菜园地垫着脚尖摘豆角,我接过来她手上的竹篓子,聊起来,不无感慨:“旦旦长大了,变得真是很不一样。上次见她还是豆丁一样瘦小的,现在也出落成漂亮的姑娘家了”。
“她爸和她妈原都在外头打工,前年吧大概,她妈回来了,可比她奶奶照看的不知道精细多少,书法课、舞蹈课都报上,当然是能叫看出变化的。”老太太边说边摘,努力垫高脚跟看起来颤颤巍巍,又稳稳落在地上,我一伸手作势要扶,她提前预判地拍掉,“哎呦!我可比你稳得多嘞!”我颠了颠篓子里满满的豆角,也预见了自己接下来几天的命运。

作者简介:
于金鑫,女,山东枣庄人,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业余文学写作爱好者。
第八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入选作品会择优在《品诗》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芙蓉国文汇》一书。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八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0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2篇以内 微小说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 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到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