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读的一本书丨独抒性灵 诗意栖居——读《袁枚小品》有感
作者:林赶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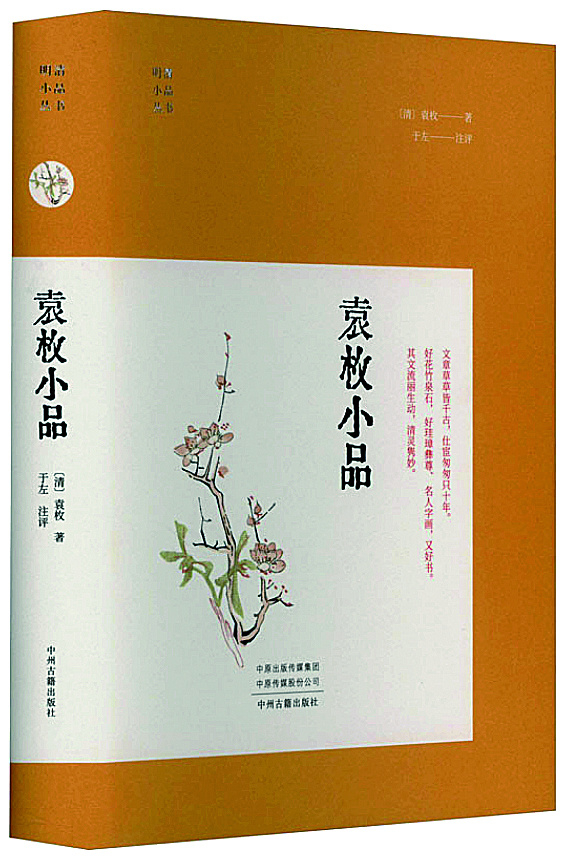
《袁枚小品》。
活了九十多岁,跨越了两个朝代,随着明清易鼎、时代变迁,“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的张岱从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高处跌落到了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低谷。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张岱年过半百,却一事无成,只能听任世人呼之为“败家子”“废物”。后来的曹雪芹也有类似的经历和感慨,所以才能写出“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红楼梦》。
相较而言,袁枚就幸运和幸福得多了。他虽然没有张岱高寿,但一生逍遥自足,绝无大起大落的痛苦。他说过一段类似张岱的自白:“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作家于左注评《袁枚小品》(中州古籍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认为,这“简单的一句话,基本可以概括他的全部生活”。“好味”就是“好美食”,袁枚写的《随园食单》即为一色香味俱全的明证。“历代文人精通饮馔者不乏其人,也有许多相关的诗文创作,但很少能够聚而成编,留下书目或存世的更为少见,《随园食单》无疑是其中最完备、最有操作性、最有文人风调的一部。”为此,在《袁枚小品》中,于左特意选注了《随园食单》的一些篇章。比如:“饭之甘,在百味之上,知味者,遇好饭不必用菜。”所谓“盐者,百肴之将”,乃是古今共识,现在民间仍然流传着“山珍海味盐为头”的谚语和故事。袁枚偏要做一回翻案文章,认为饭才是百味之本,遇上好饭甚至可以不吃菜。于左评曰:“他是一个食欲旺盛之人,但总是在消化系统出问题,否则他的寿命可能更长。”呵呵,真是老饕一枚,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吃货一个。
“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则有随园和《随园诗话》共为见证。据说,《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就是随园。在南京城北小仓山麓,原有雍正年间的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荒废后被袁枚买下,一番修葺改造之后,取《易经》“随时之义大矣哉”之意,易名为“随园”。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人生的本质是一首诗,人是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大半生都徜徉于随园内,既不仕,也不隐,歌哭于斯,聚族于斯,袁枚是真正做到了诗意栖居,将生活过成了一首诗:“每日迎来送往、觥筹交错、诗文唱和,好不惬意。”通过在园中编撰《随园诗话》,袁枚高举“性灵说”的大旗,广泛网罗同志,切磋琢磨,最终使“性灵说”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等并列为中国古代主要的诗歌理论。
说到同志与好友,除了为数众多的弟子外,袁枚自称尚有闺中三大知己,皆是吴门才女。其一姓金,名逸,字纤纤,嫁苏州同乡陈竹士,陈在与金结婚前已是袁枚弟子。袁枚视金为知己在于她“领解尤超”,对诗特别是随园诗有着非凡的领会理解能力。金逸曾与竹士同梦至一处,烟水无际,楼台出没云气中,仿佛有人告之曰:“此秋水渡也。”因共联句,醒而忆“秋水楼台碧近天”七字。其后纤纤小病于母家,一夕扶病归,谓竹士曰:“侬殆不起矣。昨夜梦数女伴邀登一舟云:‘将往秋水渡。’梦兆如此,欲生得乎?”过了十日,果然病逝。这件事虽然有点玄,但亦可略见其理解之妙。殁后,杨蕊渊、李纽兰、陈雪兰三女士慷慨解囊捐金,刻其《瘦吟楼诗》;与清代文学家杨芳灿齐名的陈文述有诗云“蛾眉都有千秋意,肯使遗编付劫尘”,即指此事。袁枚更是亲作墓志铭,推其为吴门闺秀之“祭酒”。此外,袁枚还有一位“生平第一知己”——四川诗人张问陶,与赵翼、袁枚并称为乾嘉性灵派三大家。袁枚力倡“性情以外本无诗”,所以当女弟子严蕊珠一针见血地指出“先生之诗,专主性灵”之时,他难免会戚戚然心有所动。
后来,人们又扩而充之,将袁枚、张岱等人的散文也冠上“性灵”二字而名曰“性灵小品”。中州古籍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一套“明清小品丛书”,大都能归入此类,其中的《袁枚小品》显然亦可这样称呼。散文小品之小,是说篇幅简短,文短而情长、情真,以我手写我心,则为性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