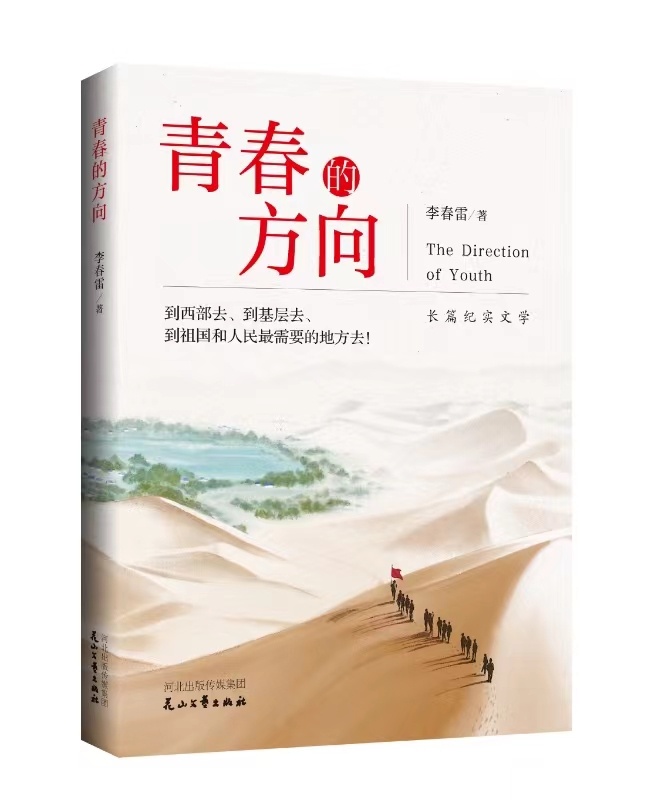大学毕业,到三千多公里外的沙漠小城去教书
侯朝茹,女,1979年生,保定市曲阳县人。2000年毕业于保定学院历史系,随即赴新疆且末任教。

2000年8月,保定学院的学子在赴新疆且末途中的合影,前排右三为侯朝茹。
选择去新疆的时候,侯朝茹刚刚过完21岁生日。签下就业协议一个月之后,才忐忑不安地告诉父母。
父母当即表示强烈反对。兄妹4个,她是老小。前几年,父亲突发脑血栓,为了治病,欠下不少外债。现在,她毕业了,在家乡就业不仅可以从经济上缓解家庭困难,还可以就近帮助照顾病人。可现在,她执意要远走万里之外。
为了打消女儿的念头,父母与她进行了长达10多天的谈判和冷战。
最终,父母还是依从了她。
临行前夜,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到西部去!我愿驾驭青春,驰骋在生命的原野上,任他风雨雷电!”
出发那一天,父母蹒跚着,送她到村头。公交车启动的一刹那,她泪堤的闸门也启动了,滚滚流淌。她不敢回头,因为她知道,父母一定还站在原地,眼巴巴地看着她。
且末在哪里?
她不知道,甚至也没有找来地图看一看(河北保定距新疆且末3300多公里——编者注)。她更不清楚,年降水量不足20毫米、全年沙尘天气近200天,到底意味着什么。

侯朝茹。
刚到且末,她就体会到了当地风沙的威力。不仅是刮风,风里还夹杂着沙粒。沙粒打在脸上,犹如针扎,生疼生疼。
第一次经历沙尘暴时的可怕情景,她至今难忘。
天空,突然间就昏暗了,犹如一块巨大的帷幕,骤然落下来。
毫无征兆,自然毫无准备。
那时候,她正在上课,压根儿不知发生了什么。
学生们大声喊:“侯老师,沙尘暴来了!”
她回过神来,赶紧伸手去摸电灯开关,啪嗒,啪嗒,连续几下,没有任何反应。
停电了!
碰到这种天气,要么是线路受损,要么是供电单位提前拉闸。
此时,不知谁点亮了一根蜡烛,教室内终于有了微弱的光亮。侯朝茹往门口一站,只见室外黄沙弥漫,面对面不辨人脸,呛人的土腥味儿塞满鼻孔。
她慌忙退回教室,把门关紧,心怦怦乱跳。
很快,学校的停课通知传来了。
按照规定,停课期间,大家都要待在屋里,不能外出。因为树被刮倒、电线被刮断是常事,极易引发各种事故。
尽管宿舍门窗关得严严实实,但第二天醒来,房间依然被无孔不入的沙粒洗劫了一遍,不仅锅碗瓢盆、杯盘灶具里全是沙子,包括床铺、被褥,甚至头发、耳朵、鼻孔都灌进许多。风停沙静后,打扫房间,清理出的沙尘,竟然几乎盛满了一个洗脸盆。
怪不得有人说:“且末一场风,就能‘刮走’几位老师。”

侯朝茹带学生到沙漠种树。
但是,侯朝茹偏偏是一个倔强姑娘,只要认准的事,没有什么困难能让她轻易退缩。
既然沙尘暴到来时会耽误学业,从此她就更加珍惜正常天气里的上课时间,力争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作用。
由于工作量增大,再加上环境恶劣,她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嘴唇干裂、咽喉疼痛、鼻孔流血……那些日子,日渐消瘦的她,眼睛红红,头脑昏昏,总感觉天空中有一群黑色的乌鸦,在盘旋、在聒噪。
有一次,侯朝茹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课,忽然发现讲桌上血迹点点。她意识到,鼻子又出血了。
这时候,前排女学生立刻掏出卫生纸,帮她止血,还关切地说:“侯老师,我们这里风沙大,空气干燥,您可要记得多喝水呀!”
轻柔的话语,听得她心里暖烘烘。她把纸揉搓成小团,往鼻孔里一塞,没顾上擦干净血迹,又开始讲课了。

侯朝茹给学生上课。
除了身体不适,生活上的不便也时时存在。
那时候,在且末打长途电话,需要去邮电局排队;寄出一封家信,收到回信至少要一个月。
恶劣的自然环境、闭塞的交通、艰苦的生活条件,让一些同事心生犹疑。
2002年底,又一位同事要调走了。
那位准备离开的老师,一直瞒着自己的学生,但不知怎么回事,纯真善良的孩子们最后仍然得到了消息。
大家去车站送行那天,他班上四五十个孩子全来了。当汽车要开动的时候,孩子们一下子都哭了,不停地挥着手:“老师,我们爱您!老师,您一路顺风!”
这时候,一个靠近侯朝茹的学生流着泪问她:“侯老师,您也会走吗?”
侯朝茹从来没想过孩子会当面问这个问题,霎时怔住了。
过了几秒,她拍拍孩子的肩膀,郑重地承诺:“不,我不会走的,我要把你们教到毕业,陪着你们长大!”

侯朝茹在辅导学生。
这些年,她除了担任班主任和历史老师之外,还义务承担着学生高考前的心理辅导。
有一个高三男生,父亲突发重病,需要到乌鲁木齐手术治疗,母亲不得不去陪护,只留下他一个人在家,情绪特别低落。
侯朝茹主动担负起了陪伴任务。每天晚自习后,送他回家。早晨,她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询问起床了没有,吃早饭了没有。如果还没有起床,或者没有接电话,她就马上骑车赶过去,顺便再带一份早餐。
整整两个多月,孩子思想稳定了,学习也稳定了。
后来,这个孩子考取了重庆市一所大学。
(从2000年到现在,和侯朝茹一起到新疆且末教书的15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24年,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2015年,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