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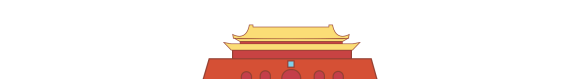

外婆
文/翟梦
2016年的最后一天,外婆离去。母亲说外婆走得很安详,舅舅们也定义“喜丧”。
耳边听着王源的“天黑黑”,莫名得流下泪来。那时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接受外婆的离世,只是觉得她还在舅舅家坐着,虽然不能说话,不能行走,但就在那里……
我是在外婆三轮车里长大的。我出生的第一天就被外婆抱回了家,90年代初的计划生育或许真的很紧吧,在我依稀记得的童年里,外婆每天骑着那破旧的三轮车,带着我“走亲访友”,东躲西藏。忘记那个年代什么人家才有三轮车,只是记得外婆家真的很穷:两间窄窄的茅草屋,上方只有一扇天窗,一进去分不太清白天还是黑夜。里屋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两三个放置衣服的箱子,外屋靠墙放着一张小床,那是我和表妹的小窝。屋外地方很大,除了屋山前做菜用的锅和吃饭的石墩、屋南头有个猪圈,四周都是外婆家的菜园。
不知几岁,外公喜欢在屋前种植烟草,他有一个长长的烟杆,那时,我总喜欢坐在旁边看着外公自己制作烟草,烟草晒干了捣碎了,就可以装在烟袋里,想抽的时候就让烟杆舀出一点来,看着外公飘飘欲仙的样子,有时也会急得心痒痒,有一次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和表哥偷偷尝了一口,结果被呛得半死,从那以后再也不觉得那是个好东西了。
除了那点烟草,其他的地方都被外婆种上了蔬菜。小时候,我很是顽皮,也是个好动的主儿。记得那时在自家楼梯上摔下来胳膊骨折后,母亲就常说我真是命大:婴儿时就因为营养不良被医生断定活不过太长时间,最后硬让外婆没日没夜地照顾把命拉回来了;再大一点,表姐拿着镰刀背着我过河,镰刀就割到了我的头中央,至今头上还有那道疤。当然小磕小绊就更是少不了,膝盖、手指、手腕现在都还有小时贪玩的印证,每到那时,外婆总喜欢搓一撮丝瓜叶或在田里摘点红草放在伤口上,不一会儿就好了。
我最喜欢坐在屋南的猪圈上方。吃着外婆煮好的茶豆、梅豆,看着底下的小猪吃食。头顶太阳高高照,吃饱了,看累了,就直接躺在上面睡一大觉,不用担心什么事,反正一切有外婆在。在我的印象中,外公少话,很严肃。外婆则就外向一点,跟谁都能热络起来,但我知道外公就是外婆的天。
外婆身体一直很好,加上宽大的骨骼显得很壮实。家中菜园基本上都是外婆去种去卖。外公生病后,她更是如此。秋收时节,外婆每天都会去集市卖菜,那时我已回家,每天卖完菜她都会到我家停留一下,把没卖出的菜给母亲,或者捡到完好的玩具拿来给我。外公09年肺病去世,那几天外婆很安静,依然抱着自己的曾孙,依然见人就和气谈笑。外公丧事办完,小舅要带外婆去苏州住,就在上车前几分钟,外婆突然倒地不起——半身不遂。得知消息时,我还在学校,母亲哭着跟我说,外婆倒下了。我怯怯的来到医院,看到病床上的她,我不敢认,母亲哭着让我叫她,我不敢叫:病床上的外婆好瘦,仿佛只剩骨头一般,原本宽胖的脸庞此时好像一巴掌就遮挡住了,我无法相信这是我的外婆,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外婆……
外婆在床上躺了7年,我去看外婆的次数却不是很多。母亲常说我冷血,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见到外婆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那时的我很想为她做些什么,却又做不出什么。外婆老了,但依然见到人很热络;我长大了,却渐渐地不再活泼好动,倒养成了个安静内敛的性子。外婆离世那一天,已没有力气发出任何声音,我默默地陪在她身边,心早已泪流不止,外婆突然激动得拉着我想要跟我说些什么,最终没说出来就撒手人寰。可是我知道,这是她对我做的最后的告别……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小时候看着别人家办着丧事,天真的在心里想什么时候家里也有。长大后,真的有了,却说不出的苦涩与悔恨。
作者简介:
翟梦,江苏新沂人,本科学历,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热爱写作,热爱生活。曾获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作文大赛优秀指导一等奖,十一、十二届等江苏省诗歌竞赛优秀指导一等奖等,作品见于《时代教育》。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大赛为期一年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