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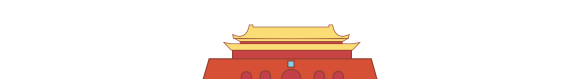

迷失的村落
文/田建文
人有时候会无端地产生一些怪念头,无端的想起一些怪事情。我、突然想起,那种古朴自然的“村”,会不会从我的意象中消失。
记忆中儿时的家乡,那是一个偏辟、闭塞的小村庄。这小村,按照那时的生活水准来说,不算贫瘠,因为人们都自给自足,没有贪念,没有过高的奢望,所以这里是一群安逸的、平淡的生活着的人们。
这里有山有水,有平地有沟壑。这里有果树有竹林,有花草饰边的小路,有藤蔓装点的村屋。一弯溪水从后山盘夷而来,又从眼前曲伸而去,窄窄的象一条绸带。
小溪绕着小村大半个圈后,便一头扎进罗江,罗江的上游是浯口,罗江的下游是罗湖。罗江虽然叫江,大多时候其实比溪流大不了多少。这江、涨水时急湍奔腾,白涛浊浪,有些壮观,枯水时却能见水底卵石,清流潺潺,可以赤脚涉水而过。如果你运气好,还能在卵石中翻寻出一种叫黄蜡石的石头。是玉石的一种。
小村就这样背靠大山,又拥着江水,依山傍水,既粗犷又灵秀,既贫乏又滋润。
村头有座石桥,建筑于什么朝代没有人考究过,只知道爷爷的爷爷时就有了。桥面平,桥孔是拱的,类似赵州桥,但没有耳孔,大孔弯成半个月亮。如果合上倒在水中的另半个,那是十五十六的团月。桥是唯一连接外界的通道,可以过车的。只是那时的车,是木制的土车,牛拉着走,也没有现在的大。那时的路,也没有这时的宽。
村子中部也有桥,是石扳桥。因为那里比较开阔,所以那桥便柱着几个墩,长条的石板三块一并地搭在石墩上,远远看去,象是在河里连接着几条长板凳。因为较近、村里人过溪河,大坻是走这板桥的。
村后的桥,高悬数丈,其实是渡槽,引水灌溉用的。1米五宽、近百米长,全是水泥石板结构,从前边山头通到后边山头。不走人。但有毛头小子斗勇斗狠,或挑担、或扛物,或推木质土车,也从那上头通过,便当是“桥”了。
几十年过去,这村、却还是脑海中那个村。现实的村、不知道现在还存不存在。
中间有一次回村,那模样就大不比幼年时我心中的村。村中己没几户人家,大部分已搬到山外去住了。少有的几户也没壮男在家,几乎全都出外打工。渡槽塌了,石板桥断了。拱桥长满滕蔓和荒草、似乎有些颤颤巍巍地,欲在苍色中老去……
我在小村也没什么亲戚,一个远房的老叔早己作古,因而我再也没回过小村。
退休后不知怎么了,总有一股苍凉的忧愁驻在心头。不知是不是开始走向老年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习惯了城市的渲嚣却又渐渐走向不习惯,平常了虚与的应酬渐渐有些厌恶,某些获得的东西渐渐又希望剥去,某些丢弃的东西渐渐又渴望获得。渴望获得什么呢?其实只是一种情愫,一种怀旧的情愫,一种回归本真的情愫,一种植身大自然,让心平静在碧水蓝天的情愫,一种只想幽居的情愫。这种情愫的实践,白居易做到了,陶渊明做到了,许多杰士名流做到了。然而生活在现代更现代,发达更发达,先进更先进的当代的我,怕是做不到了。
作者简介:
田建文,湖南省汨罗市人。本人从小受家庭艺术感染,父母从事文化艺术工作,酷爱艺术、如文学、美术、摄影、书法等。早期摄影作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曾获全国青年摄影三等奖。美术作品曾在全国大赛中入围北京参展。散文及诗歌也多次在全国、省地市级刊物中发表。是中华诗词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词协会楹联协会会员。岳阳市诗词协会及楹联协会散曲协会会员。汨罗市书画家协会、诗联协会常务理事,散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市诗歌协及摄影家协会会员。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大赛为期一年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