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海男 画
——余海岁诗歌的崇高景观书写
路 也
读余海岁近年的诗作时,我注意到他对崇高景观有着特别的兴趣。这里的“崇高”,是柏克所讲的崇高,也是康德所讲的崇高,是与优美感相对的崇高,可以分为浪漫主义与哥特,可划分为数学式崇高与力学式崇高。既空旷又孤独的情境、对越来越大事物的希冀、星空高山冰川暴风雨等充满威力的大自然所带来的惊愕、与困境博斗时失控的激情、在自身处于安全地带时被危险恐怖事物及悲剧所吸引并产生强烈情绪及快感、以宇宙为坐标想象兴发朝向无限时的狂喜……这些都可以将灵魂提升到超越庸常的高度,产生道德上的伟大。
这位诗人是岩土力学专家。岩土力学作为一门专业,要研究岩石土壤结构在受到静力、振动、和冲击等外力时会发生怎样的有效维持、变形、扩展和破坏,这是类似于铺路、架桥、挖隧道、修地铁等各项岩土工程实施的前提。如此硬朗和富有力度的专业,大致也应该划归于崇高景观里去吧。
诗人自己的一句诗“我直面秋风的目空一切”,似乎可以精准地用来概括这种美学倾向。这句诗里有秋风带来的飞扬、发散、突破、肢解和决裂的意味,更有诗人的自信和睥睨的姿态。这种对于崇高景观的偏爱所带来的审美特征,再加上作者将中国古典的绝句式表达应用于现代诗歌创作,特别注重诗节之间的空白,遂使得这些诗的风格趋向冷峻、简约、有力。
余海岁对于崇高景观的书写,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作为崇高景观的自然物象、作为崇高景观的人类活动烙印、作为崇高景观的系列人物。“景观”可以涉及人类多种感官,但主要还是视觉上的,视觉毫无疑问具有优先权,所以,在三个方面的内容之中,最基本也是最具典型性的当然是对于具有崇高感的自然物象的书写,至于后两者则可以看作是崇高自然物象在美学倾向上的进一步延伸。
诗歌中的自然物象书写,大致包括了大自然中的现象、地貌、风物、季节、温度带等各种不同层面的存在。
余海岁所写的自然物象,多为原生态,有着广袤和苍茫的特点,具有客观真实性及科学性,有时还具有不可知感和恐惧感,这是一种很西方化的自然观,大多展示出人类面对大自然时的局限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征服欲和探险精神,以及对于上苍从混沌中创立出来的宇宙秩序的好奇心。诗人的这类诗歌,在抒情方式上,区别于传统浪漫主义那种以表达个人自我感受为中心的抒情方式,而是让位于自然物象,让它们来作主角,登场发言,用一种由内而外的近乎离心力的方式让抒情主体不知不觉地浮现,由此使得被写的自然物象通常处于一种等待唤醒的暗示状态,在诗中又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诗人的形体状态和灵魂状态。
《闪电》可看成是用诗的形式来解释闪电这种自然物理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正电荷和负电荷仿佛处于相距甚远的不同阶层的一对恋人,“正电荷高高在上 / 负电荷。屈居云底”,然而致命的吸引力使它们历经千难万险,双向奔赴,“它们终于打开一条通道,在空中紧紧相拥”,相遇的那一瞬,迸发出天崩地裂的能量和光芒,如同伟大的启示。《风之痕》与《闪电》相似,只不过这次书写的对象是风,写的是热空气和冷空气之间的相互转换如何制造了力量对比与升降,从而产生了风,但诗人对此的进一步解释则是世间万事万物必须历经沉浮飘摇的命运感。还有《黑洞》一诗也属于类似诗作,尽最大努力用通俗而感性的方式来解释对于普通人来说很烧脑的科学问题,诗人表明预言属于“上世纪”而现象则属于“今天”,似乎有将广义相对论引入人生的意味。像这种以诗性思维来写科学的诗作,倒使我想起了关注宇宙的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在《二十亿光年的孤独》中对于“万有引力”的重新定义:“万有引力 / 是相互吸引孤独的力”。
目前可以看到诗人已写过三首叫作《月亮》的诗。三首诗标题完全相同,风格近似,角度略有区别。科学家所写的月亮之诗,与文科生的月亮可谓大有区别。三首诗中的月亮意象全都显得清远、硬朗和理性。写于2022年10月10日的那首《月亮》,分别写了登月第一人的阿姆斯特朗、以及李白、史蒂文斯、策兰等人视角里的月亮,月亮形象分别是平而灰暗的、梦断时洒下冷霜的、悲伤与怜悯的、宇宙深处随雪片漂流的……总之月亮给人的印象是温度偏低。而写于2023年12月2日的那首《月亮》,写的是一弯新月,在这首诗中,诗人给这弯新月寻找到两个带有隐喻意味的布景,一个是像海洋一般的蔚蓝天空,一个是有着风霜和树枝的山谷,意境清冷而肃穆。还有一首是写于2019年9月7日的《月亮》,写的则是月亮自身并不发光的真相,诗人试图解构古往今来关于月亮的审美神话,指出它只是“一道遥远而迟到的假象”,非常有趣的是,诗人在描述月球荒芜表面时竟使用了“沥青”一词,作为岩土力学家的诗人,在这里算是使用了一个自家语汇——在岩土工程之中作为防腐材料和结构胶结材料的沥青,当然属于必不可少的参与者——诗人在此使用“沥青”一词既有意也无意,一方面,是要表达月亮地貌特征的客观真相,另一方面,诗人潜意识里是否设想过研究月球上的岩土力学并有朝一日去月球上建起大工程?
另外,诗人还有三首以石头为主题的诗,分别是《力学浅说》《石头记》《一块石头》。《力学浅说》一上来就将两块石头相互快速摩擦产生出火花,形象地理解为两个陌生人之间产生爱情,这样相撞的两个物体在同一直线上,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因此爱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同理,诗人又推论出,伤害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也是相等的,于是,诗人就这样从人性的角度将牛顿第三运动定律进行了全新解读。《石头记》写诗人在沙滩上观察石头,发现石头的“纹理间折射出海浪拍岸的角度、力度 /和深度”,这可真是一位岩土力学家的视点,岩石在包括水流在内的外界因素作用下的应变正是他的兴奋点。至于《一块石头》则将铺路的石头当成书写对象,由它的刚度和强度联想到它抗压、抗拉、抗剪、抗扭的特点,直接赞美铺路石的不胆怯不崩溃的石头精神,相比前面两首与石头相关的诗,这一首更是将岩土力学理论发挥到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令人疑心是从某个岩土力学教科书或者岩土工程施工方案里直接拎出来又以回车键进行了分行排列的,而此诗最终以“和镣铐中的骨头一样”结了尾,诗意顿出,卒章显志,竟有石破天惊的效果。石头这个意象本身是坚硬的、孤绝的、倔强的,不屈不挠的。这些石头如果用于建筑,纯粹的巨石建筑总比茅草房、砖瓦房和水泥房更具有崇高感。
在《飞蛾》里,那误把引诱的灯火当成温柔月光的飞蛾,它渐次接近着灯火中心的那条运动线路被诗人描述成了数学里的阿基米德螺线,飞蛾一错再错地转身,沿着一条布满血迹的致命的轨迹,终于陷入了黑暗的深渊……这多么像一场无法避免的性格悲剧,有着宿命般的无能为力,令人扼腕叹息。在这首关于飞蛾扑火的诗中,阿基米德螺线的几何学与布满血迹的直觉真理具有同等的崇高价值。《孤独》一诗写的是一粒种子的洪荒之力、卧薪尝胆、横空出世,从干裂岩缝里长出来,长成一棵树,令人惊异。诗人写《蒲公英》时写到了它的种子飞往旷野、星空、黎明、灯火阑珊、黄昏尽头以及月光下,意境辽阔而苍茫,会引发联想起“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这支老歌,而相比之下,这首上世纪的电影插曲是一个关于蒲公英的优美版,而诗人这首诗作则是一个关于蒲公英的崇高版,或者说,这首诗是那支歌的升级加强版和苍凉版。无论多么渺小的自然风物,在诗人笔下,都有着与环境和命运进行博击的勇猛,可以生得倔强,死得壮烈。
至于地貌,诗人写了这样的山,那样的谷,这样的湖,那样的河,而他最喜欢写的——写的最多也是写得最好的——终究还是大海。不计算零星涉及大海的诗,只看直接以大海为书写对象的诗就有《在海上》《海边》《爱琴海》《沙滩》等等,余海岁所写的大海,往往是创世之时的模样,少人或无人,几乎只有大海本身,横在遥远的天空下、黑暗、荒凉、空旷、在岩石上激起浪花的潮水正永不止息地做着各种力学运动……大海是一个朝向并接近着无限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可供目光驰骋,符合宗教的伟大而开阔的要求。大海确实很难被人类改造,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平静、欣然、战栗、惊恐、未知,从友好到敌意,可以无需过渡,大海呼应着灵魂中的崇高。至于那首《爱琴海》看上去则似乎有所不同,诗中所写并非少人或无人的大海本身,而是涉及海伦和帕里斯等人物,涉及特洛伊木马,然而,这些都是过于久远的历史及希腊神话,仍然有着远离当下尘世的荒远之感,一片爱情之海,一片激烈之海,一片历史和神话之海,有竖琴,有玫瑰,有人粉身碎骨,有人私奔,“因为爱情,天空撕裂,爱琴海千帆竞发 / 不惜燃起一场十年的战火”,其中充满了欲望纠葛、骄傲、狂热、复仇、人性的紧张以及悲剧意识,这样的爱琴海跟创世之初的荒无人烟的大海拥有了共同特点,都蕴含了既浪漫主义又哥特式的崇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余海岁在诗中写到这些作为崇高景观的自然物象时,有一个明显特点,他似乎特别倾心于“北方”。诗中的北方主要涉及这个诗人长年生活的英国北方。英国原本就位于北半球的高纬度区域,诗人所任职的利兹大学又位于英格兰北部西约克郡的首府利兹,而通常意义上的英国“北方”概念大致包括英格兰北部以及更北的苏格兰地区。现任英国桂冠诗人西蒙·阿米蒂奇是诗人余海岁同一大学的同事,这位在英格兰北部西约克郡一个叫马斯登的村镇长大的诗人自觉地延续了包括勃朗特三姐妹、汉弗莱·斯彭德以及泰德·休斯等文学前辈在内的北方取景风格,坚持不懈地写自己故乡的高沼地荒野、冬日夜空、冰雪站台、冰冷房屋、北奔宁山脉、城堡、排屋、田园怀旧意味与前工业时代遗存相互交叠的氛围、既有神灵又有恶魔的超自然色彩……如今他已成为北方的代言人,执拗地认为北方就在西约克郡,就在马斯登,“虽然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只处于中间地带,但你可以称之为北方……进而是苏格兰。”阿米蒂奇在评论同事余海岁的诗歌时,其中有这样的用语:“他的诗歌打动我的是,对一个已经迷失或渐行渐远之世界的向往——这个世界的大自然曾经为诗歌提供了固定的参照和可靠的隐喻……”虽然“北方”字眼并未高频率地出现在余海岁的诗歌中,但是他在诗中常常涉及属于北方景观的意象并营造出北方气息的情境,使得“北方”确可看作是他诗歌中“固定的参照和可靠的隐喻”之一。这样的“北方”气质,无疑更接近于崇高景观。
余海岁的“北方”首先体现于对自然季节的书写。这个出生于亚热带的中国皖南的诗人,长期旅居他乡异国,有一大批诗歌书写了明显属于温带的秋天、冬天和岁末。像《十月》《十一月》《白露》《冬日》《岁末》《黄昏》《雪》《大雪》《跨年》《立冬辞》……都属于这一类。《立冬辞》这首诗里使用了一些振幅较大的语汇,可以在诗中造成某种起伏,动词有“深陷”“呼啸”“挣扎”“颠沛流离”“敲响”等,名词有“枯叶”“寒风”“碎石”“大地的栏栅”“天窗”“呼唤”“呐喊”,当然诗中还出现了“雪莱”“策兰”这两个既热情又冷峻的名词,这两个诗人名字的出现,主要目的并不是向这两个诗人致敬,而是想借他们寒冷而决绝的人生经历来进一步增加此时冬天的庄严感、肃穆感乃至命运感。诗人还一次又一次地书写一年的末尾或一天的暮晚,总之他偏爱着某种终末之景。最典型的当属《跨年》一诗,诗中全无一年时光正在逝去的伤感,而是颇有励志色彩,反复强调“岁末”“年终”“最后”的概念以及放纵类似“悬崖”“鸿沟”“地平线”“裂变”“绝处逢生”“登顶”的极端想象,诗人将跨年看作是季节极限、年岁极限和感受力极限,正是在这样的朝向极限之中,事物才会否极泰来和出死入生。这是一个很少写春天和夏天的诗人,这并不是说他缺少热情,恰恰相反,秋冬的萧瑟与岁末的凛冽在带来身心磨难的同时,也增强了诗人对于外界的警醒和敏感度,情绪更容易变得激昂起来,最终促进了内在力量的觉醒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迸发。
诗人的“北方”其次还体现在他那些涉及英格兰北部风光尤其是直接摹写苏格兰高地的诗歌上。《尼斯湖》写的是苏格兰高地北部大峡谷中联通北海的著名淡水湖泊,诗中强调“高地”和“深渊”,并引人联想莫须有的水怪传说及其来源,有一丝神秘和恐怖的气息,又有一丝得知真相后的释然和通透。在《秋日》一诗中,作者耳边回响着风笛,写出了一句颇具漂泊感的诗句“在苏格兰的群山起伏中 / 我直面秋风的目空一切”,诗人独立秋风,而风是天地之间充满占卜意味的最原始的语言,诗人直面秋风的目空一切,而读者则透过诗人,置身此景,见诗人所见,一起体验崇高,而接下来诗中忽然引用了策兰的一句诗“这个秋天将意味深长”,又给诗增加了一抹苦抑和奇倔的色彩。不知《风雨灯》是否与苏格兰相关,此诗与其说是在写人造之物,倒不如说是凭借此物来重点描述某个极端自然环境,当然更不如说是在进行某种人格精神的写照,似有那么一点儿“江湖夜雨十年灯”之意。当然,在这类写北方的诗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那首《苏格兰》:
顶着北海的汹涌,我登上辽阔的高地——
崎岖的山路,宛若雷鸣劈开的闪电
高飞的翅膀掀起一湖无边的苍茫
弥漫在断层深处的,是勇敢的心
在荒野呼啸中燃起的熊熊火焰
这真是一首激越之诗,写出了苏格兰的桀骜不驯,很有一些彭斯诗句“我的心啊在高原,这里没有我的心”的昂扬之感。从这首诗中出现的“北海”“高地”“一湖”“断层”等语汇可以看出,此诗应该也与尼斯湖有关联。在这首诗中,地形由低到高,一路攀升,由大海到高原,由山地到天空,由峡谷到荒野,由心脏到火焰……同时诗中的语调也随着地势的上升而越来越高昂,这种竖向的位移变化使诗人得以俯瞰水平面并获取了超越尘世的狂喜,似乎找到了在“本我”和“自我”之上的那个“超我”。诗中出现“勇敢的心”字样,当然会令人联想起那部拍摄于这个地点附近并获得奥斯卡奖的著名电影《勇敢的心》以及影片原型人物——为独立自由而战的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诗中就这样将自然与历史不经意地结合在了一起,最终自然战胜了历史。华兹华斯在《孤独的刈麦女》里通过刈麦女的歌声而联想到苏格兰西北部的赫布里底群岛,把这个地点当作飘渺遥远的代名词,而在余海岁的诗中,苏格兰的具体地点则全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个人经验之中。
这种对于北方的偏好和迷恋,就是对于崇高感的追寻。相对于南方,北方总是更能激起关于英雄主义的想象,也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复杂和不可测,更加决绝。另外,北方或许还可以与高蹈的精神状态甚至信仰发生关联,恰如W·H·奥登所言“对所有人来说,北方意味着弃绝”,而奥登所受之影响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则提出过“无限弃绝”的概念,通过“无限弃绝”从而使人真正走向信仰,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方其实还具有着某种精神救赎的作用。
接下来,这样对于具有崇高感的自然物象的书写,作为一种美学倾向,并没有停顿和止息,而是继续向前延伸着,导致诗人对于带有崇高意味的人类活动烙印也颇为关注。在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各种景观里,引发诗人兴味的往往是一些巨大景象,可以是了不起的名胜古迹,可以是繁荣的城市掠影,可以是宏大的工程,可以是边塞聚居地,可以是靠交通工具实现的大幅度时空位移……这一类诗作里均隐含着人类的伟大成就,充满了创造的力量。这一类诗作不少,像《兵马俑》《新德里掠景》《疏勒城》《雁北乡》《时差新解》《飞机上》《隧道》《遥不可及》《泸定桥》《双旗镇》《斯基普顿城堡》《比萨斜塔》《奥林匹亚》《柏顿修道院》等等。这些人类活动烙印更接近于凝固的交响乐或者移动的纪念碑,诗人通过这些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巨大景观体验到了物质的深度与精神的高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比萨斜塔》,诗人赞美这座塔是“不完美之美的极致”,这首诗不仅致敬了人类建筑史上这座了不起的神奇之塔,还致敬了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最后终于又向自己从事的伟大的岩土力学表示致敬:“因为地基土的不均匀性 / 导致塔的不均匀沉降 / 塔斜了。却不甘心倒下……施工就变得越来越慢”,诗人确实是将岩土力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岩土工程学写成了诗歌,反过来,不知他在本专业领域里是不是也曾试图将诗歌运用于岩土力学以及相关工程设计呢?
甚而至于,最终,这样的崇高感美学倾向还一直延伸到了对于具有崇高意味的人物的关注。段义孚有一个观点,地理学不只是空间科学,还应关注对于自然和文化的求索,于是就要关注人物,人物既包括“群体”层面的人,更要引入“个体”概念的人,关注那些超越和逾越社会一般准则的行为和追求,于是美学家、英雄和圣人最富有浪漫意味,应当被特别关注。段义孚没有提及科学家,我觉得应该把科学家补充进去并加以强调。这样的“大人物”在余海岁诗作中也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景观”,诗人或许想通过这些人物来感受人类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可以抵达的极限吧,他们大都是脑力劳动中的精英,甚至是推动社会进步以至改变人类发展进程的人,以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居多。这些诗多为致敬之作,写的是诗人在某个特定情境下与人物的相遇,诗中有时直接出现人物的名字,像《致霍金》《致牛顿》《杜甫草堂》《在利兹遇诗人西川》《D·H·劳伦斯》《致图灵》《影子,兼答W·S·默温》,而另外一些诗虽然标题是以地名的形式出现的,但诗人聚焦的并不是这个地点,而是在这个地点出现过的重要人物,像《加尔各答》写到特蕾莎修女和泰戈尔,《图宾根》写到荷尔德林、黑格尔、张枣,《牛津印象》里,更是一口气提及了霍金、卡罗尔、艾略特、王尔德、托尔金、怀尔斯、雪莱,《波士顿之忆》里提及牛顿和狄金森,《比萨斜塔》提及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青城山》里提到黄宾虹,《天都峰》提及徐霞客和岛云和尚,至于《读<坛子轶事>》《蒙娜丽莎》《呼啸山庄》《桃花潭》这种近乎读后感式的标题很明显是分别向华莱士·史蒂文森、达·芬奇、艾米莉·勃朗特、李白致敬。
最后要说的是,在余海岁的诗中,在所有这些他热衷的崇高景观的背面以及后方,有一个非常坚实的根据地式的存在,那就是诗人那颇具优美感和怀旧意味的中国皖南故乡。中国皖南故乡一直作为一个遥远背景和人生底色而存在着,或明或暗地闪烁在字里行间。《清明》《时间也需要一座桥》《小满》《雨》《与母书》《南乡》《桃花潭》《谷雨》《老屋》《灯》《信》《桥》《西溪南,丰乐河上》《故乡》《杜鹃花》等诗都与皖南故土有着直接关联。与那些书写崇高景观的诗作不同,在这些与故乡有关的诗里,诗人的语调和动作都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温柔起来,他好像忽然眯起了眼睛,而且偏向于使用一些振幅较小的语汇。直接书写故乡皖南的诗,诗人前些年写得多一些,而近些年则写得明显减少了。对于诗人来说,英国是长期生存其间的“生存空间”,飞来飞去来来往往的世界各地则是“行走空间”,而那个保存着诗人的童年和少年的中国皖南故乡则越来越接近于一个“冥想空间”了。
远离故乡,才能重温故乡、认识故乡,复活故乡,更强烈地热爱故乡。在异国语言环境之中,用母语写诗,得以把故乡带回到自己身边来。是的,诗人余海岁发现了诗歌这个奇异通道,可以将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将西半球和东半球连接起来,将后半生和前半生连接起来,将崇高感和优美感连接起来。
2024.4.20.济南

路也,济南大学教授。著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评论集等多种。现主要从事诗歌和散文创作,兼及创意写作、中西诗歌比较、编辑出版等方面的研究。
附:
在海上(组诗)
余海岁
河流
自从有了河流
命运便有了此岸
与彼岸。为了抵达——
人类发明了渡口
轮船和桥梁
这些岸上、水上
或空中的事物
都或多或少地破坏了
河水的流逝与翻卷
唯有地下的隧道
从此岸,穿破黑暗
默默抵达彼岸——
似乎并未在场
却又真正维持了
失落后漩涡的
深不可测
2024.02.25
海边
海鸥嘶鸣。潮水
争先恐后地撞击晨光
无边的碎浪
腾空
追赶抽离的脚步
肆意铺洒在裸露的
沙滩上——
犹如鹰翅上的雪花
掠过炊烟
随风坠落在空旷的
驿站
2024.01.10
桥
小时候跟父母上山干活
总要经过屋前的石拱桥
几十年了。水中的倒影
一直闪烁在心间——宛如
被黑夜洞穿的星空
今秋回老家。独自
徘徊在小桥边。暮色里
它似乎矮了很多
也衰老了许多
我没敢再次
踏上这座桥——我怕
它会被心中的
孤灯
猝然压垮
2023.10.28
飞机上
浩瀚无边的云海
静静地躺在晨曦里
一眼望去,窗外
仿佛飘浮着
一个绝处逢生的
林海雪原
2023.10.01
西溪南,丰乐河上
曾经的老街,早已
人去楼空
上学时必经的独木桥
也被坚硬的混凝土
所取代
此刻,桥上挤满
操着不同口音的游客
他们一定不会猜到
夹在中间的我
是一个地道的本地人
只是,除了脚下一意
孤行的河水,和他们一样
这里的一切——
对我,从来不曾
如此陌生
2023.11.20
跨年
如果你是个名词
那就是岁末遥远的炊烟
或是年终最后绽放的烟花
我更看重你是动词的姿态
从悬崖顶峰,纵身一跃
跨过鸿沟——瞬间
回到地平线
正是这个从一到零的
裂变而绝处逢生
世间,才又重新找到了
攀高登顶的
钥匙
2023.12.22
大雪
赶在圣诞老人到来之前
赤裸裸的雪花,一夜之间
飞越千山。悄无声息地
在沉重的大地上
铺上一张如鸽子般
洁白的面纱
被寺院拒之门外的
滚滚红尘,在此起彼伏中
添了一群陌生的面孔
他们笑而不语,且
不惧凛冽。好像是
异域的过客
只想,借助时间的岔口
避开闪电——缓缓
款待冬季
2023.12.09
月亮
窗外,一片辽阔的蔚蓝
天空犹如无风的海洋
海面上出其不意地
浮现出一弯新月——
宛如昨夜被遗弃在
山谷枝杈间的
一抹风霜
2023.12.02
爱琴海
历史与神话相互磨损——三千年前的
爱琴海,有人不知所踪。有人在木马前
受骗,而粉身碎骨
竖琴声中,玫瑰怒放。美女海伦遇见了
曾是牧羊人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
他们一见钟情。海伦继而弃夫私奔
因为爱情,天空撕裂。爱琴海千帆竞发
不惜燃起一场十年的战火
2020.08.16,2023.12.16改
奥林匹亚
地中海亘古不变的波涛汹涌
挡不住古希腊强劲的南风——
这里曾竖起雄伟的宙斯神像
它在六世纪的一次火灾中倒塌
现在,唯有残垣断壁中的杂草
在风中述说着远古的梦幻
上世纪才发掘出的原始体育场
依然保持着,公元前的样貌
它和其它现代体育场一样——
是个只有起点和终点的椭圆
斜阳照耀在古老的体育场上
站在起点的我,不禁绕了一圈
跑到终点——感觉穿越了时空
跟古代的奥运会接上了轨
2023.08.29
柏顿修道院
坚守秘密。九曲回肠的
溪流,追逐、畅饮修道院
脱轨的前世今生——
隐居的马蹄声早已走远……
斜坡上拖着影子的羊群
哭泣落日最后的伤口
暮色苍茫间的飞鸟
在盘旋中,沉思默想——
千年前的风雨之夜
回荡在这山谷里的
该是怎样一种
惊心动魄的钟声?
2018.08.10,2023.11.26改
远方
一个少年,背着书包
在妈妈的陪伴下
来到一个不起眼的远方
他慢慢整理并轻轻
放下一束花……
后来,我听说
那个很远的远方竟成了——
一片花的海洋
2023.10.29
在海上
一只船,漂泊在海上
四周是无尽的浪花
船是中心。世界好像
一个巨大的圆
圆周没有一丝烟火
天上看不到星星和月亮
无边的暗和重复的风
彷佛构成了整个宇宙
等到圆心趋向港湾
迫不及待的电子信息
忍不住闪现在眼前——
迷失的尘世,才又开始
渐渐追上漂泊的脚步
2023.06.09

余海岁,号南乡子,出生于皖南徽州。有组诗发表在《诗刊》《十月》《诗选刊》《诗潮》《星星》《诗歌月刊》《江南诗》《扬子江诗刊》等刊物。著有个人诗词集《心相忆》《天涯梦回》《立冬辞》。曾获第四届中国年度新诗奖:年度杰出诗人奖和第九届“剑桥徐志摩诗歌奖”暨“徐志摩银柳叶诗歌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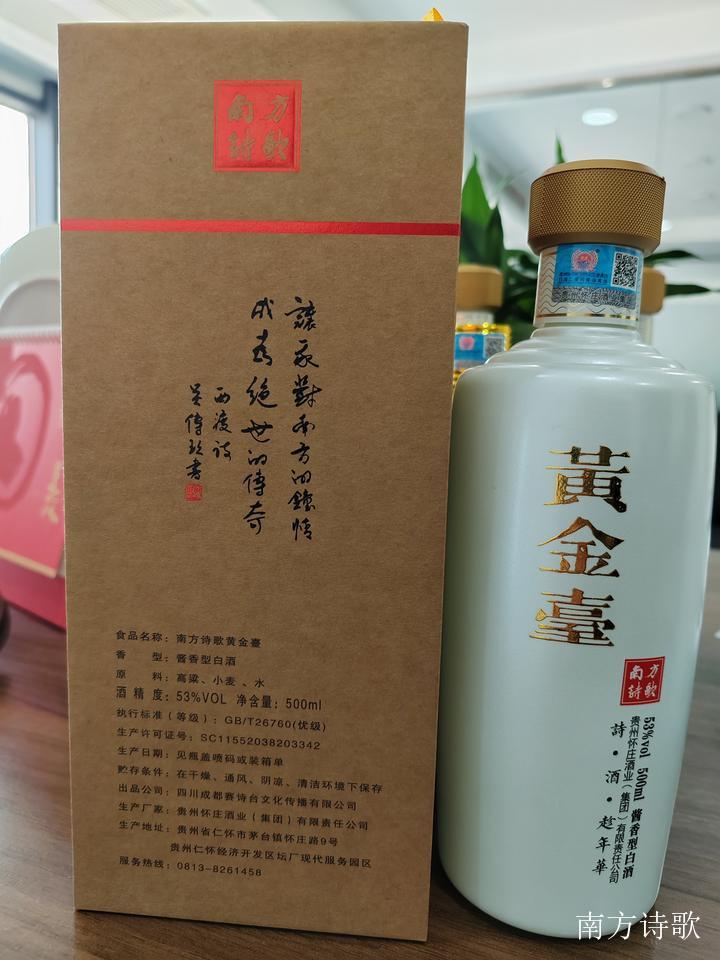
让我对南方的钟情
成为绝世的传奇
——西渡
南方诗歌编辑部
顾问:
西 渡 凸 凹
李自国 印子君
主编:
胡先其
编辑:
苏 波 崖丽娟 杨 勇
张媛媛 张雪萌
收稿邮箱:385859339@qq.com
收稿微信:nfsgbjb
投稿须知:
1、文稿请务必用Word 文档,仿宋,11磅,标题加粗;
2、作品、简介和近照请一并发送;
3、所投作品必须原创,如有抄袭行为,经举报核实,将在南方诗歌平台予以公开谴责;
4、南方诗歌为诗歌公益平台,旨在让更多读者读到优秀作品,除有特别申明外,每日所发布的文章恕无稿酬;
5、每月选刊从每天发布的文章中选辑,或有删减。
《南方诗歌》2024年九月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