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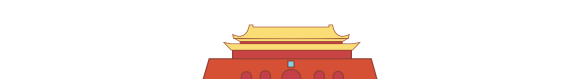

倒戈
文/陈薇
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去相信或者执行所谓坚定的事物,或许会在一刹那发生改变,或许会在不知不觉中随风消散,回首剩一片愕然。允许经历过负雪枯枝的偏爱春和景明,允许经历过沦落蹉跎的沉溺奇诡幻想,这是蓦然的倒戈。
世人都道寒梅是“香自苦寒来”,用苦寒来歌颂它傲雪的风骨,赞扬它凌霜的气节。黄檗禅师《上堂开示颂》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陆游《梅花绝句》的“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无一不认同苦寒是它绚烂的支持。
而当漫天飞雪侵蚀大地,将其染成白茫茫的一片时,梅花的一抹红便极其显眼,究竟是不畏凌寒的傲骨,还是迫不得已的无奈?
在梅的视角里,它也许并不自诩高风亮节,只是想在这孕育它的自然界安静平和地开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花,所以,凛冽和凌寒成为了它的宿敌。在朔风呼啸、雪覆花骨之季,梅花必须坚强地承受风雪之刺骨,才能让毫无庇护的花瓣不那么快“零落成泥碾作尘”。生机尚存,求生机的物便也执着。相比起那些一到时节就生机勃勃的生物而言,梅花的生存可谓负芒披苇。可尽管如此,咏梅之人总爱把那些苦难视为考验,并纵情高歌历经磨难后的成功。
无论是惯用意象的诗人,或是备受打击但仍“猛志逸四海”的“天涯沦落人”都把梅视为一种象征。皆言梅耐寒,这是他们赋予它的品质没错,可真正的梅并不像他们所说的对严寒“趋之若鹜”,它更喜欢湿润、温暖的环境。所以,与其习性不同,却被称为“岁寒三友”之一的它,只得顽强地忍受风雪的摧残,在春天期待负雪枯枝下的再一次新生。
——于是,这一次,它倒戈在春风和煦之时。
受时人称道,受后人敬仰的“诗鬼”李贺,自幼苦读诗书,涉猎琴棋书画,七岁便以长短歌行闻名于京城。这样的才子毫无疑问应当考取功名,施展抱负。
曾几何时,他坚定“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般忠君为国的决心;尽显“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般满腔热血的豪情。雄心壮志在他早期的诗和理念中表现地淋漓尽致。
可天不遂人愿,他在考进士试时因犯父名讳而被迫放弃考试,断了入仕之路。在那样一个时代,舍弃了科举就像海鸥离了大海,日光离了白昼,失去了根。
——诚然,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才子并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
沦落的家境,险恶的世态,孱弱的身体,重重堆叠在他的身上。故而,他发出“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的感慨。如此看来,曾经的意气风发倏忽间就被磨灭,只剩焦灼度日。
而这样“煎人寿”的生活如何坚持?人世已然使他颓然无望,他不免将自身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神世界。
你看“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泄”,无数人为之沉沦、为之倾倒的人世,于月宫俯视下不过九点烟。李贺将自己剥离人烟,以“神”“仙”的视角解读他眼下的世界,仿佛自己是一位主宰者,这也使《梦天》一诗给我们带来一种超然物外的错觉。
你看“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沧海桑田,尘寰变迁,令人唏嘘。读《天上谣》一诗,一个瑰丽奇幻的天庭便立于眼前。
在李贺的鬼神世界里,他是一位“旁观者”,并不置于人世之中。奇诡是他赋予诗的特性,超然是他赋予情感的外露。然而,这仅仅浮于表面的实质,实则是他的伪装。因现实苦闷,他不得已一头扎进幻想的美好世界;因情感复杂,他不堪烦忧才假意洒脱。
我们不难想象,一位受他人妒才而与仕途无缘之人,会有什么归宿?被排挤打压,被消磨殆尽……当热情被耗尽,他仅存的一副躯壳,也须得承受那些没来由的愁苦。本该是天之骄子,却落得提笔摹鬼神,把诗诉衷肠的下场。究竟什么才能寄托他的愁思?无非幻想。
——于是,郁郁而终的时光里,他倒戈在虚渺之中。
梅花的花期开放又凋零,李贺的故事结束又延续。在经历了本不该降临到他们身上的苦难后,他们的立场得以改变。一次堆积的迸发,击碎原以为正确的坚持,在洪流中慢慢溃散。以原先未曾设想过的方式藏起了梅的坚韧,藏起了李贺的忠贞。取而代之,将梅软弱和李贺颓然的一面展现出来。
梅经受凌寒固然喜春,李贺受挫后无奈沉沦。无论是习性使然还是时势所趋,在一条望不到头的路上坚持了许久,恰巧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堵在面前,迫使他们缓缓脱下那层沉重的外衣。既然,继续坚持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退让也就无可厚非。
无论是“梅”还是“李贺”,置身在这个世界,允许执着的人投身于他所坚持的,也允许动摇的人倒戈在他所向往的。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大赛为期一年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