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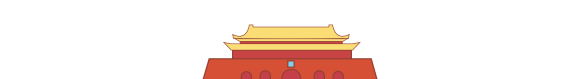

老宅的古榉树
文/吕天文
孩提年代,总喜欢到老宅屋后的那颗古榉树下玩耍。每到放暑假了,邻里间的孩子都把这里当作乐园,从事着划拳头、捉虫子、捣鸟窝、寻鸟蛋等一些娱乐活动。
据林业专家测算,老宅榉树的树龄已达七百多年。它高达二十多米,树粗需用几人牵手合抱,遮幅方圆半亩有余。周围长满许多蔬密均匀、大小相等的楠竹,看上去像一列列威武的士兵,时时保护着它的生命安全。
夏天,孩子们为什么喜欢选择在榉树下面追逐戏打。因为它遮荫面积大,太阳晒不到,非常凉爽。
最有趣但又心有芥蒂的是那次我和隔壁家的孩子大佬、二佬,还有三叔家的朋朋几个人来到榉树下,看见一群鸟儿正在树桠上的窝巢里叽叽喳喳地鸣叫,大佬不知从哪找来一根长竹竿,爬上树的半腰,捣起那鸟窝来。鸟儿一阵惊吓,从一枝树桠飞到另一枝树桠,逼迫着离开自己栖息的家。随着鸟窝的戳散,忽然朋朋板起面孔,大声地训斥大佬起来:“那是鸟儿的家,你莫再捣了,它们会伤心的,我们要与鸟儿和诣相处,你不懂吗?”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鸟窝已经戳散,只能留下遗憾。一些橙黄、斑黑的鸟蛋随即掉下来,有的被摔破,有的掉在草丛中完好无损。我们在地上找着找着,乐趣中又不免生出怜悯和悲伤来。
榉树生长在斜坡下,攀爬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滑脚、栽跟头现象。
记得满十岁的那年,刚放暑假的时候,我和邻里佰母家的孩子“祥子”在榉树下相互追打,追着追着,他一不小心,双脚踩空,栽了两个倒八叉,屁股被派生出的小榉树桩戳伤,弄得鼻清脸肿,鲜血直流,整个屁股都血肉模糊起来。一向很坚强的“祥子”虽没有喊爹叫娘的哭,但他却急得往家里跑。他栽跟头虽不是我的主要责任,可必竟是相互戏打而为。此时我有些害怕,不得不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母亲。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鼻梁,嘴里念着“紧箍咒”。骂了一顿后,三步并两步地就往佰母家奔去。哪知佰母不但不抱怨我,反而还给我和母亲各递根新鲜的黄瓜,“祥子”则坐在沙发上咪笑地望着我。我看到母亲将一叠钱向佰母手里塞,叫她给“祥子”弄点药去。佰母推来推去,硬是不收,只听得她提高嗓门对着母亲说:“小孩子玩耍依不得的,你儿子又不是故意的,况且也没什么大碍!”
回到家里,我为佰母的大度而感到震惊,当然也与母亲平时邻里关糸处里得好而自豪。如果换一个人,也许就要赔很多钱,不会像今天这样幸运了。自那次后,我幼小的心灵已懂得任性的结果是什么?也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
榉树下不仅是孩子们的乐园,而且是大人们常休憩的好地方。特别是三伏天里,榉树的树冠像一把巨伞把太阳光遮得严严实实。乡邻们坐在树下乘凉,不是谈婚论嫁,就是谈生老病死;谈天干雨旱,作物生长。年长一点的则讲着榉树的来源,我曾聆听二爹爹说过榉树的所有权问题,这树到他太太手里时,树还属他们私有;但到了祖祖手里时,树就充公到集体来了;再后来,县林业局的人将其作为古树和二级植物挂牌保护起来,就变成国有的了。
当然最让我铭记于心的是,有次我和几个孩子到榉树下面玩耍,路过居住在榉树下面有个小名叫“张跛子”的菜地时,不小心踩死了她种的白菜,除了被她一顿臭骂外,她还跑到我家向母亲告状,非逼得母亲和我向她赔了不是。但后来我又一想,反倒不狠起她来了,她虽伤了我的自尊心,但必竟是我错在先,况且她是个瘸子,残疾人吗,我们应该要尊重才是。
榉树上还成了鸟儿的天堂。每到冬天,成群的白鸽嗅觉到树叶的芬芳,从北方展着翅膀,迁徙飞来,在这里栖息,与众鸟儿一起表演起“大合唱,”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看到古榉树下很阴凉,乡邻们就在它下面凿了个水井,水井用石头垒成,大约有七八米深。自从有水井以来,滴水清冽甘甜,叮咚地流淌不断,从没干枯过。即便睛个把两个月,仍若无其事。想起四年前那段久旱不雨的日子,山上的树烤焦了,河里的水也干枯了,山沟沟的浸水也断流了,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启动应急机制,用车送水来满足生活需要。而老宅榉树下的水井仍然波光粼粼,召来几里之外的乡邻都挣着来这里挑水,见证了它的生态价值。
自从榉树在县林业局有了账号,特别是遇到久旱不雨,水井仍保持着它不干枯的灵气,乡邻们管它叫神仙树、菩萨树、幸福树,当作神龛中的神灵来看待。就连周围的楠竹都怕砍了破相,只有在它长得稠密时,才适当的抽砍一层,这对于杂夹生长在楠竹中间的榉树而言相当于是一次“理发。”
九十年代初,榉树以其稀有、珍贵、坚硬、细腻、光泽的特点红火于木材市场,如果是古榉树,更是价值连城。
那是我在县林业局工作,下属的木材公司曾有人多次要我牵头做乡邻们工作,把榉树给卖了,他们负责办采伐手续,生意谈成后,负责修一座石拱桥,以方便隔河两岸的人出行。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林业工作者,保护森林是我的主要职责,不能做出以牺牲老家榉树为代价的事情来。他们见我这一关过不了,就派人到乡里邻居那里游说。哪知乡邻们态度坚如磐石,无懈可击,有着保护榉树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的决心,就这样那颗古榉树总算逃过了一劫。
除了有人打着想发财的馊主意对榉树垂涎三尺外,病虫害的入侵对榉树的生长,也构成了威胁。
在一次古树资源普查中,林业科学工作者们发现此榉树得了“褐斑病,”有提早落叶和早衰的现象。乡邻们得知情况后,捉的捉虫,喷的喷药,忙得不亦乐呼。
遗憾的是,在我二十岁的那年,两个惊天炸雷,劈断了榉树两根粗壮的枝条,至今还留下了它饱经沦桑的伤口。
如今,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一声春雷炸响,村村组组都通了公路,隔河两岸架通了桥梁,那颗古榉树也变成一处风景,正吸引不少前来的人打卡观赏。回想起来,幸好当时没做糊涂事,乡邻们也没为那个诱惑的条件而动心。否则,无论是我还是他们,都将成为不可饶恕的罪人。
每每回到乡下老宅,瞧那长满青苔、缠满青藤、历经风吹雨打,雪压雷劈,仍根系发达、枝叶繁茂的榉树,心中不由生起惆怅来:视树为命,生我养我的父母,我常挂在嘴边的佰母和二爹,柱着拐杖的长者们,还有那个曾经让我受委曲的张跛子……他们都犹如宇宙中的一颗微粒驾鹤西去,留下几分悲凉。物是人非下,让人发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慨。
一颗古榉树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我想,要知道它的高洁品格,惟有借清.郑燮的一首诗《竹石》来作为对它的礼赞:“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作者简介:
吕天文,现供职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林业局,有文学作品散发于《中国绿色时报》、《湖南日报》、《中国乡村杂志》、《团结报》、《张家界日报》、《林业与生态》及网络平台。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大赛为期一年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