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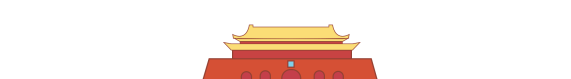

从“清油灯”到“通明美亮”
文/曾照元
从清油灯走到通明美亮,而今已是花甲年岁了。
大概六七岁的样子,随父亲在二伯家吃过晚饭准备回家,打开门一看外面黑漆漆的,赶紧退到父亲身后,两只手拉拽着衣角不敢出门。
“我怕!”“黑夜里有鬼!”父亲收住脚。
二妈嘱咐我们再坐一会儿。见她上身微屈端走供桌上的清油灯往厨屋走,并伸一只手遮护着火苗。二伯也跟去了。
二妈的动作见多了,每家每夜都有,各家有各家的角色,多为女性,年老女性最合适,稳重且心细。我做不来,一是弯不下身,二是遮护不周,不晓得见风思变。昔日的住房关不住风,窗子、门缝、山头、前后屋檐都可以进风,需要根据它们的方位来变换挡风的手势,否则灯吹灭了,一家人都成了睁眼瞎。
过了一小会儿,二伯点燃了像扁担那长的火把递给父亲。父亲一手牵着我一手打着火把,在弯曲的田埂上晃动着。还没走到八亩埂火光突然没了,父亲立马挥动火把将风招来,也拯救了火光。
那些日子,每家每户都是用小碗清油熬过来的,那叫一个清苦。白天也一样,劳累比夜晚更明朗些。
像犁田、操田、耙田、割稻、打稻、插秧、耘草、治虫,没有一样不咬人。先说用牛吧,队里老金头每次用牛回来,衣服汗湿透了,前胸后背巴贴着难受,泥巴星子溅一身,脏兮兮的。同样干一天活,别人的衣服看不出有多脏,到歇畔的时候歇畔,到吃饭的时候回家吃饭,可老金头还得起早摸晚割牛草,放工了还得牵牛饮水给牛喂食。
再说割稻,那练的就是蛤蟆功,三五个女的依次下田,下身半蹲上身前扑,左手抓捏右手挥镰,有的一行六株,有的两行一放。遇到长田一趟稻子割下来已经累得够呛,一天下来真的直不起腰。
不知道是读小学几年级,上下传的沸沸扬扬,说是要给大家按电灯。电的到来,逐步改变了生活环境,逐渐提升了生活质量,也降低了人们的劳动强度。
几年后,铁牛代替了耕牛,电打稻机代替了脚踩打稻机,省时又省力,劳动效率倍增。
就说铁牛吧,它吃油不吃草,省去了大把割草时间。我小时候怕割牛草,你不知道草它割手,跟草长在一起的藤藤蔓蔓稍不留神会扎你一下,有时像猫抓的那样留下一指伤痕。最关键的是铁牛效率高,它一天干的活用耕牛至少十天半个月。使用电打稻机不用脚踩,同样省时省力又增效。
有了电的农家渐渐热闹起来。收录机、黑白电视丰富了人们精神生活,听的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家里的固定电话方便了与外界联络,找人帮忙、接客喝酒、谈话沟通,不管远近足不出户均能如愿。电熨斗、电饭锅、洗衣机等深受家庭妇女喜爱,常在一起谈论“电”的神奇与功用。
母亲最爱洗衣机。有了它,母亲不用每天拎一篮子衣服往河边跑,不用一件件槌一件件清洗。
如今,电的发展更带劲儿。农村有了插秧机、收割机,黑白电视被液晶彩电替代,智能手机更是用处广泛、奇妙无穷。
出去走走吧,选择在开发区转转。一座座厂房热闹非凡,各种机器发出的声响合奏出欢快的乐章,像为敬业工人歌唱,又像为产品效益颂歌。走进一家超市,乘电梯上下,观商品琳琅。商贸中心商铺繁多,电子广告夺目招客。举目四望闻八方来声,可叹商贸街兴旺繁华!
夜幕降临,商场是亮的,街市是亮的,小区是亮的,道路是亮的,厂区是亮的,公厕是亮的,人心是亮的。
人心亮,家乡何处不闪亮。卢湖大坝站着亮,卢湖水下倒着亮,坝上坝下比着亮,来往车辆跑着亮。竹海深处躲着亮,农家小屋闪着亮,停车场上列队亮,笄山顶上仰着亮。竹乡画廊美着亮,康养福地分外亮,行政区域暖心亮,旧城改造透新亮。灵山秀景、牛山云景、高铁车站、滨河乐园、天寿寺塔、森林公园、恩施茅田……可谓亮点多多,吸引游客往来不绝!
从清油灯走到通明美亮,家乡变得如此亮丽,首当致敬点亮2165平方公里的这群人——可爱的广德电力人!
是他们照亮我们的生活,点亮人们的信心与思路,保障城乡发展与时俱进!
拆旧建新需要他们,新厂建投需要他们,改道扩宽需要他们,亮化美化需要他们,文明创建需要他们,居家故障需要他们,低压消缺需要他们,农网改造需要他们,灾害降临需要他们,不管高温蒸烤还是寒风刺骨,不管阴雨连绵还是大雪铺盖,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无时不在,随唤随到。
都说电如老虎会咬人。而我们的电力人就爱跟老虎打交道,不惧高不嫌脏不怕累,爱岗敬业,织网护航!
从清油灯走到通明美亮,让人难忘的一幕铭刻心底:在又高又粗的水泥圆杆上,电力师傅戴一顶蓝色或粉红的头盔,着一身蓝色或灰色的工作服,一条擦汗的毛巾绕在脖子上,一张脸晒得黑红黑红的。
这样的情景我见了好多次,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好几个。是那么高,不敢往上看,可心里头又想看,十分敬佩地去看。虽然每次看的时间很短,但我会用同样的方式作别:站姿庄重,表情严肃,昂首挺胸,行礼致敬——辛苦了!你们是最美的劳动人!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大赛为期一年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