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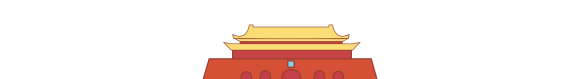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
文/孙至圣
父亲在我们眼里是深沉的,是严肃甚至严厉的。
当我和姐姐还是年幼无知的小孩时,就非常惧怕父亲,所以在父亲面前的我们从来不敢放肆。
小时候我和姐姐调皮在被父亲看到之后,总会在父亲数一二三,三个数之后迅速地停下手中一切动作不敢调皮。然而父亲这样的严厉使得我从小便与父亲之间形成深深浅浅的隔阂。这种隔阂仅仅是来自父亲的严厉么,我至今无法说清。
依稀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们上街,每次上街总是在父亲数次问我们想吃什么想要什么之后,年幼的我们不像许多小孩不论跟着谁都无所顾忌地吵着闹着要吃的要玩的。恰恰相反,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得到我们坚持并且一致的回答: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吃。
其实,那时的我们和许多顽皮的馋嘴猫一样,都有着对各种零食的憧憬向往甚至渴望,但那时的我们就是违心地不要,因为和父亲生疏,所以不敢要。
现在常想,彼时,年幼的我们竟有着那样一颗敏感而细腻的心,竟在骨肉亲情间所表现出的本能羞涩是那么的难以言喻。也常想,彼时的父亲又是那样的严厉,以致于年幼我们和父亲不敢表达想法和需求。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我们的成长,父亲从未改变过他严厉的做事风格,然而父亲的严厉但却多了些浪漫的色彩。同时渐渐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亲的生疏感逐渐减少。当我们懂事后,记忆中的父亲总是骑着一辆上世纪90年代的大梁车子带着我和姐姐去田野、去菜地。父亲在田间劳作,我在田间玩耍,风儿轻轻地吹,柳枝轻轻地摆,在这片地里,我们用照片记录下了童年的美好时光。
儿时的美好单薄的一切记忆中总会随着那张照片的出现清晰地再现在我脑海:树影下大片大片的金黄色的油菜花海,在油菜花海中间蹲着一个麦色皮肤的年轻人,年轻人嘴角露着浅浅的笑意,两边站着两个穿戴一模一样的小女孩,一人手中捏着一串油菜杆,小女孩在粉色的草帽下腼腆地抿着嘴,快乐凝固成永恒的微笑。
后来随着我们长大,上学后,父亲依然严厉,他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严格。他严格要求使我们在学习上不敢懈怠。他的严厉使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踏出坚硬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父亲的严厉始终未变,只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随着我们懂事以后,父亲不像对我们小的时候那样冷峻,我们和父亲的隔阂也渐渐磨合。父亲在岁月跌宕中洗净铅华后愈见流露出慈爱浪漫的一面,这种浪漫让我多年以后想起来都会颇为诧异,但这并没有让我们措手不及:或许父亲本身就是一个浪漫的人,只是迫于生活压力和经济负担,父亲总是一副严峻的样子,很少笑,很少带我们玩,也很少给我们买吃的。印象里,特别小的时候,和同龄人比,家里经济条件很差,这种状况在我们长到十几岁才好些。我觉得,成长里,父亲逐渐变得温和浪漫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得归结于,家境的好转。
后来记忆里的父亲明显有一些慈爱和情趣。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记得我们小学毕业后父亲带我们玩的经历。那天父亲下班回家,连饭都顾不上吃直接骑车带我们去城南的“小南海”---我们县唯一的蒙古语音译的大面积水域,是我们县城的地标,更是我和姐姐向往已久的天堂圣地。然而正是父亲,满足了我们小小的心愿。
也记得,父亲总是在春意盎然万物复苏的季节带着我和姐姐以及我家小狗在野外散步探春游玩,一路上小狗冲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那时的我们还年少,那段时间淳朴简单美好,那种记忆,也始终会是我人生荧幕中的重要剪影。
记忆中的父亲总是认真的,勤奋的,他对生活有着坚定的信仰,执着的信念。他坚持不懈的态度一直是我们成长历程中的美好榜样。由于他年少的时候家境贫寒而不得不在高中毕业后放弃学业,尽管失去上学的机会,父亲依然百折不挠地面对生活的考验。他年轻的岁月里布满荆棘,但在生活的困难面前,父亲从来不会轻易言败。
在生活里,父亲是个勇于承担生活责任的人。他的这一品质体现在两件事上,这我至今想起来都非常钦佩父亲。其中一件事是我年幼的时候家境贫寒,家里生活拮据,那时候,父亲为赚去一点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常常伏案写作赚取稿费来维持生计。记忆中父亲写作写到深夜我都睡醒一觉父亲的身影还在昏暗台灯下影影绰绰。时时在睡眼朦胧处看到,本来就瘦小的父亲在灯影显得更加下瘦弱不堪。我的父亲很瘦小,但是却很努力。父亲的勤奋努力换来的一叠叠证书成为许多年后,我和姐姐学习的榜样。现在偶尔想起那些年少不更事的我们找来毛笔把父亲奖状上的名字争先恐后地改成自己的名字的傻事就想发笑。
父亲的另一件让我钦佩的事是,在我们特别小的时候,为减轻生活负担,父亲毅然决然地把抽了许多年的烟戒了。这一件事让我们至今想起来,都怀着对父亲说不出的敬仰和感激。可以想象当时的父亲为了我们,为了生活,下了多大的决心,克服多大的困难。
后来呵,关于父亲,依然忘不了的是,我和姐姐上初中的第一年,父亲骑着摩托一天六趟地送我们上学放学,那时候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风中夹着雪,雪中裹中风,父亲在寒风中风雨无阻地来去。依然忘不了,上大学时,父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坚持送我千里之外的西安,为我跑前跑后地安排,任劳任怨。依然忘不了,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父亲在北京西站接我,我们在西站小饭馆里吃饭时,父亲一直说着他和我妈是怎么样怎么样地想我,我不小心抬头看到父亲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闪啊闪的,泪眼模糊了视线……如今的我和姐姐在父亲的严格教育和影响下,都成为了高中的人民教师。这时的我们依然忘不了父亲的教导。
关于父亲呵,从来没有想过,所有的细节在我三十几岁里密密麻麻地回旋缠绕着一路走来的年年岁岁。
父爱如山,真是说也说不完,想也想不够。
作者简介:
孙至圣,毕业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爱好文学。曾任花开杂志的文编,作品散见于《张家口日报》《河北日报》《花开杂志》《燕山日报》《北京晚报》《长城文艺》,作品在各类征文中获奖,作品曾获得文学之心全国文学大赛36强。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大赛为期一年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