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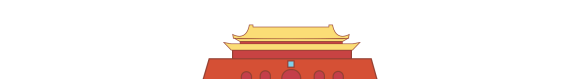

鱼腥草、折耳根、猪鼻拱
文/王莹
鱼腥草、折耳根、猪鼻拱,你们知道的它的名字还有哪些?不用我过多介绍,喜欢的很喜欢,讨厌的很讨厌!
我很庆幸,找的对象也爱吃,生的孩子目前算不上爱吃,但是不排斥,我相信在我们这样的饮食环境下,终有一天她会喜欢。为什么这么说呢?得从我自身经历讲起,作为四川人,我们也不是天生喜欢吃,小时候经常在爷爷奶奶家吃饭,开春那段时间,桌上总有一盘凉拌的鱼腥草,一开始也不喜欢,就是见它久了,总有些时候会好奇的要去尝一尝,慢慢的,也不知道是习惯,还是喜欢,总之就是能吃了。
再到后来上大学,结识了来自其他地方的四川、重庆的同学,大家出去吃路边的炸豆腐、烤鱼、洋芋花……里面除了常规的调料和香菜小葱,还有一样就是鱼腥草,而我也很少听说谁不爱吃,似乎是一种心理和味觉的本土融入,久而久之,我也会对老板儿说,“折耳根多来点儿”!
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四川,辗转到了山东、福建、湖南、上海工作,日常吃的都是食堂,偶尔出去吃也都是各大地方的特色菜系,鱼腥草便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偶尔还是会想起它,但当下的时节和地方条件都不允许,也就作罢了。
我以为它对我而言不过是一道菜,看不见了可以不想,吃不到了可以不念。确实也是如此,但忽略了看见它吃上它的时候,仍然会大快朵颐吃个尽兴。我们来陕西定居也好几年了,偶尔逛菜市场会看到鱼腥草,但是都特别老,吃起来口感不佳,可是我依然控制不了的要拿到手上闻一闻,掐一下根部试试老嫩,鱼腥草的汁儿便渗到指甲缝里,即便我没买,走后的一路,我都会把手放到鼻子前,使劲儿嗅它的味道,那是一种难以言喻、或臭或香的味道,掺杂着对家乡的思念!
老公的老家在重庆丰都,一到春节,田坎上长满了嫩嫩小小的鱼腥草。有一年寒假回去遇到了他远在广州的堂姐,堂姐难得回老家一次,一回来就寻着各种工具,镰刀、小锄头,挎着小篮子,兴奋的号召着一群小朋友出去挖折耳根了。回来的时候是满满的一篮子,我看了看,还有点看不上,因为有点老了,可她却如同宝贝般的觉得很开心,说在外多年就想这个味道。
前些年过年返渭的时候,从家里带了一些鱼腥草,请朋友到家吃饭时,自然想着和他们分享一些“特别”的家乡美食,一上桌,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大家都兴致勃勃,可手上的筷子却畏畏缩缩,在我的鼓励下,他们勇敢的夹起一小根放到嘴里,那一脸狰狞就表明了对它的态度,我一筷子夹起一大簇放进嘴里,津津有味的吃起来,一边念叨“这多好吃呀!”,引来他们“崇拜”的目光,能这么吃的都是狠人!从此,我让他们的禁食名单里多了一样,鱼腥草!
近日,我妈学会了卤牛肉,蘸料的灵魂就是鱼腥草,切成细细的末,伴着辣椒酱油醋,有点酸有点甜,还有一点鲜,每一片牛肉都包裹着满满的鱼腥草调料,放进嘴里,仿佛是美味在旅行,连着吃了好几天都不腻。
还是那句话,喜欢的很喜欢,讨厌的很讨厌。
鱼腥草因为有了我们这些忠实粉丝的存在,还是很值得的生长的!
晚上吃的鱼腥草有感而发,却不想写成了一篇小作文,话有点多了!
作者简介:
王莹,研究生学历,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干事,热爱生活,喜欢写作。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大赛为期一年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