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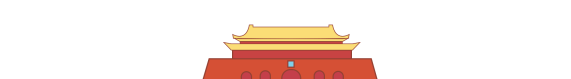

湖居
文/殷咏天
说湖居,实际是想说说临湖而居的感受。
2012年夏,我们搬入了满洲里紧邻北湖北岸的世纪金城新居,这是我们在满洲里第二次换房。那一年我们已来边城近20年,原本想让喜欢自然、特别是喜欢水的老母亲来此养老,也好弥补一下我们常年在外而不能尽孝的缺憾,但并未能如愿。母亲只在此住了一周,就坚决要回牙克石老宅 :“我知道你们对我好,这地方也确实挺好,但毕竟不是我的家呀!让我回去再想想吧。”就这样,直到过年问她想好了没有?回答是与预料一样:“还没想好”。我知道,母亲是离不开她的“家”了,因为这里有她大半生的记忆,怎么会轻易离开呢!而作儿女的“孝”,大多时候还是要以“顺”为前提的。由此,这一美好的湖景房也就由我们居住独享了。
首先是让我增添了生活内容,这应该感谢开发商赠送的二楼大平台,才会盖起了阳光房,进而才有了内外各两个木槽的绿色,也深深体味了生命的神奇。许是第一年新移来粪土的缘故,夏天内外一片葳蕤,悦目怡心。阳光房内小白菜水灵灵,水萝卜脆生生;阳光房外阳台上西红柿枝弯,青梗菜滴翠……秋深冬近,外面木槽里早已是叶落秧枯,一派萧索。然而阳光房内却仍是一片盎然;小白菜和水萝卜罢园后,第二茬种的黄瓜又很快成长起来,尤其是槽中间的一棵十分茂盛,竟长到一人多高,黄瓜一根接一根,差不多繁荣了一冬,自然我们也没断了新鲜菜蔬。
那一阵儿的确是有了很惬意的时光。工作劳累一天之后,在满目冰雪中回到家中,立即就会被一片绿色所陶醉,身心的疲惫也似乎消融了大半。业余笔耕,夜深人静,每当灵感消隐,或倦意袭来之时,来到阳光房内木槽前站上一会儿,似乎就又有了力量和启谕。
然而变化无常。第二年春天,室外的木槽尚无异常,但室内的木槽却像犯病一般,无论种啥都出苗不齐,即使出来的苗也一副病歪歪的样子,几经浇灌和施肥也无济于事。但一种野生植物却疯长起来,起初我们发现后即铲除掉了,但两三天便又生出一茬,后来索性就只好让位于这顽强的“不速之客”了。经查,其叫马齿苋,俗称”不老草”,是很好的养生野菜。也真是名副其实:铲掉的不老草如果放到槽内边上,不两天就又生根挺拔起来;即使放在阳光下暴晒一天也不会死。从此以后我们没少吃凉拌不老草,虽味道不佳,但想想其药用价值和这种现象,也就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这么多的不老草种子从何而来?取土的地方并未发现有他的身影;如果是从土中带来,为什么第一年不见一颗发芽?为何一草兴旺,百蔬不荣?世界之奥妙真的是难以理解。
阳光房冬天可以说是“屋子里的春天”,但一到夏天晴日却酷热难耐,甚至影响到了客厅,不得不拉上厚厚的帘布阻隔。但事物总是利弊相生、阴阳互补的。家中养的仙人球原本生长缓慢,开花稀少,但自从搬入阳光房后,就开花不断,小仙人球层出不穷,甚至到了为难的地步:弃之不忍,养之已是盆满为患;临近的一盆茉莉花也花朵满枝,香气盈室。于是本不怎么喝茶的我,也自调起了新鲜的茉莉花茶,每品一口都清香唇齿,回味绵长。
湖居不仅是有园圃之乐,更有开阔视野和眺望的享受。过了大年,出了正月,春光咋暖。这时眼瞅着雪白的北湖冰面开始变灰、变黑,然后北岸边慢慢融出水来,并向中间渐渐扩大。到了四月中旬左右,眼前就变成了盈盈春水了。虽是咋暖还寒时节,但迁徙的候鸟却如期而至,在水面游弋着,鸣叫着,像欢呼着春天的到来,更像呼唤着春天的圆满。这不,唤着唤着,湖岸便萌出了绿意,正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那种;岸畔杨柳也争着秀出了浅绿的眉眼,望出去便有了几分“拂堤杨柳醉春烟”的意味。天暖了,跑步的、遛弯的、游园的……这里不是北湖公园正门,既少了几分喧闹,又不显得冷清,于居住、于观景,真可谓适中恰宜了。
到了夏日,游人涌至。北湖北岸是观赏边城夜景的最佳地,二楼阳台或阳光房自然是“更上一层楼”了。夜幕降临,环湖灯光璀璨,尤其是西南一片,灯焕七彩,高低错落,星衬波摇,如梦似幻……有人说像外滩景色;有人说像到了维多利亚海湾;还有人说像到了拉斯维加斯……每当听到这些溢美之词,为家乡而自豪之情便会油然而生,也为湖居而多了几分骄傲。而清晨或傍晚这里自然成了散心和纳凉的好去处。人们或湖上泛舟,桨声霞影;或一竿垂钓,心惬景幽;或双双椅偎,情意融融……生活的亮点在窗前频频展现。
及至秋来,看着树叶一点点儿脱色变黄,或变红、变紫,然后在萧萧秋风中飒飒而落,总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悄然而至。每至此,我就会想到“悲秋”一词。自从宋玉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后,似乎就定下了悲秋的基调。几千年来尽管有“我言秋色胜春潮”和“不是春光,胜似春光”的放达高唱,但终未能减少绝大多数人的心底凉绪。于是便常思忖:这是为什么呢?本来春萌、夏长、秋收、冬藏,就是个节令时序的轮回过程,就像人的生死也是个必然的过程,本无需有没必要的悲情愁绪。那么这种悲凉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因对死后的无知而恐惧和焦虑呢?这不禁让自己由此一再想到“形而上”的问题,想到了如何“面死而生”,如何让信仰支撑起灵魂的高蹈和永恒的自由……也许这该是湖居最大的收获吧!
冬季的北湖则冰封雪裹,满目凛冽,是另一番冷峻的景象。但隔窗而眺,这一片冷寂却偏能生出许多诗意来——那冰面上踩出的一条窄窄的小路,一直伸向南岸并消失在冬霭之中,瞩望久了,忽而像幻化出的一根坚韧的绳索,要把隆冬紧紧勒住;那胡须挂满冰霜的晨练人,每日都按时出现在冰冷的岸畔,他显得那样孤寂而又决绝,像怀着一种特殊使命,于是一个诗题《踽踽独行的人》便水到渠成;夜长昼短,阳光显得十分可贵,特别是2014年二线之后,我常在阳光房内看书,看着看着,下午的阳光就不知不觉悄悄低远、暗了下去,但我的笔下却汩汩地流淌出了《冬日的阳光》……即使后来到了南海边,仍然受到当时的影响:“天黑透了,黎明就会隆隆启程;地冻透了,春风就会打点习习的行装……”
由此也引发了更多的思索。“天人合一”是否有着更深刻、更繁复的内涵呢?比如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有阴晴雨雪,人有悲欢离合;天有寒暑交替,人有顺逆转圜;天有难解之象,人有无妄之灾……由此思之,便对自己卸任后的意外境遇、病痛的突袭折磨有了释怀的出口,这或许也是湖居给我的另一种深深的启谕吧!
还是回到事物的两面性,阳光房总体不错,但却也有麻烦处。夏天还好办,但冬天需要早上开窗通风,晚上关窗保温。2014年起我们经常在海南或云南过冬,只好将阳光房委托好友或同事打理,时间一长很是过意不去,加之需要回牙克石陪老母尽孝,在满洲里的时光很少,于是还是在2017年夏不舍地卖掉了湖居。
在告别湖居离开满洲里的时候,正是“天苍苍,秋草黄”时节。途中,泛黄的巴尔虎草原起伏着向后迅疾地退去,像是向后追赶在边城倏忽逝去的二十多年的难忘时光。许多的人,许多的事纷至沓来,交相穿插,百味难陈。其中鲜明的就有满槽的不老草、疯长的仙人球、馥郁的茉莉花,还有阳光房中数米的阳光,在我眼前一再闪亮……

作者简介:
殷咏天,笔名:古木,曾在《草原》《散文诗》《青年文学家》等刊发作品,曾出版诗集《灵悟》和散文诗集《心灵的高原》,并有多篇作品获奖和入书;其中曾获第三届“翰章杯”新锐奖等;曾入选香港《九十年代短诗选》、《三新诗选》等。倡导作品要“兴、观、群、怨”,瞭望时代,洗涤心灵。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大赛为期一年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