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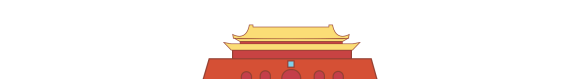

父亲的“战马”
文/李梅
在往昔的回忆深处,有一件物品始终萦绕于心田,那便是父亲的“岁月伙伴”——一辆28寸的自行车。
父亲的自行车车身涂满了宁静的蓝色,车架高大且坚固,仿佛是专为父亲这样的高个子量身打造。车把一侧悬挂着一只小巧的铃铛,每当那清脆悦耳的铃声悠扬响起,那便是爸爸即将启程的信号。
在一个月光柔和的夏夜,父亲借着那盏光线虽弱却暖意融融的煤油灯火,手握一支细长的单锋毛笔,笔端轻点上一抹鲜艳的红色漆料,在那辆自行车的后轮保护盖上,细致入微地写上“战马”二字。这两个遒劲有力的汉字,犹如为那辆自行车注入了勃勃生机。
在我印象中,父亲骑自行车时,他那标志性的上车动作,总是那么一气呵成。他左脚轻踏左侧踏板,两手稳推车身,右脚轻点地面数步,随后身躯前倾,右腿后扬,宛如蓄势待发的箭矢,瞬间高扬、精准回扣,身体与自行车车完美融合,稳稳落座于鞍上,右脚亦恰好踏足右侧踏板。这一系列动作,父亲已将其锤炼成一套行云流水般的艺术。
父亲是一名乡村医生,时常骑着他的“战马”外出诊疗。无论是在炽热难耐的夏天,还是在冰冷刺骨的冬天,这辆自行车始终是他最可靠的伙伴。记得有一回,在深夜时分,邻近村落的张阿姨误食了不明种类的蘑菇,出现了呕吐、腹痛和腹泻的症状,爸爸一听闻消息,立刻跃上他的“战马”风尘仆仆赶到了张阿姨家,为她进行了初步的治疗并稳定了病情。在那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了父亲身为医生的责任和担当,也愈发钦佩他那辆始终相伴的自行车。
童年时候,江口镇的电影院是我们这些孩子心中的圣地。曾记得1982年的夏天,当《少林寺》这部武侠巨制首次闪耀荧屏时,它如同一股清新的武侠风,吹进我们那个边远的小村庄。几位老师和村干部,还有我的父亲,在一番商议之后,心中怀着对电影的热爱与期盼,兴高采烈地前往江口看电影。一行骑着自行车的队伍,一路撒下清脆悦耳的叮铃铃叮铃铃的铃声,真是气势不凡。而我也有幸被父亲带上,为了避免后座横杠使我屁股感到不适,细心的父亲特意在后座上垫上一条柔软的毛巾。
转眼间,我到了上初中的年龄。经过努力,我被江口的重点初中录取。父亲一听到这个好消息,为了鼓励我,为我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引人注目的红色女式凤凰牌自行车,车身光彩夺目,父亲还专门帮我安装一个别致的车头篮子,并在暑假教我学骑自行车。父亲稳稳地扶住后座,让我先试着蹬踏,在父亲的鼓励和指导下,我逐渐找到了平衡感,刚开始只能独自骑行几米远,虽然过程中也摔了几跤,但每次跌倒后都有父亲那双温暖的大手将我扶起。那个暑假,我学会了骑车,从中也学会了勇敢和坚持。
初中开学了,是父亲亲自送我去学校的。他骑车在前面,我跟在他后面。他的“战马”后座上,用坚韧的胶带绑着一个木制箱子(那时我们习惯称之为“木笼”)里面装着我的衣物和生活用品,箱子表面覆盖着一层细腻的光油,在阳光下闪烁着温润而低调的光芒,木箱上还绑着半蛇皮袋大米。
上初中的那条路,凹凸颠簸,由于长时间未降雨,黄土漫天飞扬,但父亲如同一位无畏的骑士一直向前。汗水,如同细雨般悄无声息地浸透了他的衣衫......他的双腿有力地蹬踏着,脚下的链条发出阵阵有节奏的“咔嗒”声。父亲的身体微微前倾,双手稳稳地握住车把,目光坚定而深邃,仿佛前方有着无尽的目标等待他去征服。瞬间,我觉得那辆自行车就是父亲的战马,和他一同驰骋在生活的征途上。
去到学校,父亲便忙碌地穿梭于校园各个角落。从财务室细心地交纳学费,到注册处耐心地完成各项手续,他的身影始终忙碌而专注。随后,他又细心地为我整理床铺,还亲自前往食堂,为我交上半袋沉甸甸的大米,以确保我在学校期间能够睡得好、吃得饱。我默默地凝视着父亲那稳重的背影,他的步伐虽显疲惫,却异常坚定有力。
读到初二时,我遭遇了频繁且量大的流鼻血困扰。得知我这一情况后,父亲亲自到菜市场选购了猪鼻子、莲藕节以及席草等材料,熬制成一碗碗温热的汤品,每隔数日,就骑着他的“战马”不辞辛劳地将汤送到学校,确保我能按时饮用。这样的坚持,直至我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流鼻血的现象彻底消失。每每望着他和那匹“战马”消失在校园拐角,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失落和痛楚。
次年,弟弟也上初中了。于是,父亲将他的“战马”给了弟弟上学,自己则踏上了步行出诊的道路。尽管失去了自行车的辅助,但父亲的步伐依旧稳健而有力,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满溢着对病患的深切关怀与责任感。每当我看见父亲肩扛沉甸甸的药箱,在乡间小径上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行,心中便会被一股温暖与深深的崇敬之情充盈着。
记得那年的一天清晨,父亲早早起床告诉我,今天要带我去江口交公粮。那时的我对交公粮还一无所知,但内心却充满了兴奋与期待。那天早晨,阳光炽烈,父亲将自行车推到天井中央,稳稳地撑好脚撑。随后,他将沉甸甸的稻谷搬上自行车的后座,并不断捶打着,然后用力拉紧胶带,将稻谷牢牢地固定好,以防路上掉落。
出发了,父亲费力地推着车,我紧跟在他身后帮扶着,小脸上写满了认真与好奇。沿途,稻谷的香气与父亲身上的汗水味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农人的辛勤与付出。我们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前行,一路颠簸,刚来到木桥,天空却突然乌云密布,木桥四周并无避雨之处。父亲停下脚步,用身体支撑着车身,同时用手紧紧扶住后座的公粮。我看着父亲满头的大汗如断线的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滑落,呼呼的大风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心里既担心又惊慌。父亲试图让我帮忙稳住自行车,但我力气太小,无法完成任务,急得几乎要哭出来。就在这时,一位同样前来送公粮的陌生伯伯出现了。他拉着木车,见状便放下车柄,跑过来帮忙。我们连忙向这位伯伯道谢,他憨厚地笑着,没有多说什么便走开了。父亲早有准备,从挎包里拿出三张雨衣。他先帮我披上一张,仔细地扎好,然后又用另一张盖在公粮上,四角都牢牢地扎在车身上,最后才自己披上一张雨衣。
雨停后,父亲首先检查公粮是否淋湿。然而,雨后的路却变得异常难走,厚厚的黄泥巴卡在车轮上,让自行车动弹不得。那位伯伯见状,再次伸出援手,让我们把公粮放到他的木车上。父亲让我留在路边等他们回来,看着伯伯和父亲在泥泞中艰难地前行,我的鼻子一酸,眼眶不禁湿润了。
前几年,我陪伴父亲前往人民医院就诊,在医院里偶遇了村里的钟阿姨。她一瞧见我,便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告诉我她的老伴与我父亲是同学,并且提及了她当年的婚礼。阿姨回忆说,在她大婚之日,迎亲的队伍中众人都倾向于挑选轻便的嫁妆如木笼、棉被等以减轻负担,而我的父亲却主动站出来要求承担拉新娘的任务。她生动地描绘了当天的情景:父亲的自行车车头装饰着一朵鲜艳的大红花,后座绑着一条绣有大红喜字的柔软毛巾与一把黑色的迎亲伞,格外引人注目。宾客们还注意到了自行车后轮防护盖上的“战马”二字,纷纷给予了赞赏。阿姨接着说道,那时的父亲年轻力壮,即便是在上坡路段,她故意不下车增加难度,父亲也能够稳稳当当地骑行上去,让她毫无害怕之感。
聊着聊着,钟阿姨的眼眶泛起了泪影,带着几分伤感地说起她家老伴如今年老体弱,疾病缠身,而子女又都不在身边,每个月她都得跑医院帮他取药。现在,我父亲也住进了医院,她感叹着人老了总难免会遇到这样的境况……我没有打断她的话,只是静静地聆听着她的诉说。这时,钟阿姨突然松开了我的手,让我稍等片刻,转身快步走向小卖部买了一个利是袋,封好红包后,请我带她去见我的父亲。当她见到我的父亲,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大家都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不由得转过头去,默默擦去眼角即将滑落的泪滴。
如今,那辆曾伴随父亲多年的自行车,已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被静静地放置在院子的角落。但在我心中,它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它见证了爸爸一生的奋斗和奉献。每当忆起与父亲和自行车相关的往昔,我都会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那辆自行车不仅是父亲的得力助手,更是我们全家珍贵的记忆。每当我重拾起那些零星细碎的记忆片段,那辆承载着丰富故事的自行车,那条伴我成长的上学之路,以及父亲被汗水浸透的背影,都会在内心深处泛起层层涟漪,涌动起一股既温馨又坚韧的力量。
作者简介:
李梅,热爱阅读写作,有作品散见于《三月三》《当代广西》《贵港日报》《领导月读》等报刊及网络媒体。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截稿日期:2025年3月31日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