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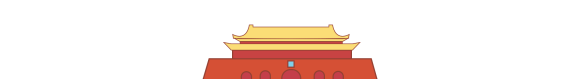

难忘故乡袅袅的炊烟
文/范源清
今天清早,我沿着龙湾环山公路散步,忽然被路旁厂房里飘出的炊烟所吸引,多么亲切的炊烟啊!我似乎很久不见炊烟了,它缥缈如云,朦胧如梦,清远如笛,仿佛西施浣纱时,信手放飞的一缕缕轻纱,在或蓝或红的屋瓦上,在渐浓的暮色里,盘旋、萦绕、写意、舞蹈……让我遥想起那些炊烟中飘散的过往和快乐的童年,恍惚让我回到了故乡,心中涌起一种极为踏实的温暖……
我的家乡是永嘉场颇有名气的一个自然村落,东临东海海滩,西近大罗山山麓,长期以来,由于一天两次潮涨潮落,汹涌澎湃的潮水跟北边来的瓯江水,西边来的多条水沥的水流交汇冲击,使塗滩形成了许多条条块块。塗滩上便有南沙、北沙、江正沙、上爿沙、下爿沙五条大沙垄和五条水渎(俗称沙渎)。先民们根据这种独特的地貌,就将自己的村庄取名为“五溪沙”。
那时的家乡大地上除了一些烧砖瓦窑外,几乎看不到工厂的影子,田垟还是一爿爿地连着,很空旷,很有野味。人们沿着曲曲折折的河岸走时,田野上会不时吹来习习的晨风,教人觉得凉爽舒畅,想起来这风也很独特,除了甜甜的清新泥土味外,还混合着一种淡淡的海腥味,这味儿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那时候家乡的人们都是靠种地为生,田地是农民的根,吃的食物都是自己种的,一日三餐的饭都是自家煮的,家家户户家里都有一口或多口土锅灶,煮饭柴料都来自田地里的稻草等!每当早上、中午、晚上时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故乡那袅袅的炊烟,那浓浓的柴火味……
看到炊烟,我心中便涌起了一种久违相逢的亲情感。它若隐若现的柔姿里似乎闪现出妈妈在灶间忙碌的身影。饮烟下有我的老房子,老房子里有我勤劳朴实的母亲。母亲在,炊烟在;炊烟在,故乡在;故乡在,根就在。每每这时,母亲便在灶前忙碌着,一边蹲下身子往灶膛里续上柴火,一边坐在灶前拉风箱,随着风箱的抽动,发出有节奏的呼哒呼哒的声音,柴火在灶膛里燃烧着,照亮着,把母亲的脸渲染得彤红,有时候也呛得母亲喘不过气来。在那个年代,我们大多数人家里烧的是稻秆、麦秆、横豆秆、柴子秆、树叶等烂柴,特别是稻秆火力小,不经烧,易熄火。这种柴火也很容易捂烟,如果再加上沒晒干或是潮湿的烂柴,烟囱里的烟会往灶外散,母亲会被烟熏得直流泪,做顿饭真是又烟又呛很不容易。有时候为了让饭熟得快一些,我也会在母亲做饭时帮母亲拉风箱。
在我童年时,记得母亲经常对我说:“炊烟就是庄稼人灶火膛里开出的花,花一开就有饭菜吃,天天饭菜香,就是好日子”。那时候青葱懵懂的我,对母亲的话一知半解,每天在意的只是母亲又做了什么好吃的饭菜,对于一天三次从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并没有多少感动与思考,正所谓:“饥望炊烟眼欲穿,一心只想肚儿圆”。
有时候,袅袅的炊烟刚从屋顶爬起,便被赶来的轻风抓了个正着,或东拉,或西扯,但好像怎么也拽不动,炊烟的尾巴还是紧紧抓着屋顶,久久不肯离去。轻风好像有了新主意,一时从四面赶来,准备把炊烟连根拔起,但好像效果也不理想,因为除了少数被轻轻拔起,大多炊烟还是稳稳盘在屋顶上。
因为炊烟老不散去,我曾问过父亲,父亲的回答是因为炊烟有灵性。有灵性?我将信将疑,见过动物有灵性的,还没听过炊烟也有灵性。显然父亲看出了我的疑惑,便往屋顶盘着的炊烟指了指:“你看,它们是不是躲进了瓦缝里?”躲进瓦缝?我伸长脖子,认真望去,是哦,好像确实有那么点意思。原本快被抓走的炊烟,经轻风一吹,好像又重新钻进了瓦缝里,或窜到屋檐下。
看我理解了炊烟的“灵性”,父亲便接着给我讲炊烟的“团结”。风为什么吹不走炊烟,因为炊烟很团结,它们肩并肩手拉手,连成一片,风想一下吹散它,可不容易。说的时候父亲激情满满,像一位教者,教人新知,育人道理,又像个仅懂点生活的人自卖自夸。父亲还想继续卖弄下去,不过很快就闻到了炒菜的香味,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便不得不停下来,迎着母亲的声音和菜香味奔去。这便是我幼时对炊烟特别的记忆。
中午的炊烟,则是农事的生动写照。俗话说:“农家饭,十点半”。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岁月里的人们,少有钟表,所以外出劳作的农人,多喜欢看炊烟。远远看去,若是炊烟升起,很浓厚,那是刚生火,最多才煮饭;若是炊烟变淡,那应该是炒菜了;等炊烟散尽,那肯定菜饭都熟了。所以那时乡下流行一句话:饭不饭,看烟散。大意是想回家吃饭,要等屋顶的炊烟散去,就可以回去了。炊烟便成了当时最好的“时钟”。虽然很俗套,但却是老百姓长时间总结出来的经验。
在大多数的农闲时节,故乡的中午炊烟总是慢条斯理的升起,随后,男人们会三三俩俩聚拢在某一家商店里,喝着自家做的“白眼烧”、剥着花生米,谈天说地,从容闲适,怡然自得,处处散发着宁静、美好、和谐的生活气息。然而,当生活节奏慢下来的时候,时光却显得出奇的快,转眼就到了农忙时节。在繁忙的日子里,很少有人家升起中午的炊烟,即便有也是短促的几缕轻烟而已,更多的是为了抓紧时间抢收抢种,天不亮就上路,带足了晌午和饮水,午餐自然就在田间地头用餐。
黄昏的炊烟,薄暮冥冥,最具诗情与画意,也最能诠释“人间烟火”这个词,总能给人以强烈的归宿感。当夕阳湮红了乡村,炊烟缓缓蠕动,像是一幅水墨画,涂抹着安宁与闲适,炊烟缕缕升起,弯弯的,袅娜的,像母亲低垂的睫毛,把一切心事和梦收藏。结束了一天辛劳的农人,扛着犁具,赶着牛,远远就看到了自家院落正冒着袅袅炊烟时,那一刻,谁会不感到由衷的幸福呢?当村里的灯火次第亮了起来,小乡村宛如一帧水墨丹青,彰显着夜晚的安宁与闲适的时候。炊烟,便是家的代名词。我们的先民,是何等的睿智与伟大啊!这一点,仅仅从“家”的结构上便可体悟到。“家”是“冢”字中的点往上移,其意蕴就是升起直上蓝天的炊烟,这是生命、活力、和谐与希望的象征;可见,我们的先民,对“家”的理解是多么深刻,多有寓意啊!
炊烟是农户生活的真实写照,有时候,烧什么柴就出什么烟。如果某家烟囱里滚出来的是一团团黑烟,时续时断,说明烧的是稻秆柴;如果滚出来的烟黑一段灰一段,说明烧的是麦籽柴或者油菜籽柴;如果滚出来的烟先有点黑,后面都是青灰的,说明烧的是横豆秆柴;颜色淡灰的烟,烧的是竹片之类的柴;颜色又白又细,就一定是木块木片,这些柴称之为硬柴。硬柴是最难得的柴,平时做饭都烧“杂柴”,很少用硬柴,树枝、柴子秆等硬柴便堆放在房前屋后的屋檐下,待到逢年过节或做红白喜事时才拿出来烧。家乡人有一种“硬柴火煮饭,煮熟的饭特别香、好吃”的说法。硬柴火旺,意味着红红火火;硬柴不易熄火,尤其是大年初一,一旦熄火或者火不旺,就犯了大忌,让人心情极不爽快。
“锅里有煮的,烟囱有冒炊烟的”,成了家乡代代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做饭烧水需要柴,冬天取暖还是需要柴,柴火是生存的必备品。有柴烧与有米下锅一样重要,都是衡量一家人日子是否富裕的标准,甚至后来也就慢慢演变成了男女青年择偶的先决条件。
长大后,我离开故乡,在不见炊烟的钢筋水泥丛林里漂泊,那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城市生活让我感到疲惫和无助。然而,每当我看到那城市稀少的炊烟升起,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的炊烟,想起那青砖瓦房、乡间小路、田园里的春草、夏花、冬雪,想起童年时无忧无虑地在田野间奔跑、嬉戏,想起不惧酷暑在马路边一颗一颗的捡小石头,想起那竹林深处的家。假日里,买一张回乡的车票,走进久别的故园,想感受一下当年的烟火味,不过总找不到少年时见到的袅袅炊烟。现在电磁炉及煤气都已经进入千家万户,告别了那种用枯枝干叶做饭的场景,炊烟也就变成了一种遥远的乡土记忆。就算有一两家还烧点柴火,但炊烟却不肯再盘着屋顶飘逸,竟直奔向那淡蓝的天空。失去了炊烟的村子,好像也失去了曾经的灵气,变得干脆直接,甚至有点赤裸。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炊烟却在灯火阑珊处。
故乡的炊烟是我对家的思念,也是我对母亲的怀念。在那淡蓝色的炊烟中,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的身影,听到了母亲的呼唤。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经历了什么,那袅袅升起的炊烟都是我回家的路标,是我心灵的港湾。
作者简介:
范源清,男,195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从事中学教育教学工作41年,多次被评为各类先进。2000年被评为温州市优秀教师;2006年被评为首届《中国教育报》十佳作者;2007年被评为浙江省教科研先进;2009年被评为浙江省职教名师;2015年被评为温州市“百姓学习之星”。在学校教学工作中一边实践,一边学习教育科研知识,积极撰写教育教学论文,开展课题研究。退休之前共有100多篇论文在国家、省级杂志上发表。2019年5月返聘到温州市龙湾区委党史研究室担任组织史、党史第三卷编写工作。在龙湾区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的五年期间,认真进行地方志研究,撰写的《史志文化助力社区文化礼堂建设》在《足迹》杂志2019年第6期上发表;撰写的《强化使命担当,助力村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中国社区教育》杂志2020年第5期上发表;撰写的《疫情对龙湾民营企业的影响及后续时期的考量》荣获2020年浙江省社科联论文评选(温州)二等奖;撰写的《地方综合年鉴规范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在《浙江方志》杂志2023年第2期上发表;2024年撰写的《共同富裕进程中实现精神富裕的现实困境及提升之策》《中国式现代化龙湾实践的成效与经验启示》分别在《温州学刊》第2期、第5期上发表并获一、二等奖;《论“一区五城”建设方略成就及经验启示》荣获2024年浙江省社科联论文评选(温州)二等奖。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截稿日期:2025年3月31日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