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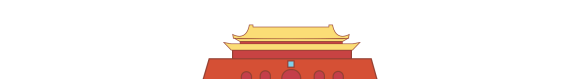

匆匆的午后春天
文/孙春红
像捧着一件珍贵易碎的古瓷花瓶,我珍惜有着海水般丰盈阳光的春日。可我又不免发愁,这么美好明媚的日子,我究竟该怎样度过才能配得上它?长了草的心,急惶惶的,与空中找不到路的鸟儿相仿。这样焦虑地盘算着,不知到底该干什么才最值得。天光却海潮般一分一分涌上来。它高过墙头。它挂在如烟如雾的柳梢。那越来越浓厚的明黄色,那些长长短短看似稀疏却无论如何也数不清的芒刺般的光线,都由窗子源源不断地照射进来,成为一大片一大片金水似的帘幕。可是在这样灿烂的金光里,你未及做什么,它就停在花上的黄蝴蝶一样,已经翩翩飞走了。
于是,我喜欢春日里一连几天的霏霏细雨。我一厢情愿却毋庸置疑的将阴雨天定为休假的日子。而且,我毫无理由地相信,时光的脚步会在雨天中放轻放缓。妩媚明丽生机盎然的春光却令我手足无措。
与上午焦躁不安茫然无措,像有什么无形双手推着的紧迫感相对应,午饭后的时间变得失落而怅惘。可是,温暖寂静而疲乏的午后,能做什么呢?只好闭上眼午睡,尽管明知那一缕疲倦根本抵不过没有心情的胡思乱想。睡意未浓,窗帘也懒得拉上,任凭光跳跃着的光线透过眼皮来胡闹。它的确像个调皮的孩子,透过眼皮的光不断变化颜色。它在眼底一会儿成为紫红的玫瑰色,让人想起在风中摇曳着的美丽的花儿。一会儿成为幽深如海的蓝色,这又让人想起天空宇宙及无边无际的星海。一会儿,它又成为黄鹂鸟颤动着的金色,这又自然让人想到一切可能飞翔的东西。毫无悬念,午睡的个把小时就这样在“似乎什么都没想,又似乎什么都想过”的辗转反侧中悄然度过。
站起身形,离开床铺,并未感到空虚。可是人却感到累,打不起精神,对万事万物都提不起兴趣的那种累。脑子在动,人却懒得做事,因而导致思维混乱。乱梦般的思维又导致睡眠不足,而苍白的睡眠又使人更懒。我兴奋且骄傲于自己无师自通的哲人般的推理。老祖宗“无事生非”的成语划过眼角眉梢。也许本就没有艺术家的潜质与情怀,我没有在春天里产生的感伤,我只是对生命与时光的匆匆深感敬畏和惧怕。
下午二时的阳光,春末的树木般茂盛葳蕤,人内心却如老式煤球炉上煎熬着的中草药,“扑扑扑”,“嘟嘟嘟”向外冒着无穷无尽而热烈苦涩的潮湿水汽。街上依然空旷,可是阳光像舞台上闪闪发亮的镁光灯一样直晃得人眼睛睁不开。街道上铺满了金色缎子似的阳光。可贵的是,这缎子上还镶嵌着无数散发着斑斓色彩的水晶、钻石以及珍珠之类的稀释珍宝(尽管这些在街道会发光的东西,也许只不过是几片碎玻璃,或被路旁小店丢弃在那里的脏贝壳,抑或是被小姑娘们丢弃不要的半支头花。可是,它们的闪光却真正的珠宝般光华四射)。成年人的世界不会轻易流泪,然而难过却无处不在。从未辉煌过的工作,庸庸碌碌的生活,容不得人感叹“时光匆匆,”——也没人会听这无谓的喟叹。可是没有脚,没有翅膀,甚至连一种模糊具象都没有的时光,却已然将人抛掷在它的身后。这像你童年天空中飞过的那只白鸟,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多少美好的东西,注定只能任其逝去,我们却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午后的阳光并未松弛,午后的人却疲软起来,这连带着神经也放松的肌肉般松懈了。与蝴蝶效应相似,这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于是,人的痛苦也由尖利变得钝圆。它成了一缕缕游丝似的忧伤情绪,虽然浸入骨髓,然而无伤大雅。不出意外,大半天的时光其实什么都没做,只是在大好阳光里,以锻炼身体的名义瞎逛着,眼看着太阳东升西落。今天的这只时光之碗,我该往里装些什么,才不致使它太空虚。可是,我双手空空,脑子里只有枯瘠的思想,我装不满它。
如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接受了自己的不好,从而奋发图强一样。突然,那些伤怀之感烟逝了大半。没有任何理由,似乎就是懒得太久了,或者赖了太长时间的床,自己觉着讨厌,也就一骨碌爬起来,将自己收拾收拾,去做好手边该做的事情一样。我腾出手理了理自己纷乱的头发。光落下来,夕阳与晚霞的颜色却更加缤纷多彩。这一缕光线,那一缕光线,都是我前两天所见到过的吧?!也许是,也许不是,没人能弄得清楚。神思在无数道光线间向前穿行,却不像漫出河岸的水般涣散,它们仍然聚在一起。时间在光线里消失,可也在光线间绚丽。
春天匆忙,在多风的北方,特别明媚妖娆的天气很是稀有,这犹如难得一见的优昙花,自会让你历经多姿多彩的忧郁之后,懂得匆匆的无尽诱惑及其真谛。
作者简介:
孙春红,山东德州人。曾在《山东文学》《唐山文学》《鲁北文学》等杂志报刊发表作品。德州市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2022年获第九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征文“佳作奖”。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截稿日期:2025年3月31日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