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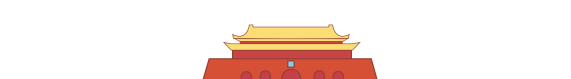

磨盘豆腐好过年
文/甄长虹
锅煮豆腐,俗称锅烧豆腐。传统古法的制作模式,流传了千年浓郁醇厚且独特的铁锅烧煮味道,在农家食谱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味美价廉的锅烧豆腐时时勾起我对家的思念与期盼。长此以往,我对这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味道久久无法忘怀,每每上街采买非它莫属。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老家长丰人每到春节家家户户都要磨一盘豆腐过年(此盘非餐桌上的餐盘,而是70公分见方的木头托盘)。起因很简单,做豆腐的原料—黄豆家家自产。重要的是,一盘豆腐可以吃很长时间。春节多处于隆冬时节,天寒地冻,豆腐容易保存,自然环境成就了美食,也成全了爱好美味的人们。将做好的豆腐置于房檐背阴处,随吃随取(那时候,整个冬季零下十几度的天气十分常见)。
磨豆腐大约从过小年前后。繁杂而又繁重的程序由此在众家庭拉开序幕:将黄豆里面掺杂的桔梗土粒及石子等杂物剔除干净,去掉发烂变质的坏豆子,用井水静泡一夜。而后,挑上两大水桶的泡好的豆子去豆腐店排队等候。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三家了。但见豆腐房里蒸汽升腾,推磨的人和在大锅前忙绿的身影,在氤氲的热气中时隐时现。没有欢声笑语,只有推磨人疲惫沉重的脚步和偶尔发出的大勺碰缸沿的豆浆搅拌声音,突显出几份寂静与压抑。
一盘豆腐从磨浆、滤渣、煮浆、下缸、点卤到上案板压制,前前后后耗时四个多小时。所有的程序操作,除了磨浆滤渣这些个体力活由磨豆腐人家出,其他的技术活均由店家操劳。店家还要搭上柴火和锅灶石磨,很多时候还要现场手把手指导,免得出现不必要的差错。至于2元钱加工费,今天想想看,实在是不高。店家付出的除了技术和辛苦,还有那份一丝不苟的责任。故此,在煮浆点卤这几个关键环节上,店家一定是亲手操持,不让他人代劳。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点卤水:一个见证神奇的时候到了,店家将调制好的卤水顺着缸内沿缓缓倒入缸内,边倒边用长把勺轻轻的顺时针搅动,好让卤水充分均匀,在卤水的作用下浆水分离。沉淀片刻,再将其舀至已经铺上纱布的木板框内,盖上木板压上重重的石块。冒着热气、泛着微黄的豆腐水瞬间顺着木框四周喷流而出,由快及慢直至充分沥干。经过约莫一个多小时的压制,一盘豆腐制作算是大功告成。
整个豆腐制作过程,推磨概是既繁重又乏味的体力活。推着比腰高比胸口略低的石磨,开始还觉着新鲜,到了半程,就有些支撑不住,后来干脆越推越重,此刻只有咬牙坚持。磨盘中央上方悬着一个底部留有小孔的铁皮桶,好往磨盘中间的孔洞内注水。在一圈又一圈推转中豆子被磨成豆浆。推完最后一圈,人已头昏眼花站立不稳,几乎晕厥。此后若干年,虽然再也没有推磨磨豆腐,但那场令人心悸的“磨砺”算是永远铭记于脑海之中了。
一种味道一丝乡愁,这种来自遥远流传经年的传统食味早已植根于心,无法替代。纵然历经艰辛与困苦也心有所向,追逐不息。如今,摊位上面表白净的豆腐,多少有些“中看不中食”,拎起来即散且食之无味。据从业人描述,这种豆腐制作只需半个时辰,磨浆不用滤渣“短平快”,像极了快餐般加工模式。至于味道营养情愫,大概不属于商家考虑范畴了。
让我欣喜深感意外的,位于下塘西北面的老家钱集悄然间立起一家豆腐房。循着那股浓浓的朴实淳厚之味我走进了这家豆腐作房,只见院子里挂满了长长的笼布。那种长时间被豆腐水浸泡已经泛黄的笼布,似乎宣示着这个沿用传统豆腐又回来了。与店主交谈过程中,我得知,这位来自豆腐发祥地—淮南的董老板几代人皆以制作豆腐为营生,堪称豆腐世家。电动磨浆机替代了人推牲口拉磨的落后操作。整洁干净的作坊里,物品整齐摆放井然有序,早已不再是旧时的模样。
近些年,每到春节前夕,家家户户再也不用自家推磨浪渣“自寻苦累”。但,买上几斤锅煮豆腐过年,是老家人至今还在延续的传统。那种透进骨子里的味道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长此以往,经久弥坚。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截稿日期:2025年3月31日
为期一年,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