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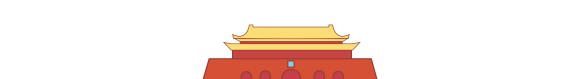

白
文/文右
爸爸的三舅,哪怕站在我面前我也不认识,只记得过年时他们聚在一个屋子里抽烟,抽得屋子里白茫茫的,光照进来像照进老鼠洞,每一束光都清晰的要命,裹满了稀碎的粉尘。一簇一簇的烟雾从他们的嘴里升起,慢悠悠地攀着往上走。罩在男人们的头顶上,变成一顶白绒绒的假发,又像盘踞的鬼魂。
三舅爷是一个白色的老男人,白、稀、软,和他吐出的烟雾一样,被阳光一照就化作了粉尘,他现在和我婶婶的妈正搭伙过日子,他已经结了两次婚了,这个炊烟一样的男人不可能再走进民政局了,那儿不让吸烟。他没了那层云雾的笼罩,就失去了自己的白,被世事重新上了颜色。在民政局的档案上,三舅爷是一个离了一次婚又死了一次老婆的男人。
亮姑是三舅爷的女儿,第二任老婆生的,她也白,是踏踏实实的皮肤白。好多好多年前她就嫁去河南了,中原的太阳没有灼黑她,我们刚在升学宴上见过面——婶婶的儿子的升学宴。她穿着白T恤,白裤子,好比一块汉白玉,正在正午时分的太阳下,带着一种令人恍惚的白。
我望着她记起,几年前她回来过一次,借住在我家,和我睡一个房间。当时妈妈铺床的时候把两个被子分得很开,中间几乎可以再装下一个发福的我爸,妈妈起身时犹犹豫豫,眼神与床铺拉丝缠绵,似有多少恨。
“你睡觉老实点儿。”她对我说。
我知道为什么——妈偷偷地问姑姑能不能我一起睡,“这孩子睡觉打把式”,她说,瞄着亮姑姑的肚子,“你别被她打着了”。
姑姑笑了,那是一种尴尬而苦涩的笑,“没有呢”,她说,“没事儿的,嫂子”。
那天晚上我想上厕所,可门锁着。过了一会儿,亮姑姑从里面出来,走进房间里去。我脱下一层裤子,想着妈妈是什么意思?姑姑怀孕了吗?怀了那个我所不认识的男人的孩子吗?
我褪下内裤,它堆在我的腿根间,像一块软肉,我不想上厕所了。
这个马桶姑姑坐过用过,我要是用了会怎样呢?怀孕可以传染吗?怎么是怀孕,怀孕了又怎么办呢?
我是蹲着上完厕所的,爬到床上,亮姑已经在灯光下睡着了,看起来很舒服。我盯着她瓷白的脸,上半身越过她关上了灯。黑暗里,我蜷成一团,拉紧了被子沿,望远挪了挪,微弱地逃离了我的噩梦。
姑姑回来是因为她妈妈生病了,一个年纪大的女人生病往往不是什么好事,不是要花钱,就是要费力,幸而那女人生的是精神病——据说她快疯了。这是姑姑带来的第二个噩梦,在她和爸爸的交谈中,我听见那个女人怎么死去。
姑姑和三舅爷带她去看病,莫名的那女人就发了疯,众目睽睽下,这一对白色的父女当即束手无措了。他们管不了她,也难以掏出钱来彻彻底底地给她治病。乍一看两位云朵一样的人让这疯女人打碎成了满地的瓷片,但他们也没放过她,不出声的躺着,扎了她一身血。
姑姑在电话里哀叹:“我当时都要给她跪下了!我想说,妈,你别闹了……”三舅爷倒似乎没在电话里出现过,真不愧是多吃了几十年饭的人,真是人淡如菊。
这三人就这样反复拉扯了几个月,随后传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同村姨妈家的猫走失了,好在姨妈她看的很开,“母猫发情了到处乱走,指不定吃错了药药死了,不用找。”,另一个是姑姑的妈妈在某天清晨带着药出门,死在了一个小山坡上 。
村子里反应平平,因为时常有男人上吊,有女人投井,死亡和接近死亡像土一样常见,被人踩在脚下沉默着。
但她的死使所有人都大大地长舒了一口气,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到底是赢了!这口荡气在肠子里转过个七八回,总算让人挤出了一丝悲凉来,大家又默哀下来了,觉得到底是逝者为上,不便再讲人家的闲话了。
只是偶尔晚上,小孩子不听话时,做父母的瞥一眼左邻右舍已拉了灯,低声喝道——再闹疯子来抓你!
疯子姓甚名谁,并没有人知。

作者简介:
文右,在校学生。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截稿日期:2025年3月31日
为期一年,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