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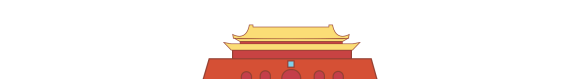

老屋
文/徐建辉
老屋是每个人心中最原始的根。
有了根,就不会失去方向,失去翅膀,失去灵魂。
我家的老屋,于我而言,不管飘向何处,身处何方,泊在何地,这个根始终在我的心灵深处,拔节生长。就像老屋后面那株盛开的木棉,花朵红艳,热情燃烧,吐出相思的火苗。
说起老屋,其实我有两个。一个是留存在记忆深处的茅草屋,另一个是现在仍然屹立在老家的原野之上,风雨飘摇了40年,但好些年没有住居过的红砖瓦屋。
这两个老屋的份量,外表听起来和看起来显得渺若尘埃,可在我心中,如同一棵参天大树。树上的每一根枝干,便是心灵的方向,每一片叶子,便是浓浓的乡愁。
记忆中的茅草屋,伴随着我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光,而红砖瓦屋,则撑起了我的青春和后段的幸福时光。
老家的茅草屋,是用木桩、横梁和稻草架设而成,墙壁用黄麻杆一字排开,再在外面敷上由剪短的稻草、牛屎和泥巴混合在一起的泥浆一样的东西。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除了生产队是红砖瓦屋,家家户户都是茅草屋。父亲说,我家的茅草屋是在我出生前两年建造的。在当时,这个茅草屋算是时髦的,因为父亲当时正从广东宝安火车站卸职回来,手头多少有些积蓄。他还说,茅草屋竣工的那天,不少的亲戚和邻里乡亲前来道贺,送上祝福的话语。可我那时还没有出生,不然脸上或许会流露出傲睨自若的神色。
自打记事起,父亲每年都会对茅草屋进行修缮。所谓修缮,就是对漏雨的部位,把腐烂的稻草翻出来,重新将全新的稻草填充进去,确保下次不再漏雨。三五年内,茅草屋上面的稻草已是陈旧不堪,需要来一次整体的翻新。这个时候父亲会请来三五个人过来帮忙,将3间房屋顶部的稻草全部掀掉,重新铺设全新的稻草。还需要对墙壁进行查漏补缺,将掉壳的部位重新填补。
每当我看到父亲爬上屋顶,一天下来腰酸背疼,看到他用手和着泥巴,里面掺杂着剪短的稻草和牛屎的过程,我感觉到了生活的卧雪眠霜,生存的筚路蓝缕。生活,往往都是扼住自己命运的咽喉,去拾掇属于自己的乐点。
茅草屋内的地面,均是泥巴地面,这也为老鼠打洞创造了条件。白天,老鼠偷吃家里的粮食和储存的食物,晚上便来到洞里休息。没有吃饱的老鼠,晚上还会活动,还会继续翻箱倒柜,跟日本鬼子跑兵一样,惹得全家人睡不好觉。老鼠打的洞,大多是柜子下面,或者不起眼的角落。每年,父亲会将柜子移开,把这些洞填起来。这些可恶的老鼠,一个洞刚填好,它们又会去别的地方,打出一个新洞来。可以说,茅草屋自诞生到消亡,就是与老鼠打洞共存亡的过程。我由此想到了“人蛇共舞”。尽管老鼠不是善类,或者说不是人类的朋友,但它作为自然界的物种,人类善待了它,或许也是善待自己。
时间的春风拂过80年代的原野,拂过洞庭湖平原,拂过我居住的南县。在这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一只巨大的手,手背是政策指引下蓬勃发展的天空,手心则是农民改天换地的豪情。衡量农村的生活水平,往往就看居住条件,看自家住的是什么房屋,看这个房屋的造价和美观程度。那个时候的农村,想建一个红砖瓦屋,大多村民会选择手工制作红砖,这样可以减少建设成本。记得我居住的生产队,第一个建起的红砖瓦屋,就是我家隔壁邻居黄三爹家,这一年正好是改革开放后的第四年。他家男丁多,全是青壮年劳动力,自己除种好责任田外,平时外出打鱼撒网,收入颇丰。
从手工一口一口制作红砖坯子,到所需要的3万多口烧制红砖,建起5间大瓦房,时间耗费了一年,这当中的辛劳只有他家人知道。可这种辛劳是值得的。如同行驶的一叶扁舟,没有动力便失去了航向;如同吟唱的一首歌谣,没有激情就失去了乐感;如同翻阅的一部传奇,没有追寻就失去了精彩。
黄三爹家手工制作红砖坯子时,我刚好10岁。有时候,他家的劳动力外出用卡子钓捕鱼了,缺少搬砖的人手,便许诺我们这些小顽童,只要搬运10口砖,就奖励1粒糖。我记得每次放学回家后,立马做完家庭作业,随后飞奔到他家,运送红砖坯子。一口一口的红砖坯子,一个来回五六十米,运往有阳光的地方晾晒。为了每天的这几粒糖,我们这些小顽童,已经很倾心尽力了。
季节更替,大雁南飞,领头的雄雁冲破云遮雾罩,煽动的翅膀引领雁阵一路向前。波谲云诡,蚂蚁搬家,工蚁所发挥出来的模范带动作用,足以让蚁群安身立命,饱食暖衣。黄三爹家红砖瓦屋的建成,犹如清风拂过山岗,明月照亮大江,加快了周边村民克服困难、改变自身、追求幸福的步伐。
榜样在前,亦步亦趋。两年后,在父母亲的操持下,拆掉茅草屋,建造红砖瓦屋,摆上了议事日程。不过,这个时候所用的红砖,已不再是手工制作的了,而是有了专门的压砖机。
记得我家压砖的那几天,队上的男女老幼,只要空闲在家的,都跑过来帮忙。大人挑泥巴,女人推板车,小伙伴们用手从板车上一口一口的卸下红砖坯子。这些过来帮忙的人,没有工钱,没有刻意邀请,那自觉的劲头,将邻里关系粘贴得天衣无缝。
这如胶似漆的邻里关系,不求索取、不图回报、互帮互助的情愫,放在现当下,是否可以震撼很多人的灵魂。世间万物情笃定。村民之间笃行了上千年的情感偈语,用到现在,足以让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感到陌生。
通过场地选择、压制砖坯、晾晒、烧制等一系列流程后,一口口棕红色的红砖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迎来了我家建造三间红砖瓦屋的日子。我家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开工的那天,村民们跟上次压砖一样,同样的不要工钱,不需要刻意邀请,轮番跑过来帮忙。几天下来,就到了上梁的时刻。
记得红砖瓦屋上梁的那天,全队的小伙伴们,还有一些老人,差不多都来了。老人们过来是目睹下红砖瓦屋的风采,小伙伴们过来是为了那几颗糖果。随着木匠师傅一声令下,一根通过精挑细选的上等的、上面画着二龙戏珠、挂着红布的梁木,缓缓向上提升。当梁木安放好后,鞭炮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随后,木匠师傅站在屋顶,一边念着吉语,一边大把大把地往下面撒糖果。下面的小伙伴们,还有围观人员,不顾一切地争抢着地上的糖果,场面不亚于正月观看龙灯花鼓,蔚为壮观。
红砖瓦屋建好后,我家迎来了搬家的喜庆日子。这乔迁之喜,亲朋戚友都会来造访的。那天,我家大门上贴着的对联“千金海上求骐骥,五色云中凤引凰”,在阳光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我全然不懂这副对联的含义,但我硬是用心阅读了好多遍,直到印在脑海中。多年以后,回味这副对联,它正好印证了我家自此以后踏平崎岖路,迈上康庄道这一过程。
记得那天前来道贺的亲朋戚友,有的提着水果,有的拿着面条,有的夹着一段布匹,有的带着白糖或红糖包裹好了的“封子”……这些就是当年人与人打交道、做朋友的礼尚往来。不收现金,不要红包,只有一点点小小的诚意,全然不像现在专门请一个人写人情簿收钱。
在乡野上空激荡了上千年的朴素的礼仪文化,以真诚和质朴为内涵,现当下已经很难捕捉到了。我推崇的敦风厉俗,我仰慕的抱素怀朴,我需要的古道热肠,我敬重的质木无文,飘向了何方?
自住进红砖瓦屋以后,我家的状况是出谷迁乔,扶摇而上。我老兄在这里参加工作,结婚生子;我姐姐在这里参加工作,随后出嫁;我也在这里参加工作,结婚生子。我年迈的父母,一直没有离开老屋,故旧不弃。
后来,我调到了县城工作,同时把父母亲接到了城里。此时从建成到我们来到县城,红砖瓦屋已经为我家足足支撑和奉献了23年。
自打父母亲搬离老屋,到县城生活,老屋到今年在没有人的陪伴下已独自孤零零地飘摇了17年。这17年当中,我经常下到老家,看望老屋在风雨中飘摇的样子,回味老屋为我家支撑起风雨的点滴,怀想当年住在老屋里,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天伦之乐。
5年前,我的父亲走完了人生83个春秋,安详地离开了我们,随后就葬在老屋前面禾场的一角。父亲生来是离不开老屋的,离世后也得与老屋依偎在一起。因为这里,就是他的根,就是他的魂。这个根和魂,托举着人生寄托,裹挟着情感皈依,承载着生命欢歌!
现如今,我经常开着车,载着已经90岁的母亲,回到从建成到今年已经整整40年的老屋,到处走走看看。看地上长眠的父亲,看天空飘忽的白云,看屋后疏河泛起的涟漪,看堂前燕子翔起的姿态……
作者简介:
徐建辉,男,1973年出生,湖南省南县人,业余作者。在《神州文学》《湖南文学》《黄河文学》《散文诗世界》《齐鲁文学》《美国海华都市报》《益阳日报》等发表作品60余篇。两次获得全国文学大赛三等奖、优秀奖和国家级、省级农机新闻奖。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截稿日期:2025年3月31日 为期一年,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