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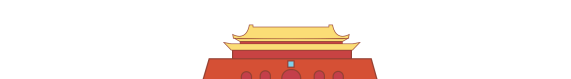

纽扣在心脏上生根
文/马建斌
窗外的雨丝斜斜地扎进玻璃,我蜷缩在宿舍铁架床上,指尖正捏着第三枚银针。缝纫盒是母亲托表姐捎来的,蓝白碎花缎面已然泛黄,盒盖内侧还黏着九十年代百货公司的价签。线轴上缠着深浅不一的棉线,靛青色的那根已经褪成雾霭灰,像极了老家清晨瓦檐下的炊烟。
针尖在第二颗纽扣的孔洞里迟疑地游走,忽然想起十四岁那个暴雨夜。母亲在昏黄的台灯下为我缝补校服,她总说扣子要缝成交叉的“十”字才结实。那时的我正为中考焦躁,将练习册摔在桌上怒吼:“别缝了!吵得我头疼!”母亲的手指顿在空中,银针在布料上投下细长的阴影,如同悬在我们之间的透明冰棱。
此刻我笨拙地捻着线头,线轴忽然骨碌碌滚到床沿。捡拾时瞥见盒底压着张泛黄的字条,蓝黑墨水的字迹洇成朵朵墨梅:“青线缝扣,白线缀花,红线补心。”这行小楷像把锈迹斑斑的钥匙,突然拧开了记忆的闸门。
那是大二寒假归家时,母亲正在厨房煨鸡汤。我倚着门框看她掀开砂锅盖,氤氲的雾气漫过她眼角的沟壑。她转身时我注意到围裙带子松脱了,要帮她系紧,她却慌乱地避开:“油烟大,别沾着衣裳。”直到夜里起夜,撞见她在阳台晾衣服,月光照着她后背蜿蜒的疤痕——那是半年前心脏搭桥手术留下的印记,她竟瞒了我整个学期。
针脚在衬衫上歪歪扭扭地爬行,像我们母子之间永远错位的对白。上个月视频时她总把镜头对准窗台的君子兰,此刻才惊觉那些刻意偏移的画面里,她灰白交杂的鬓发早已不是记忆中鸦羽般的颜色。线头突然打了死结,我凑近咬断的瞬间尝到咸涩,才发现雨水正顺着没关严的窗缝渗进来。
缝到第五颗纽扣时,指腹沁出血珠。想起去年生日寄来的包裹,拆开是件手织毛衣。当时嫌弃款式老气随手塞进衣柜,此刻却突然记起毛衣内袋有块补丁,针脚细密得如同心电图波纹。急诊室的白炽灯下,护士剪开那件毛衣抢救突发心梗的母亲时,是否看见那些藏在针脚里的年轮?
线轴终于安静地卧在掌心,二十七个春秋的重量压得掌纹生疼。母亲常说每颗纽扣都是守护心脏的盾牌,可她自己胸口那道十四厘米的刀痕,又何尝不是岁月缝给我的最痛楚的纽扣?雨幕中恍惚看见她立在老屋廊下,白发与晾衣绳上的蓝布衫一起飘摇,手里银针牵引的棉线正在时空里缓慢氧化。
最后一针收线时,手机突然震动。视频里母亲举着刚包好的韭菜饺子,背景音是新闻联播熟悉的片头曲。她鼻梁上架着我的旧眼镜,说是找老花镜时翻出来的。“扣子缝好了?”她忽然凑近屏幕,褶皱里漾着狡黠的笑。我扯了扯衣襟,三十七度二的体温正将那些歪斜的针脚熨成通往心脏的秘道。
雨不知何时停了,月光淌进窗棂,缝纫盒里的银针浮起细碎的星芒。那些未能说出口的歉疚与牵念,此刻都化作衬衫上歪扭的十字针脚。原来母爱从来不是密不透风的锦缎,而是任由我们在岁月里跌撞时,悄悄在心脏缝上的备用纽扣——每当我们莽撞地撕裂生活,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将伤口缝补成绽放的茧花。
后半夜的风掠过晾在阳台的衬衫,二十七颗纽扣在月光下轻轻摇晃,像是母亲年轻时乌发上的银簪,又像是手术室里无影灯下的钢钉。而我最隐秘的肋骨间,正生长着第三十八颗隐形纽扣,用她手术线般坚韧的丝缕,将两个错位的心跳缝进同个永恒的针脚。
作者简介:
马建斌,00后青年写作者,汉族,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读学生,研究多学科交叉融合学习方法,爱好文学,勤于阅读写作,间或获奖。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截稿日期:2025年3月31日 为期一年,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