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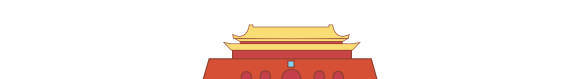

父亲
文/兰泽
父亲是一个朴实的农民,父亲有着和土地一样黝黑而深邃的眼睛,有着高粱一样紧密结实的脸庞,脸上刀刻般的皱纹如同阡陌纵横的田垄,父亲的形象总是让我想起广袤的大东北。
小时候,我体质差,经常生病,村子里无医无药,父亲便用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驮着我奔向镇上的卫生所。冬日里,北风吹起,雪雾弥漫,父亲驮着发烧的我在三尺深的雪里艰难地推行着,瘦弱的身躯在风中飘来飘。他偶尔会别过头去躲避刺骨的寒风。这时我从父亲深邃黝黑的眼眸里看到雪很大,风很烈,而父亲宽大的皮袄里裹夹着一个个小小的我。
父亲喜欢早起,而我是个天生的瞌睡虫。母亲总是惯着我,不到日上三竿不会叫我起床。父亲却全然不同,他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于是他常常早早叫我起来,我却故意赖着不起,于是第二天,我便会在睡梦中突然感觉到手上一阵阵钻心地疼痛。睁开眼,发现父亲正用一根小树条一下下用力地抽打着我的手,从此我每天都会早起,也因此养成了睡觉时把手藏到被子里的习惯。
上小学时,父亲要求我作业必须在学校写完,放学后便要参加农事活动。每日的散学铃一响,我便飞奔出校门去地里寻父亲。我将书包往地头一扔,拿起点葫芦踉踉跄跄地跟在父亲的犁铧后播种。若是假期,更不必说,日日与父亲在田间干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田垄上留下了我幼小的脚印,一行行,一串串,踏进了艰辛,踩出了坚忍。更让我品尝到劳动过后的轻松与愉悦。我吃过我自己种的玉米,喝过我自己汲的井水。饱食了麦香的镰刀也品尝过我手指上的鲜血。辛勤的汗水也浸湿过我破旧的衣衫。感谢父亲予我的十年的田垄劳作,致使我在十年寒窗的孤灯清影下总能找到前行的不竭动力。
上初中时,学校离家有三十多里的山路,骑车需行两个多小时。父亲把他那辆唯一的交通工具——永久牌自行车移交给我,却从不曾送我上学。初一初二时,还有邻村的同学结伴而行。同伴间的欢声笑语,你追我赶使得山路不再漫长。可到了初三,上学的就我一个了,父亲依然不送我。晨光熹微中,我恋恋不舍地背起行囊,骑上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奔赴那条熟悉而又漫长的山路。有时还会看到一只狐狸在我身旁奔过,惊慌失措的我无暇看清那狐狸的形容,气都不敢喘地狠命地蹬车,因为我知道在这荒山野岭间无人可以帮我。就这样老式的永久牌自行车愣是让我骑出了山地赛车的速度,时至今日我都喜欢骑自行车。不过有一种情形是骑得再快也没用的。杂草丛生的林间小路上会时不时地横亘着一条土灰色的蛇,不仔细分辨根本发现不了,直到车轮从蛇的身体上轧过,蛇便扭动着身子绞到车轮里。我便大叫一声,飞身下车,将车一扔,拼命向前跑,边跑边哭,边哭边跑,跑着跑着,哭着哭着又不得不戛然止步,掉头往回走,拿起一根树棍试着将车轮上的蛇挑走。扶起车把,飞身上车,绝尘而去。
上高中时,去了县城,我的成绩在高手如云的班级里极为逊色,巨大的落差感消磨了我所有的斗志与自信。高三那年,我愈加烦躁不安起来,成绩也陡转直下,感觉自己要撑不下去了。于是我假托生病坐车回到家中,我以为父亲会责备我。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午饭后,我跟着父亲来到打谷场,金黄的麦子一层层地平铺在场院里,饱满的麦粒迫不及待地咧着嘴笑将起来,似乎在等着石碾的驾临。父亲熟练地牵马套上石碾。石碾一圈圈飞快地转动起来,麦粒欢快地跳脱窠臼奔向自由。突然父亲使劲地抽打起马来,碾子越转越快,就这样半个小时过去了,马儿任凭父亲的皮鞭甩得山响,就是一动不动。只见父亲把马从套子里拉出来,
自己亲自拉起了石碾。我上前劝阻道:“爸,你干什么?”“还差个二十来圈麦子就打完了。”父亲淡淡地说。我正要说什么,只见父亲两手将夹板往胸前一扣,身体前倾,脖子一伸,后腿用力一蹬,沉重的石碾竟随父亲的步伐律动起来,我的心也随之一颤。我呆在那里,看父亲的脚步逐渐加快,看石碾逐渐甩掉沉重……
第二天,我比父亲起得还早,背起行囊,奔赴我人生的“打谷场”,拉一回高考的石碾。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一天,我兴奋不已,因为我是村子里唯一的大学生。我到打谷场寻到父亲,把通知书故意高高扬起,激动地喊道:“爸,我考上长春师范了!”“哦,知道了。”父亲没回头,继续用扬掀扬着他的麦子,丝毫没有停滞,眼神专注地看着随风散落的麦粒。我还以为风大父亲没听清,就又大声喊了一句“爸,我考上大学了!”父亲放下手中的扬掀,用衣袖擦擦额头上的汗珠淡淡地说:“我早就知道了。”
原来父亲早就在我心里深埋了一颗信念的种子。
毕业后,我毅然决然地来到新疆工作,大漠青春也好,碧海胡杨也罢,总之我与父亲从此万里之隔,相见恨少。母亲去世的那年,我只身一人奔丧回家。见着父亲,觉得他苍老了许多。我要父亲陪我去坟前祭拜母亲,父亲却挥手不肯。临行前我想寻母亲的一件旧衣物留作纪念带回新疆,父亲却冷冷地说:“没有,一件没留,都烧了。”我很诧异,这还是那个衣不解带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长达六年之久的有情有义的父亲吗?他何时变得如此冷漠?听哥哥说父亲只是在母亲下葬时去过一次,却再未祭拜过母亲。几年的不见已让我忘记了心中的疑惑与不满。直到去年我回家看望父亲,帮他洗衣服时,发现父亲的一件旧外套胸前的内里上缝制了一个长方形的布口袋,歪歪斜斜的针脚一看就知道出自父亲之手。我用手摸了摸那个布口袋,感觉里面有张硬硬的卡片,心里暗笑父亲怎么把身家老底随身携带呢?可抽出来一看,我愣住了。原来那里装的不是银行卡,而是母亲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母亲正凝神微笑,望着我,也望着父亲。
霎那间我的泪又来了……
原来,最深的伤痛与最真的思念都装在了父亲胸前的那个口袋里。
“喂,爸,咱们那旮瘩下雪了吗?”
“下了,老大的雪了,都封门了。”
“喂,爸,园子里的甜杆长出来了吗?”
“长出来了,等你夏天回来时就可以嚼了。”
“喂,爸,你干嘛呢?天凉了,多加件衣服啊。”
“英儿啊,爸在山里采蘑菇呢,晒干了给你邮过去啊。”
……
作者简介:
兰泽,女,原名费秀英,出生于吉林省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毕业于长春师范大学,就职于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第三中学,语文教师,素爱文学与写作,喜欢用笔记录心灵行走的轨迹。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截稿日期:2025年3月31日 为期一年,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