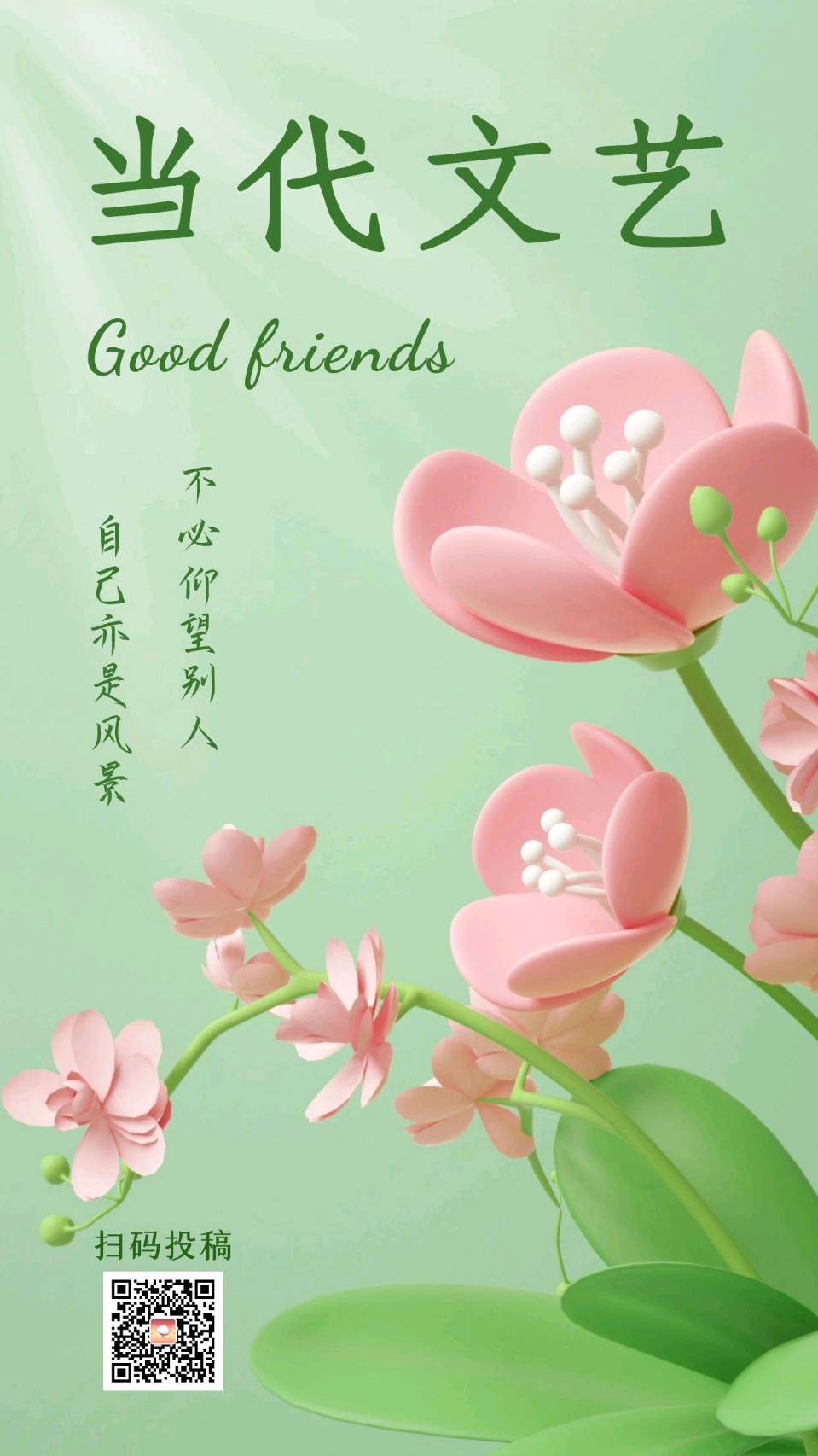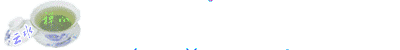虫子去哪了?
作者:王玉权
我们这代人的童年,饭都吃不饱,遑论玩具。虫子陪伴我们度过了儿童时代。
冬天冻老河,那时高邮的冬天很冷。大雪封门封路是常态。各家各户自扫门前雪,两旁的雪堆得有人把高。天晴了化雪,草屋檐下的冰凌能从檐口拖到地。河面封冻,冰结有尺把厚。大人小孩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上面蹦跳、斗鸡、掼陀螺、打砖头、砸铜板、翻跟头、划连叉。冰面滑溜溜的,谁都免不了跌跟头。好在有棉衣裤全副武装,跌不伤的。当然,和北方零下几十度的苦寒不能比。但和现在暖冬,成年见不到一片雪花比起来,那时的冷,冷得够呛,是够人们喝一壶的。
我们那地方属粘土层。久晴路上汤灰能积有寸把厚,灰喷喷的;久雨烂耷耷、粘乎乎的下不了脚。胶鞋的普及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事,那时,哪家有双钉鞋就算条件不错的了。
钉鞋,就是用厚厚的老土布叠上几层糊成骨子,做成蚌壳式的鞋面,像纳鞋底那样钉满密密麻麻的针脚。加上鞋底绱上好后,浸在桐油桶里泡上几天,或用桐油油它几十遍,务必让它喝足桐油,然后阴干晒干,就成了双黑褐色又硬又重的钉鞋了。
穿钉鞋走泥路,扒滑,但叮烂泥。得随身带根小棍子,走几步就得剔泥,否则莫想再走下去。吃力、硌脚,像戴着脚镣,活受罪。那辰光,到处是土路。雨天泥水稀尚可,最讨厌的是雨后连天阴,出门就难了。
好天好日的,穿布棉鞋的不多。那时兴毛窝子。我们水乡,蒲草不稀奇。这种草晒干后软和柔韧,夹以破布条、麻丝、鸡毛编成。衬以随处可摘的芦花,暖和。就是难看些,外观根根鸡毛管怒目苍天,像极了不讨喜的刺猬。有的姑娘还会别出心裁地在鞋口鞋头上镶以红绒线,怪里怪气的,引来一片赞美声,哈哈声。
虫子,冬眠了。寄生在人畜体上的虮虱却很活跃。那时十有八九的人都穷得没件换洗的内衣。不少人根本不穿内衣,睡觉时,扒光棉衣裤就攻进被窝里。从深秋到初夏,几个月不洗澡,可以想见身上有多脏。大姑娘小媳妇爱好,外表还是很体面的。许多邋里邋遢的男人小孩子,颈项、手脚上都有层黑鱼皮。只有到了夏天才开光。洗把澡过年,算是奢侈的享受。镇上澡塘里的热水,那叫水吗?又黑又臭的一桶杀猪汤!
“穷生虱子富生疮”。长期不洗头,少梳头,头发乱糟糟的结了饼,成了虱子窝。不洗澡不换衣,内衣、棉衣的缝隙成了虮風的大本营。白花花的虱虮一串一串的,蠕动的虱子历历可见。“虱多不痒”?未必。看看光身上的抓痕就知,左一道右一道,有的结了痂,有的还渗血呢,不过是神经麻木了而已。
晒太阳捉虱子是旧日司空见惯的冬季一景。老头子大小伙子居多。彼此彼此,大哥不用笑二哥。反而会穷开心,斗笑。伢子懒,也会被妈妈捉来,剥下棉衣,加入捉虱子大军。女人当然不好意思献丑了,望着这班大爷吃吃地笑。听得见虱子在火盆里格炸格炸地响,间以阵阵焦臭和轻烟。虱虮是虱的卵,一挤一排,格崩格崩声此起彼伏。没火盆的,则捉一个撂口中,牙一斗,格格有声,呸呸呸的吐声不断头。
这情景早已成为历史。如今的年轻人已不识此物。学生会在生物课本上见到虮虱的尊容。放大了的虮虱图像,面目狰狞,丑陋,爪子毛茸茸的,令人恶心。“汤沐具而虮虱相吊”。这些寄生虫如今已断子绝孙。好!
惊蛰春雷震四方,冬眠的虫子甦醒了。人们,特别是伢子最开心的春天来了。
渲染春意的虫子首推蜜蜂。这种土蜂,我们称作骡蜂子。它体型大,圆滾滾的,比放蜂人的小蜜蜂要大几倍。劲儿大,向阳面的土墼墙被它锥了无数小圆孔,织成一幅神机莫测的蜂国图案。 这就是骡蜂的家。若捉住放在洋火盒(即火柴盒。那时的叫法。不同于今日的纸盒,是薄片木材做的,霸壮,结实。)或小瓶里,它们会拼命挣扎,嗡嗡振动,劲儿蛮大的,跟犟骡子的烈性差不多。这土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村庄里几乎都是土草房。近的是菜园,村外是田野。桃花开了,菜花黄了,麦苗起身了。到处响着骡蜂子的嗡嗡声。采花酿蜜是它的本能。我们晓得它把蜜贮藏在草屋东西山墙望箔芦材的断面里。
茅草屋苫盖前,要铺一层芦材打的箔,用河泥搪望。屋的东西向横断面会露出一排整齐的芦材圆孔,聪明的骡蜂就把蜜贮藏在那里。
我们伢子个子小,专挑矮屋檐。搬张凳或搭个人梯就够得着了。住在矮屋里的大都是更穷的人。白天,大人都下田了。留守的都是老弱病残。他们当然不让破坏。和善的会劝我们,乖乖们,不要淘气啊。跌下来,胳膊腿断了不划算啦。凶神则二话不说,张口开骂,有人养没人管的细砲仔哉,家(土音读如嘎)去掏你娘的屁眼洞去!滚!说着扬起手中的小板凳,作出要砸的架式。我们会吓得连滚带爬,落荒而逃。
高的土墙,我们没法,只好望“墙”兴叹。在够得着的土孔里用树枝子掏,用耳朵贴着孔听它们在里面嗡嗡的,看来不止一只,好玩。从望箔上摧(Cul读第三声)下的芦材管里贮满了蜜。淡黄的粉末,甜津津的,香喷喷的,对于我们这班馋虫来说,太有诱惑力了。
菜花黄的日子里,除了满世界骡蜂的嗡嗡声,就是令人眼花缭乱上下翻飞的蝴蝶在跳舞。白色的蝴蝶居多,我们没兴趣理它们。花蝴蝶既大又好看,引得我们团团转。它忽高忽低,忽东忽西,就是难逮住,干着急。麻小五有办法,从家里翻来夏天用的大蒲扇。来事,容易得手。花蝴蝶一落地,纷纷去抢。有时两个人同时各抓住一个翅膀争执。我的!我的!小不点们说翻脸就翻脸,一用力,好端端的花蝴蝶被撕成了两半,谁也玩不成。望着手里沾满花粉和蝴蝶身子流出的粘乎乎的绿汁,并不美,甚至是癔怪。一场蝴蝶梦!
马蜂梦更惨,恶梦!小时经历了一次,终身难忘。祸起麻小五子,这家伙太野了,胆子太大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大人是说过的,告诫我们千万不要碰火锥子。火锥子是我们那里人给它取的土名,它学名马蜂,身材颀长,瘦腰长翅,深黄的底色上有道道黑纹。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畜。基本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信条。下一句就可怕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强者才有的宣言。
麻小五子玩得忘乎所以,大蒲扇触到了一只停在菜花上的马蜂。这马蜂可不像悠雅的蝴蝶和有点呆头呆脑的骡蜂。它十分矫健敏捷地逃逸了出去。一刻儿,来了十几只马蜂,轮番攻击麻小五子,疼得他妈妈娘娘地哭喊,在地上打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场的我和几个发小,无一例外地也跟着遭了殃。
麻小五子头肿得像笆斗,眼肿得像桃子,脸上麻子红肿得发亮。有的发小脸肿得鼻塌嘴歪,有的光着上身小奶头肿得像馒头。大头那时正好躺在草地上,双脚伸向空中,脚趾头中了招,肿得好几天不敢下地。我算侥幸,受伤最轻。只不过倒霉,正手上被蜇了一口,顿时感到一股火气注入身体,火辣辣地直疼得咝咝地吸气。正手肿得抓不住筷子了,只好用反手搛菜扒饭。开头极不习惯,几次把菜送到了鼻子里,弟弟把饭都笑喷出来了。从此,养成了左撇子。在家还无所谓,若坐席就尴尬了,常和人家筷子打架。人家飞来一个奇怪的眼神,能让人羞愧得无地自容。到老了,我仍是个左撇子。不过,写字还是用正手。这火锥子害人,太毒了,惹不起的虫中霸王。
夏天最惬意,剥去了外衣,一身轻松。叮叽溜(知了,蝉)是我们伢子乐此不疲的事。为什么?刺激,好玩,捡拾叽溜壳换糖吃,实惠。
甜糖对孩子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那辰光,几乎没有小胖子。伢子们颈后都有个深深的好吃塘。不像现在的小朋友,营养过剩,颈后圆溜溜的,浑身肥嘟都的。
捡叽溜壳得趁早。待大太阳出来,叽溜便上班了。太阳越大,越热,它们喊得越起劲,吵死人,中午觉都没法睡。
掏骡蜂蜜,破坏性大,大人反对。叮叽溜,大人还是没意见的。我们选用一根大芦材杆,把上端折成三角形,用线绑紧,绞蜘蛛网。街巷上上下下有许多大蜘蛛网,这种蛛网粘性大。高处的够不着,大人还帮我绞呢。绞的层次越多,粘性越大,战斗力越强。
不像现在,蛛网几乎不见了,那时,蛛网是无处不有的。家里旮旮旯旯的小蛛网粘性不大,蛛的体型也小,灰白色。外面空间的网,蛛丝在阳光下发亮,黑色的大蜘蛛比拇指甲盖还大。它们织的网似八卦阵图。经线纬线间矩精确,几何图形一丝不苟,真不了起。破了的会很快重新织好。它们的肚里像蚕似的有吐不完的长丝。人们走路时,常被低处的蛛网网住,有点讨厌。
织网捕虫是蜘蛛的生存智慧。它们像极了扳罾的守株待兎坐享其成。一旦有大点的猎物入网,大黑蛛迅速出击,爬到挣扎不已的猎物前,伸出口中的毒针一蜇,猎物如中了麻醉枪不动了。蛛牙很锐利,如注射针,猎物化成了液汁,很快便被吸光了。若不食,便用丝缠绕挂在网上作储备粮,以后慢慢享用。
黑蛛其貌不扬,知了外形也丑陋。一个会织网,一个会喊叫,各有所长。喊叫虽为噪声,但长久了,高低抑扬的音阶,便形成了韵律。没知了为夏弹歌,炎夏会失色的。没蛛网的八卦,怕也是生态失衡的一种标志吧。
叮叽溜的工具是人手臂的延长。要悄没声息地接迈猎物,一粘一个。不怕它挣扎,越挣扎越会被深度粘紧。除了绞大蛛网,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偷把面粉洗面筋,有一小团就够了。面筋比蛛网更粘。把面筋粘在小竹竿头上,对准未发现我们动静的叽溜,叽溜便无悬念地成了我们的俘虏。
小时太淘气任性,对待所有的虫子俘虏,没一丁点优待俘虏的意识。相反,虐待,且是恶虐。先把叽溜翅膀剪了,叫它飞不成,可怜它只能一蹦一蹦的或慢慢爬了。不叫?用手括它的腹部,它乖乖地喊;不中意,明显不如在树上叫得雄壮,就换用小竹片括,用小棍子戳,直到把它折磨死。简直是一群毫无人性的小法西斯。
你道完了?没。把死叽溜朝鸡群里一丢,也许它没全死,大公鸡一啄,它的爪子还会动。大公鸡后退一步,又上来一啄。还在动,鸡又后退下,又上来啄。如此几个回合后,大公鸡会啄啄啄个不休,直到开膛破肚,露出雪白的肉。吃肉了,多快活,大公鸡啯啯啯地开心地唱起了歌。
更惨忍的是麻小五子把刚捉来的叽溜朝锅膛里一丢,用火灰一埋。听到吱的一声便没声息了。肉的焦煳气味出来了,取出,已成一黑炭团。剥去焦皮,掏去内脏,麻小五抓着如蛋白似的肉,蘸点盐,嘴里故意发出咂咕咂咕的声响,头一点一点的,得意地气我们。还送到我们嘴边说,尝尝,好吃呢。我们一个个的推开,眯着眼,伸出舌,头摇得泼浪鼓似的,显出癔怪瘆人的表情。我们可不敢吃,这家伙真侉。
据说,昆虫真的可吃,是座高蛋白富营养的宝库。油炸蚕蛹,油炸蝗虫、蚱蜢,大酒店里的一道名菜呢。
玩拿猴子(学名天牛)是我们另一兴奋点。拿猴子是我们给取的土名。它全身披着油黑的盔甲,三角形铁头上长有两根威武的长触须。黑白点相间,酷似戏台上孙猴子头上的两根长雉鸡尾,故有此名。
这拿猴子太好玩了。三角形铁头上一副大嘴,嘴里有锐利如钳的黑牙,一夹一夹的不住地动。用小虫子喂,它不费事地就吞下去了,好有趣。我们先废了它的武功,剪翅膀,叫它逃不成。抓住它的两根长触须,上下左右任意弯曲或者逮住三百六十度转圈。若失手,它会依惯性从空中落在地面打几个滚。不动了,阵亡。死了拉倒呗,喂鸡。鸡不食,撂茅坑沤粪。小时懵懂,无恻隐之心,漠视生命,这就叫儿戏。大人若这样就是种该被谴责被惩罚的行为,谁叫你把郑重其事的事当儿戏呢。
最豪放的是逮蜻蜓,放飞蜻蜓最有趣。一般的草蜻蜓呆,叮在花草上不动。只要屏住呼吸,蹑手蹑脚接近它,手一伸,就能捏住它的长尾。剪去一半翅膀,放蚊帐里,会替我们捉蚊子。不剪翅膀,用线扣在它长尾上放飞。我们便牵着线跟随它飞。往往一队七八个人齐步走,颇有阵势。比谁的蜻蜓俘虏飞得远,溜得上气不接下气,汗沙沙的也不减兴致。
全身泛绿的大蜻蜓,身子比草蜻蜓要大好几倍,像个俏丽高挑的美人儿,我们最想拥有它。但很不容易捉到。
麻小五子故伎重演,把扑蝴蝶时从家里偷来的大蒲扇装在长竹竿上,时有捕获。绿蜻蜓劲大,要用勾被线扣。它的嘴可厉害了,会咬人,咬出血来,可见它捕食的凶狠。牵着绿蜻蜓飞,能把人心脏病溜出来,太快了,数玩它顶刺激!
玩蜻蜓,伢子们一头劲。飞翔,寄寓着孩子的童真幻想,常常做自己会飞的春之梦。……,哈,你抓不住我。啪地一声,我腾空而起。嘻嘻,飞来飞去,在他们头顶上绕,他们还傻乎乎东张西望找我哩。笑醒了,转头又呼呼了。飞啊,飞啊,不知飞到哪了,认不得家了。呜呜呜……又哭醒了。妈妈叨叨,这细东西玩疯嬉了。听到了妈妈的话,才晓得自己既“喵”飞又“喵”迷路,还在妈妈身边躺着。一踏实,又迷糊过去,继续做春之大梦了。
唉,大人不可能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其实,他们小时也打这么过的。只是岁月的磨砺,生活的重负,压弯了他们的腰,销蚀了他们的脑。小时的梦早已忘得狗掠干净。幼儿园的阿姨,多少还能理解一点,所以能成为小朋友的大朋友。
秋天的打谷场上,傍晚时分是蜻蜓约会时间吧,比草蜻蜓身子小多了的红蜻蜓,比丝线还小的幼蜻蜓,被人称作黑寡妇的乌蜻蜓,一阵一阵,一阵一阵的。千军万马,在夕阳光波下,呈现出磅礴气势,蔚为壮观。
现在,少见甚至难以见到蜻蜓的身影了。蜻蜓停在小荷尖尖角上的诗意去哪找寻啊?
经春历夏,像骡蜂子、粉蝶、拿猴子等,过了季节便少见它们的身影了。带给我们童年乐趣最长久的是磕头虫或叫作翻跟头虫。没百度,不知这甲壳虫是何学名。
从春夏到深秋,翻开破砖烂瓦的土堆,都可以找到它们。
每到阴雨天,外面疯不成,三五发小便心照不宣地玩磕头虫去了。家里人趁雨天要做好多事,嫌恶我们在家碍三绊四的。我们也巴不得躲开他们,便相约去土地庙的香堂里玩。那里安静空旷。寂寞的菩萨,你们心慌难耐了吧?我们便在菩萨眼皮底下开起了热热闹闹的赌场。
土堆是虫子的大本营,蠕虫甲虫都有。我们对蠕虫没兴趣,蚯蚓之类便成了跟在我们身边鸡们的外块。可以开荤加餐了,特别是大公鸡,开心地咯咯地笑着。甲壳虫也有好多种。我们认得磕头虫,它全身黑,前爪短后爪长,长长的楕圆身子,虽体量不大但很结骨。翅膀很短藏在甲下,偶尔飞下,也不成气候,如同鸡样,翅膀的作用巳退化。
捉对厮杀,捺住后腿,它会直立起来,前爪屈曲,身子直直地一百八十度以头撞地,香堂砖地上会传出“笃”的一声。哈哈,给力!有专人计数决定胜负。谁的虫子不给力,输了,胜者会刮负者输的数量的十倍的鼻子,以此取乐。有的家伙故意加大力度刮,被刮者则咧开嘴咬着牙眯起眼忍着。心下默念,狗日的,等着,等老子赢了你,加倍报复。
这甲虫很傻,不会偷奸取巧,它会反反复复地磕头不止,次次都笃笃有声,直到以头碰地再也直立不起来为止。触触,不动了。咳,完了。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换一种玩法。把它甲壳朝下,肚皮朝天。它的四条长短不一的爪子会不住划动,划动,似乎在积蓄力量翻身。正常是肚皮朝下,想翻转身子,甲虫的本能。划、划、划,长爪一用力,只听“啪”地一声蹦起老高,从空中一百八十度调转身来落到砖地上。我们会拍手欢呼,为它加油。
随着虫子气力的不断消耗,速度渐慢,高度渐低,直到翻不动阵亡为止。
磕头相对容易,翻跟头不易。人世上许多事同理。“男儿膝下有黄金”,钢铁硬汉是宁死不屈的。为了拍马溜须追随权贵讨点残羹剩饭,不惜下跪卖身求荣的多多众矣。
知了扯着嗓子对炎夏叫板,青蛙撑着肚子为丰秋鼓噪。都是轰轰热热铜琶铁板式的昂扬声调。而蟋蟀金铃子纺织娘等秋虫的声调却是悠扬的浅唱低吟。
古人谓秋之为声多悲凉,旧文人遣春恨秋悲,营造的是萧瑟伤感的氛围。我们伢子没有这些消极的东西。叫驴子的声音多好听啊,哪像叽溜、青蛙的大嗓门成天制造噪声。
奇怪的是,我们那儿把秋虫一古脑儿称为叫驴子,多可笑。乡下人对秋虫的污名化也令人莫名其妙。蠢驴的叫声多难听,抽疯似的,吓人一跳。秋虫的声音,文质彬彬,一听心就安静下来了。我们循声找去,谁叫你们自我暴露行踪呢,十有八九逃不出我们的围猎。
蟋蟀,姑且还用我们那里习惯了的叫法一一叫驴子。这虫子好斗,这一点倒像犟驴。还是一对一,比谁的虫子狠。把它们放在同一瓦盆里,它们仿佛像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吱地一声,触须直竖,缠成一团嘴咬撕打不可开交。真残酷,缺胳膊断腿是常事。胜方的虫子会吱吱地得意鸣叫,金鸡独立,如同得胜还朝的大将军。小虫子也会骄傲呢。
看叫驴子相斗,吸引力太大了。虫子狠命地斗,我们拼命地鼓掌,握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喊叫。小人们和虫子都活在昏天黑地里,忘了一切。到了饭点,总要大人三番五次地催,我们口里答应身子却不动。恼怒的大人往往火冒三丈,一把揪住我们的耳朵拖走。气性下的力道多大啊,疼得我们杀猪似地大喊。刚刚还笑不够的,这会子麻油榨得淌淌的,可怜呢。
不怪大人发毒(方言,着急光火生气的意思),他们要急着下田,伢子们也有寻旱草放老牛的任务,不可能让你一味玩玩玩。啊,自由,自由,世上哪有绝对的自由。
许多虫子都是我们小时的玩伴,带给我们无穷的欢乐。也有不少虫子带给人们痛苦和灾祸,比如虮虱蚊蝇臭虫等。
我小时得过疟疾,尝过滋味。我们那里叫打摆子,蚊虫引起的夏季流行性传染病。很凶险。高烧近四十度,大汗淋漓,人会失水虚脱休克。恶寒时,三床大被捂在身上,也止不住上牙打下牙激烈颤抖。恶寒发热周期性地过山车式的轮番折磨,不及时治疗,大有生命之虞。
一晃,老了。当年陪伴我们度过童年的虫子,无论益虫还是害虫,有的不见了,有的少见了。虫子去哪了呢?
【作者简介】
王玉权,笔名肃月。江苏高邮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退而不休,码字怡情。不钓名和利,只钓明月和清风。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