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情思
严 民
四月的微风,尽染了春天的绿。
我从近邻孔家小院路过,香椿的枝芽隔墙探出,似乎在呼唤主人快来采摘;从紧闭的铁栅栏门里望去,雨后湿土里吐出的嫩绿薄荷和荠菜花儿交相互映;蓦然间,我的脑海里涌出了“竖一个绿耳,听风听雨,蜻蜓立于圆,蜂醉于蕊,天地一色,济南开了”——是的,这正是著名山水诗人孔孚家人曾经的居住地,尽管他们刚刚搬离,这里的一草一木却又唤起我无尽的情思……
我与孔孚老师的近距离接触也是在一个春天。
其实,在此之前我早就与他相识。孔老师青少年时代就读于济南正谊中学,我的父亲严薇青先生曾于抗战时期在此任教,于是他们二位便结下了师生之谊。然而,在此之前我和孔老师只是相知而不熟悉,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春天里,我在山师门前与他不期而遇。

几乎没有寒暄,他劈头便问:“听说你最近新出了一本书,怎么没送我?”我一下愣住了。
不久前我的长篇小说《月圆月缺》刚出版,单位里有一种习俗:不管谁出了书,都要按花名册赠送,免得有厚此薄彼之嫌。然而有些人并不读书,更有甚者,一位所谓的文人,这手接书,那手就当废品卖掉。经他之手,流入地摊的书有几十本,且每本扉页上都有作者题词。这种让人寒心的事看久了,我这次出书索性来个物极必反,除了家人亲戚,干脆谁也不送。
此时,我正考虑如何作答,孔老师又直言不讳:“我听说你觉得送了书没人看,便不送了。你怎么知道我不看呢?”我被他问得面红耳赤,只好分辩:“我寻思你是大诗人,又很忙,哪有空看我写的这些破东西。”
“写诗的就不看小说了?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还很关心你的创作呢!”他接着便问起我的创作近况,并再次叮嘱我一定给他送书。
以前我就十分敬佩孔孚老师的人品、文品,这次路遇,使我更加了解了他为人的坦直、真诚。那本小书当然给他送去了,不久他又找我谈对书的意见,从此便与他有了较多的来往。
1997年春节,我去给孔师拜年,临别时他送我一幅书法作品“无”字,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不料那年四月他便离世而去。
多年后,我有幸参加了孔孚诗歌研讨会。那几次研讨会的发起者、组织者、与会者都是孔师的文友、学生及慕名而来的诗歌爱好者。会场分别是从山东大学、济南大学借来的会议室,规格低调,且没有官方人士参加,但格调高雅,是纯学术性研讨。与会者来自四面八方,有学者、记者、教师、工人、公安……上至80岁高龄的老者,下至20出头的大学生,他们都怀着对诗作的虔诚之心,畅所欲言,言之由衷。我常常在想,在当下这种物欲横流的浮躁年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在孔师过世多年后,以毫无功利之心,来参加他的研讨会呢?他的诗歌为什么至今还能广为流传,甚至获得比他在世时更公正、更高度的评价?
直到有一天,我又翻开《孔孚诗选》,一首《母与子》闯入眼帘:
见到海
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怕是海的儿子
泪水也是咸咸的呀
霎那间,我的困惑迎刃而解:人们欣赏孔孚的诗,是因为他的诗真,情真,意真!尽管他曾被一个个惊涛骇浪所淹没沉浮,却从不随波逐流,甚至敢于逆流而上,既便被巨浪冲击得头破血流,依然“还是抱紧大海”,因为他“是海的儿子”!
我曾一度觉得孔老师的诗写得玄隐,难以读懂,后来才知道,是我缺乏诗人的“灵性”。2013年春天,我去敦煌莫高窟,在月牙泉畔的沙丘上观赏落日:那红色的火轮沉落在大漠尽头,染涂在天际线上,在人们的惊叹声中,由血色渐渐变成浅蓝色的线条,一切都无声无息,归于沉静……那一刻,我脑海中突然跳出了两个字——“圆 寂”,这正是孔师的诗句,我第一次悟到了孔孚诗的意境……
春风拂面,牵回了我的思绪,我对这满目青绿的小院依旧依恋。因为这儿符合孔孚老师择居的意愿:“窗前有个小院子,小院里种一棵小树,我坐在写字台前,哪怕能看到一瓣绿叶,便会觉得心旷神怡,所谓会心处不必在远也!”
是的,尽管他别离家人和我们已经28年,却始终没有走远,在这春风里,在这绿叶里,他的吟诗声、他的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会心处不必在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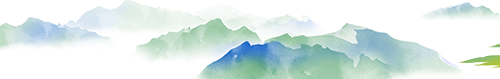




玫瑰手绘折扇、玫瑰国画
订购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