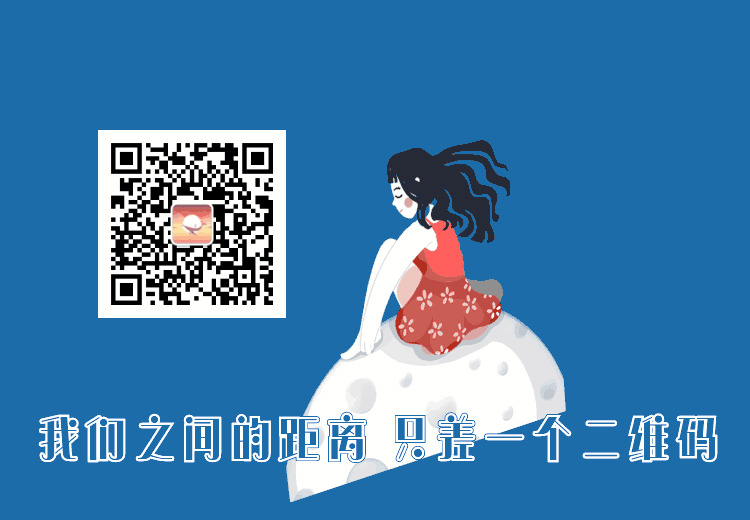谷 雨 三 叠
作者:墨染青衣
谷雨这日的雨来得突然。孟溪搁下毛笔时,第一滴雨水正巧砸在砚台里,墨汁溅起微小的浪花。他望着宣纸上未完成的诗行——"谷雨初晴后,孤云独去闲",后半句却怎么也接不上。这已经是第三张废稿,纸角蜷曲着,像某种软体动物死去的躯壳。
窗外的雨渐渐织成密网。孟溪租住的这间老屋位于江南某个地图上需要放大三次才能显示的小镇,青瓦屋檐下挂着去年留下的艾草,枯黄的叶脉里还囚禁着去夏的阳光。雨水顺着瓦当滴落,在石阶上凿出深浅不一的凹坑,他数着这些岁月的印记,突然想起父亲说过,谷雨的雨滴能砸开沉睡的种子。
书桌上的手机亮起,是编辑发来的第七封催稿邮件。孟溪把手机反扣在《现代汉语词典》上,词典边缘贴着五颜六色的便签纸,每一张都写着半途而废的开头。作为四十岁后才崭露头角的中年作家,他的散文集《雨水与铁》意外走红后,出版社要求他在谷雨节气前交出新作。截稿日期像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而他的灵感却如同这江南的春雨,看似丰沛,落地便消失无踪。
雨幕中忽然飘过一抹青色。孟溪眯起近视的眼睛,看见巷口伞铺的老板娘正在收晾晒的伞骨。那是个约莫三十五岁的女子,总穿着靛蓝染的棉麻衣裙,镇上人都唤她沈师傅。此刻她踮着脚去够竹竿最高处的那排伞架,衣摆被风掀起一角,露出脚踝上若隐若现的纹身——似乎是某种古老的雨水图腾。
孟溪抓起门后的黑伞冲进雨里。他的伞在昨日狂风中断了两根伞骨,此刻撑开便歪向一侧,像只折翼的乌鸦。雨水趁机钻进他的后颈,顺着脊椎流下去,冰凉如一条苏醒的蛇。
"伞要这样收。"沈青禾接过他手中残破的伞,手指在竹骨间灵巧地穿梭。她的工作室弥漫着桐油和生漆的气息,墙上挂满各式油纸伞,从最简单的十二骨青绢伞到繁复的二十四骨重彩伞,在雨天的光线里泛着幽微的光。工作台上有本摊开的册子,孟溪瞥见密密麻麻的数字与符号,像是某种气象记录。
"您在记雨?"孟溪指着那本册子问。
沈青禾没有立即回答。她取出一根细如发丝的竹篾,在酒精灯上微微烤软,开始修补断裂的伞骨。"从二十四岁开始,每年谷雨都要记下雨水的重量、时长和落速。"她忽然抬头,眼睛像被雨水洗过的黑曜石,"父亲说,做伞的人要懂得雨的脾气。"
孟溪注意到她手腕内侧有道淡白色的疤痕,形状像道闪电。屋外雨声渐密,有雨珠从瓦缝漏下来,落在锡制的接水盘中,叮咚作响。沈青禾转身从木箱里取出把泛黄的老伞:"你看这把民国二十四年的伞,当时匠人用桑皮纸浸了七遍桐油,到现在还能挡雨。"
修补好的黑伞在她手中旋转,伞面上暗藏的银线突然显现,竟是幅精细的星宿图。孟溪看得入神,没注意自己的笔记本从口袋滑落,直到沈青禾弯腰拾起。本子上是他涂改无数遍的开头:"谷雨是春天的遗书,写满未完成的承诺..."
"你是作家?"沈青禾把笔记本还给他,指尖沾了点墨渍,"我父亲生前常说,谷雨时节的雨有墨香。"
雨突然下大了。密集的雨点砸在瓦片上,像千万颗玉珠倾泻而下。沈青禾的工作室有个小小的天井,雨水顺着青苔覆盖的竹管流入陶瓮,发出深浅不同的回响。她拿出两个粗陶杯,从瓮里舀出雨水煮茶。
"去年谷雨的水,"她将茶杯推给孟溪,"存满一年才能喝出甜味。"
孟溪捧着茶杯,突然想起童年时外婆用雨水腌制的咸鸭蛋。蛋黄会凝成夕阳般的橙红色,蛋白上浮着松花状的纹路。那些在屋檐下接雨的午后,雨丝把世界隔成模糊的水彩画,而外婆总说谷雨的雨水能让腌制品生出"魂"来。
"您知道为什么谷雨的雨特别吗?"沈青禾突然问。她取下一把未完工的伞骨,在灯光下像展开的鸟翼,"因为这时的雨要穿过整个春天的花雾,带着桃李的精魂。做伞的竹子得在谷雨前砍伐,这时候的竹浆最饱满。"
屋外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几个小学生穿着彩色雨衣跑过巷子,脚下溅起银亮的水花。孟溪看见沈青禾望着孩子们的眼神突然柔软下来,她转身从柜子里取出捆扎好的小伞,伞面上画着憨态可掬的生肖图案。
"镇小学的订单,"她抚过伞面上未干的颜料,"现在孩子们都喜欢印着卡通人物的塑料伞了。"
雨声中混入了遥远的雷声。孟溪发现沈青禾的"雨谱"上,每年谷雨那页都画着不同的符号:有的是蜻蜓,有的是麦穗,去年那页却画了盏将熄的油灯。他正想询问,突然瞥见里屋供着个小小的牌位,前面摆着碗清水,水中沉着三粒青麦。
"父亲走在上个谷雨,"沈青禾顺着他的目光说道,"临终前非要我们把他抬到院子里,说要看最后一场谷雨。"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腕上的疤痕,"他接住一滴雨才闭的眼,那滴雨在他掌心停了很久才散。"
孟溪想起自己父亲去世时也是雨天。肝癌晚期的老人坚持要听雨声,他便推着轮椅带父亲去医院后花园。那时父亲干枯的手突然有力气抓住他的手腕,说听见了雨里混着老家插秧的歌谣。现在回忆起来,那日的雨确实不同寻常,落在水泥地上会弹跳起来,像无数细小的珍珠。
沈青禾开始往伞面上刷第二遍桐油。金黄的液体在素绢上蔓延,渐渐显露出底稿上隐形的莲花纹样。孟溪注意到她刷桐油的动作带着某种韵律,手腕每次转折的弧度都精确一致,仿佛在遵循某种古老的舞蹈。
"您知道油纸伞为什么都是二十四骨吗?"她突然问,没等回答便自答,"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根伞骨。老祖宗做的伞,撑开来就是幅活历法。"她的指尖划过伞骨间的夹角,"这里对应惊蛰,这里是芒种,最顶上这根..."
"是谷雨。"孟溪脱口而出。他看见伞顶的铜制伞帽上确实刻着"谷雨"二字,周围环绕着细密的水波纹。
雨势渐小,天光从云隙漏下来,工作室里浮动起淡金色的尘埃。沈青禾把修好的伞递给孟溪时,他闻到自己伞上散发出的新桐油味,混着淡淡的松香。这气味让他想起大学时在古籍修复室打工的日子,那些被蠹虫蛀蚀的线装书,在修复师手中重获新生时,也会散发类似的气息。
"谢谢。"孟溪掏出钱包,"多少钱?"
沈青禾摇摇头:"给我写句话吧,就写在你刚才掉的那页纸上。"她指着孟溪的笔记本,"关于谷雨的。"
孟溪翻开被雨水洇湿的纸页,钢笔悬停良久,终于写下:"雨是倒流的星河,而我们是沉在河底的星星。"沈青禾接过纸页,将它压在工作台的玻璃板下,那里已经积攒了厚厚一叠各色纸片。
离开时孟溪回头望去,沈青禾正站在天井下仰头看雨。光线透过雨水在她脸上投下流动的阴影,那一瞬间她仿佛也成了某种雨水凝聚的造物,随时会随着云散而消失。她的身影让孟溪想起自己散文中写过的一句话:有些人在雨里出生,在雨里活着,最后化作雨的一部分。
回到老屋,孟溪发现书桌上未完成的诗稿被风吹到了地上。他拾起来,发现雨水从窗缝渗进来,在"孤云独去闲"后面洇开一片水痕,恰似半阙隐去的词。他忽然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了。
【作者简介】
张龙才,笔名淡墨留痕、墨染青衣,安徽芜湖人,爱好文学,书法,喜欢过简单的生活,因为 简简单单才是真,平平淡淡才是福。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追求了过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懂得知足的人,即使粗茶淡饭,也能够尝出人生的美味!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