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微山湖二级坝的坝顶远眺,湖水在阳光下碎成万点金鳞。312孔闸门像巨龙的肋骨般向天际延伸,7300米长的坝体蜿蜒入云,恍惚间竟分不清是长堤切开了湖水,还是湖水托起了这条横跨鲁苏的钢铁脊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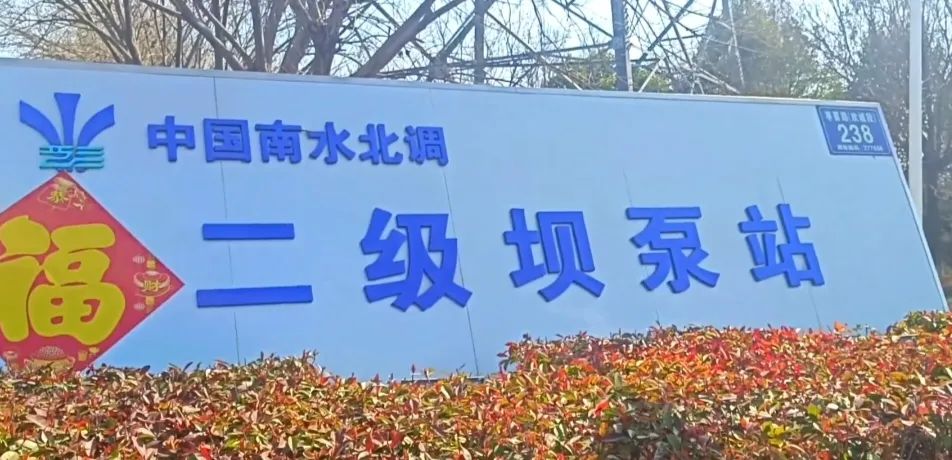
1958年的冬天,微山湖畔的冻土被数万民工的号子声震醒。18岁的济宁小伙赵金柱跟着父亲推独轮车运土,车把上挂的窝窝头冻得像石头。当年参与建设的老人回忆:“哪有什么机械?全凭人拉肩扛,大坝是一寸寸从湖底长出来的。”

如今的坝体剖面展馆里,陈列着半截锈迹斑斑的钢钎。讲解员总会指着展柜说:“这是当年女工突击队的工具,她们在零下15℃的冰水里清淤,钢钎敲冰的声音能传出三里地。”那些被历史封存的瞬间,在发黄的工程图上依然鲜活——3.2万民工用2000个日夜,在芦苇荡里筑起了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湖腰蓄水工程。

清晨6点,老闸工推开第48孔闸门的控制室。布满划痕的操作台上,红色按钮旁的铭牌还刻着“1977年检修”字样。“这闸门见过大世面。”他摩挲着铜质手柄,“98年洪水闸门连续开启72小时,水流把闸底的水泥墩冲出半米深的坑。”

如今的二级坝早已不是孤军奋战。智能水文监测系统实时跳动着数据,无人机在芦苇丛中巡查渗漏点,但那些嵌在混凝土里的岁月痕迹仍在诉说往事:闸墙上深浅不一的刻度记录着历年最高水位,维修梯上绑着的红布条是二十年前防汛突击队留下的标记。

盛夏的二级坝是最“泼辣”的。荷叶挤挤挨挨漫到闸门下,粉白的花苞“啪”地绽开,惊起一滩鸥鹭。摆渡的老周常笑称:“荷花能听懂闸门声,开闸时它们都往江苏偏,闭闸时又朝山东歪。”

最动人的却是冬日黄昏。芦花乘着暮色飞过泄洪闸,落在守坝人老吴的茶缸里。他裹着军大衣坐在观测站门口,看落日把312孔闸门染成紫金色:“这坝是活的——开春时带着土腥味,入秋后全是鱼虾的鲜气。”

湿地公园广场上的青铜雕塑总让游客驻足:老渔民肩扛鱼篓,两只鱼鹰昂首挺胸。当地人老陈蹲在雕塑旁卖菱角,冷不丁会插句话:“现在湖东头老孙家还养着六只鱼鹰,逮着鲤鱼时翅膀扑得比人高。”

去年通车的枣菏高速从坝区掠过,服务区观景台上总能看见举着相机的游客。但那些真正懂湖的人,偏要沿着坝体西侧的老渡口走一遭。踩着被独轮车碾出凹痕的青石路,抚摸长满藤壶的旧系缆桩,忽然就听见了1958年的风雪声。

当无人机航拍镜头掠过今日的二级坝,60多年的光阴在屏幕上流淌成河。闸门下穿行的货轮拉响汽笛,惊飞的水鸟掠过智能水文站的天线,穿汉服的姑娘举着自拍杆从治水纪念碑前跑过——这条横卧在微山湖上的“钢铁巨龙”,终究成了连接历史与未来最生动的锚点。
(清风)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