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刘棉朵 《呼吸》 (长江文艺出版社)
山顶上的春天总是比别处短一些
刘棉朵
海鸥齐飞
海水退潮,河滩裸露出来
下午开车经过大桥时
看到一群海鸥从河滩上飞起来
起先是一两只
然后哗啦是灰白色的一群
一霎那,我感到大自然中如果有神
一定就住在那片飞起的羽光里
温暖,赤裸,永久——
它们似乎一直等在那里
在那片肮脏的淤泥里
忍耐着
等着起飞时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平庸,晦暗,苦难
都被一束天光的照亮,褪除
伐木者
我没见过伐木者
在一个大院里
我只看见许多木头
堆在一起
巨大的松木
和外省的气候和山岭
我经常爬到那堆木头上去
选择一棵坐下来
像坐在一棵树下一样
有时
也有一只鸟会落在上面
和我互换面孔
但没有树叶
也没有松鼠
伐木者也从没有出现
那个木材场里的
那些沉睡的木头
似乎早已被伐木人遗忘
直到有一天,大院
突然空旷起来
空地上只剩下一些干枯的树皮
直到那些树皮也没了
地上只剩下了一些
树木躺着时留下的迹痕
直到大地上能让人
想起伐木者的
所有物体和迹象都没了
也没有谁看见,汗流浃背的伐木者
带着他的样貌、热气和电锯
在春天,在深深的森林中
疯狂地伐木
修剪
整个下午
那个园丁都在
修剪冬青、扁柏
还有黄杨
我发现,总有
一些枝条
高出其他的同类
就像有些人
总是特立独行,不同
于众
其实修剪
主要就是剪去
高出的这一部分
让整个灌木丛看起来
就像士兵那样
排列整齐
虽然窜出队伍是
危险的
但是不出一周
你就会看见这些
刚刚修剪过的
灌木丛
又有一些不安分的枝条
山顶上的春天总是比别处短一些
山脚下的花已经开了
山顶上的种子还没发芽
那是因为山顶上的春天总是比别处短一些
甚至没有春天
因为春天总是从山顶走到山脚的
春天也有一把降落伞
它从高处降落到地面上
然后变成那些无数的小伞
而更高的山上,从来都没有春天
只有白雪皑皑,白雪覆盖
只有一个人在山脚下长久地对着它凝望时
它才会有一小会儿的春天
它的冰才会融化一些
变成人用自己的眼睛看不见的水蒸汽
而如果那个人不去望它了,掉转过头去
山上的春天就结束了
桔子在曲阜火车站的一种吃法
我不知道桔子在其他地方
是怎么被吃掉的
但是在曲阜火车站
我却看到了桔子
是被这样吃掉的
那是坐在对面的两个老人
一对已经结婚多年的夫妻
他们坐在一起,然后
丈夫拿出了一袋桔子
妻子低下头仔细挑选了一个
先用鼻子闻了闻
然后掰开,撕去了那些白色的筋络
先是给丈夫的嘴里喂一瓣
又送到自己嘴里一瓣
那个丈夫一边吃桔子
一边看报纸
几乎没有人看见
他是在吃桔子
后来,报纸换到了满头白发的
妻子的手里
丈夫就低着满头白发
给妻子剥桔子
他也是先用鼻子闻闻
然后才掰开
第一瓣
给了妻子
看见妻子慢慢咀嚼了
才把第二瓣送到了自己的嘴里
水挤在深夜的水管里等待
水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里
怕冷一样
它们挤在深夜的水管里
谦恭地等待天亮时有个早起的人
会拧开水龙头
它们像一群鸽子一样在等着
有人能打开笼子的门
它们憋着嗓子里的声音
不出声,在水管里暗自地歌唱
它们歌唱它们是带着鸟粪、树叶
泥沙和泡沫的水
曾经住在一座水库里,一起穿过一座水厂、水泵
和长长的旅途
现在已经可以喷出
它们从黑暗的地方来到明亮的前夕
一滴好奇的水已经打算跑到镜子上去
它要看看自己的颜色和面容
也要有一种镜子里的生活
它们挤在深夜的水管里唱着歌并等待
等着我明天一早拧开生活的水管
黄昏时我经过一座小镇
黄昏时我经过一座小镇
看见了一片果园
它在一片靠近麦田的地方
似乎曾经是被谁砍过的园子小小的一角
这一种剩余不知为什么
被保留了下来
果园里果树稀疏
隔着一条小路和青青的麦田
看不清里面有什么果树
它们好像有的已经开过花了
有的还没来得及开
落日用剩余的光
照耀着田野上这剩余的一角
我仰望那些模糊的树冠
猜测那些来过这里的人
那些曾经经过这片果园里的人
它曾经是如此的温暖、宁静
散发出浆果成熟后弥漫的酒的香气
但此刻人们都已从果园里走了出去
沿着那些通向园子的小路
我已经驶出很远了,黄昏中
小镇已经被我远远地抛在身后
而那片果园仍在远处闪烁,像一本书里的符号
我有一无所知的一个小时
天空的空白是我一无所知的一个小时
没有一只鸟儿飞过
也没有下午的云
一叠信纸的空白是我一无所知的一个小时
它没有墨迹、标点、字
地址也早已失效
夜晚的火光也是
我不知道它们是为着什么燃烧
又为什么熄灭
大海冲刷着海岸是
我不知道波浪为什么涌来
为什么退去
哪里才是一朵波浪要奔赴的目的地
那些漂浮的尘灰也是
只要我盯着它们
我就永远不知道它们的前身是什么
从哪里升起
又将在哪里坠落
一幅无名的油画也是
我一无所知的一个小时
我不知道我看见的画的色彩是什么
黄昏时,厨房里的蒸汽也是
我一无所知的一个小时
我不知道它有多少轮子,像一辆火车
要开往哪一片开阔地
蜜蜂把自己锁进一个箱子里
蒲公英要从一片原野走向哪一片空地
墙角边一张蜘蛛织的网
天花板上一个不知谁留下的鞋印
一架晚点的飞机在天上画出的云状轨迹
好像谁在天上哈出的雾气也是
它们是我一无所知的一个小时
是我一天当中的数次走神
是我打发时间的胡思乱想
它们组成了我一无所知的一生
它们身上的烟雾、水汽、斑驳的光线也是

刘棉朵,山东青岛人。著有诗集《呼吸》《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面包课》等。曾获诗探索奖青年诗人奖、刘半农诗歌奖等。

海男 画
诗与生活一同呼吸
——读刘棉朵诗集《呼吸》
张媛媛
诗歌源自呼吸。呼吸掌控着生命的节律。吐纳之间,身体与万物交换气息,人类由此与世界产生不可割裂的奇妙连结。而诗歌,正是呼吸在语言与文字中的体现。诗歌摹仿呼吸的节奏和方式,将生命的体验和感受,以最纯粹的形式表达出来。许多抒情诗人都将呼吸视作诗之灵魂,比如诗人柏桦认为“诗和生命的节律一样在呼吸里自然形成”[1],孟浪则直言:“有了诗歌,我毫不怀疑,语言本身所发出的呼吸比我们人的,更亲切、更安详。”[2] 法国汉学家艾田蒲(Rene Etiemble)更是表明诗歌的快感源自生理学,具体而言,源于肌肉和呼吸。对此,墨西哥诗人帕斯(Octavio Paz)的观点有所不同,在他看来:“我们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呼吸、节奏、形象和感觉的整体练习的运动中呼吸着这个世界。呼吸是一个诗意的动作,因为它是协调一致的动作。”[3]也就是说,诗歌的快感并非出自生理,而是寄寓于呼吸这一诗意的且协调一致的动作中。可见,呼吸不仅塑造了抒情诗的语感,掌控着情绪与思维的韵律,更将身体经验付诸于诗性语言,让语言回归其本质。
诗人刘棉朵最新出版的诗集便以“呼吸”为名。她将诗集名称译为“Spiritus”,这个词汇在拉丁语中除了代表呼吸,还蕴含着“精神”或“灵魂”的含义。这个译名的选择,充分展现了刘棉朵对诗歌艺术的独特理解和追求。她将呼吸作为诗歌的载体,让语言在呼吸的起伏中流淌,如同灵魂在生命的旋律中舞蹈。这意味着,对她而言,真正的诗歌不仅是情感的抒发,更是灵魂的呼唤,是生命与世界的对话。通过这个名称,诗人强调了诗歌与生命力、存在和感知的紧密联系,以及在呼吸吐纳间充盈的语言力量。诗集封面的一行小字已然透露她的初衷:“诗是我和语言一起呼吸”。
一、“半两烟火气”:平淡日常与真挚诗心
作为刘棉朵的诗学关键词,“呼吸”首先在诗歌的外部形式中表现出来,亦即诗歌的分行、停顿、速度与节奏。在她的诗歌中,呼吸是掌控诗歌节奏和韵律的首要元素。呼吸调节着诗行行进的速度,每一处分行,亦即每一次气息的停顿,既是诗歌语言的自然表现,也是诗人情绪起伏的重要标识。然而,正如深长的呼吸能够稳定心率一样,刘棉朵的诗歌并不追求情感或诗意的剧烈波动,而是保持着一种平静安稳的特质。她的诗歌语言展现了一种平淡、质朴且温暖的气息。诗人擅长梳理诗歌与生活经验的关系,着重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无论是田园的风景、厨房的琐事,还是旅途的所见所闻、阅读的所思所感,都深深地浸透着诗人的哲学思考。这些诗歌充盈着热烈的情感和生动的意象,仿佛“冒着馒头的蒸汽”[4],始终保持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
诗人刘棉朵能够从平淡无奇、习以为常的细节中捕捉诗意,将那些细微平凡的物品用语言的织物精心包裹,使想象得以无限延伸。比如,在《清扫》一诗中,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力描摹清扫卧室的场景,通过对外物的描绘引申到内心的情感表达——“对于世间的一切/我想让它们更加洁净、更加美好”[5];《你要想象一下我烙油饼的样子》一诗则将画面定格于一位主妇的劳动场景,烙饼步骤与心绪变化相互交织,美味佳肴和自然景象彼此相喻,在爱人依偎的温馨时刻,“身上传递着人间的烟火和人的温暖”[6];而《她整晚都在擦锅子》这首诗通过清洁、擦拭的动作,放空大脑,提纯灵魂,重新审视生活的阴暗面,透过无法避免的星星点点的污渍,诗人深刻地意识到:“生活中还有这么多痛苦、残缺和阴影/那些正是生活的记忆、永恒和魅力”[7]。清扫、做饭、洗涤等琐碎繁杂的家务劳动,被诗意的表达赋予了新的意义,不再是庸常无聊或辛苦劳累的象征。在诗人的笔下,家务劳动成为了一种思考生活的途径,一种修炼内心的方式。
在刘棉朵的诗中,日常事物与诗歌本身构成了密切的连结。诗人以细腻的笔触,不厌其烦地将自己写诗的状态与情境具象化,这一点可以从众多与“写诗”相关的诗歌标题中窥见一斑,比如《我要在病历上写一首诗》《我用沾着面粉的手写下我的诗》《我也有一种40℃的语言》《我想让一首诗冒着馒头的蒸汽》《生活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将被爱重新擦拭》《每一个词语都有一番它自己要说的话》……她会书写“一首诗与土豆的关系”——用剥土豆皮的手写下了一首诗,而后再用刚写完一首诗的手切开一个土豆。这样一来,诗歌便染上了泥土的气息,而土豆中也隐藏了诗歌的秘密。在她的笔下,写诗如同翻炒土豆丝,每个细节都需精心把控:
在一首诗诞生以前
要有7克思想,5粒花椒
3克来自大海的盐,还有半两烟火气
(《一首诗与土豆的关系》)[8]
这些细节和元素不仅表明了诗人创作的灵感来源,更指向一种质朴率真的诗学理念,强调诗歌创作的自然性和自发性,既具有超脱性,又不失现实感。她追求诗歌最本源、最真切的状态,就像真实的生活,毋需故意塑造或刻意掩饰,诗人相信——“我活生生地在人世间穿衣、做饭、走路时的样子/就是一首诗本来的样子”[9]
二、“少女的镜像”:女性视角与空间想象
作为一位女性创作者,刘棉朵在她的诗中展现出了“女王”般的特质,以绝对的掌控力驾驭着生活和诗歌。同时,她也审视着记忆中“少女的镜像”,以此映射出女性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共同的桎梏与困境。当然,“女王”和“少女”并非一组反义词,而是女性特征的一体两面,展现出了女性在不同生活阶段和角色中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女王”般的特质代表着女性的独立、自信和掌控力,展现出女性在生活与写作中的强大和魅力,而“少女的镜像”则映射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的纯真、敏感和依赖性,代表着女性内在的柔软和细腻。这两种特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诗人自称为“一百五十二平方米的女王”,这个称号不仅是自我认知的界定,也是生活态度的写照。她的房子,就像她的国土,被她视为自己的领地,并在其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洞察一切具体而微的事物,从家具家电到书籍文具,都在她的掌控之下。这个空间不仅是她的生活场所,也是诗意栖居的场域,是诗人的灵魂居所。在这里,诗人能够“把存在的变得虚无,让消失再次呈现”[10]。而在《女王》一诗中,诗人展现了作为“女王”的另一种权力——亦即无限扩大“虚无”,强调“没有”而非“拥有”的权力。她用诗意的想象和充沛的词语为自己加冕,成为诗歌的女王。在“女王”的世界里,她拥有足够的“没有”,这意味着她拥有足够多对未来与未知的想象空间。诗人通过诗歌创造了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文本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百五十二平方米的空间不再是局限,而是不断拓宽边界的起点,包容着一切“没有”。这样的文本空间是开放的、无限的,充盈着对未来的期待和未知的探索。
提及对于空间的想象,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表述甚是精彩,在他看来:“语词是微小的家宅,它们有地窖和阁楼。常用的意义居住在底楼,时刻准备着‘对外贸易’,和他人等价交换,这个过路人永远不是梦想者。登上词语这个家宅的楼梯就是一级一级地走向抽象。下降到地窖就是梦想,在不确定的词源的遥远走廊里迷路,在词语中寻找无法找到的宝藏。在词语本身中上升和下降,这就是诗人的生活。”[11]诗人刘棉朵亦是如此在词语的空间中升降,无论“大词”还是“小词”,都被她重新擦亮,焕然新生。她的诗中鲜有生僻的词语,但即便是那些平凡普通的词语,在她的诗歌中也能焕发出独特的光彩,不再索然无味。她超越了词语的日常用法,避免了流于表面的、陈词滥调的表述,而是将它们引向了更深刻、更富有内涵的方向。她的诗歌不满足于仅仅在“底楼”徘徊,而是探索语词家宅中藏匿于阁楼与地下室里的隐秘世界。诗人坦言:
我的诗是写给阁楼
写给抽屉和地下室的
我的诗写在我的大理石上
写在我黑夜的丝绸上
写下沉静的生命和光
(《我的诗只写给抽屉和地下室》)[12]
抽屉代表着诗歌的私密与隐晦,地下室象征着诗歌的幽暗和未知。而阁楼在文学和文化中常常意味着封闭、隐蔽、禁锢和边缘化,同时也暗示一种女性的地位和命运——比如《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妻子,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囚禁她的阁楼便隐喻着被男权社会压抑、遮蔽、孤立的境地。在19世纪,一位女性作家不仅必须居住在男性拥有和建造的房屋中(诸如狄金森、勃朗特、罗塞蒂等女性作家都被囚禁于她们父亲的屋子之内),她还同样不得不待在男性作家所构建的艺术宫殿和虚构世界的囚笼中,承受着各种无形的约束和限制。[13]当代社会,女性作家仍然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尽管她们可能在现实中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居所,但是她们仍然难以逃离社会与文学的双重禁锢。
在《娜拉之死》、《阿黛拉》、《贞德》等诗中,刘棉朵以女性视角探讨了女性在文学与历史中的地位和命运。这些诗歌揭示了女性在文学中的困境,以及她们如何通过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在她的笔下,娜拉代表着那些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她们在困境中挣扎,最终选择死亡作为解脱;阿黛拉是一个坚定而孤独的女人,不会轻易从生活现场溜走,人世孤独,她只满足于自由与死亡;贞德则褪去传奇与英雄的光环,还原为洛林乡村一个纯真无邪的傻姑娘。女英雄脱去铠甲,露出的是内心的柔软。或许,女诗人挣脱桎梏的方式就是成为“女王”,但“女王”又何尝不是一种“少女的镜像”?
三、“隐秘的蜂巢”:幽微言说与身体经验
刘棉朵的诗歌语言干净、通透、流畅而内敛,然而在“明朗的呼吸和合适的节奏”[14]之外,潜藏着幽微的、不可捉摸的情感与思绪。正是这些难以言喻的情绪与感受,使她的诗歌保留着某种神秘性的内核。一首诗的诞生伴随着它自身的犹疑抉择,词语的歧义丛生与意境的模糊朦胧造就了诗意的留白,“某些无法确定的事物”[15]便在其中暗自涌动。这种隐秘的、不确定的事物,以不同的面目反复亮相于刘棉朵的诗中。在《找斑鸠》中,它是“一种田野上的事物和影子”[16], 不知道藏身何处,也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它的样子;在《回家的路》中,它是“另一些无家可归的事物”[17],说不清道不明具体为何物,但可以肯定它从光线幽暗的小路跟随“我”回到了家中;在《一封信可以支配的事物》中,它是时间、地址、语言、邮递员、收信人等一系列被罗列出来的名词之外,等着被下一封信带走的其余的部分。诗人以看得见的事物为载体,巧妙地捕捉了那些看不见的存在,从而让诗意更加幽微深远。
在这本诗集中,“隐秘”一词的出现频率极高,比如一颗洋葱的腐烂“由隐秘处开始”[18];两只相爱的天鹅,相互探寻,“并念出那些隐秘的声音”[19];三月的跨海大桥下,被切割的渤海“只遵循自己隐秘的忽而自由和律法”[20]……最具代表性的诗是《隐秘的蜂巢》,这首诗脱胎于北马其顿纪录片《蜂蜜之地》(Honeyland)。纪录片中的女养蜂人哈蒂兹使用世代相传的古老方法采集悬崖峭壁隐秘蜂巢中的野生蜂蜜,“她从来不忘/只取一半,另一半要留给蜜蜂”[21],遵循着维系自然平衡的古老哲学。诗人可能受到了哈蒂兹的启发,她在描述这个场景时,采用了相同的方法——点到为止。她没有详细描绘整个采集过程,也没有深入探讨哈蒂兹内心的波澜。相反,她选择了简洁、含蓄的表达方式,将更多的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这种点到为止的写作方法,其实也是诗人发现生活中隐秘诗意的一种方式。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更多的余味和深意则留给了诗歌自身的想象力。又或者,词语就像是蜜蜂的巢穴,它们密密麻麻地按照某种神秘的秩序堆叠排列在一起,形成了迷宫般的小小世界。而诗人在这个隐秘的蜂巢中,时而迷失于甜蜜的陷阱,时而又找到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就像一个有窥视癖的蜜蜂/妄想从词语的缝隙里找到/那些没有说出的秘密”[22]。
罗马尼亚作家埃米尔·齐奥朗(Emil Michel Cioran)说:“对于一切看得见的事物,我们自愿地赋予它们气息。一个呼吸器官难道不是某种存在吗?——由于存在看来比它的对立面更可取,我们创造了呼吸的习惯,感受呼吸的好处。是什么驱使我们懂得只想象它,在延长我们的半醒状态中维持它的生存?”[23]或许是从呼吸这个协调一致的动作中获得了启示,刘棉朵的诗歌充分调动感官机能与身体经验。词语如同呼吸一般自然流淌,它们是身体的声音,是心灵的倾诉,是情感的宣泄。词语在呼吸中找到了生命的力量,如同星辰在夜空中闪烁,各自独立,却又共同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宇宙。正如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说,“身体能够呼吸,凭借呼吸吐纳,身体化为字句,并在话语中得到暂时的安宁。而一旦呼吸化为字句,身体就以呐喊呼吁的形式传递给了他人。”[24]这是一种身体的转译,一种情感的逃逸,一种灵魂的共振。这种传递并非直接言明,而是隐秘幽微地通过字句间的空白、呼吸中的停顿以及身体的姿态暗示出来。在刘棉朵的诗中可以辨认出一种虔信的身体姿态,借助祈祷的动作,灵魂与宇宙相互感应,彼此连通。一种超然物外的宁静与深沉浸润于呼吸之间,让人不禁联想到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诗中的迷人声调:
呼吸,你——不可见的诗!
始终为谋求自己的存在
而纯粹被交换的宇宙空间、平衡
我在其中律动地发生。[25]
2023年11月17日
[1] 柏桦语,见《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2] 孟浪语,见《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3] [墨]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歌与呼吸》,《弓与琴》,赵振江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第258页。
[4] 刘棉朵:《我想让一首诗冒着馒头的蒸汽》,《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224页。
[5] 刘棉朵:《清扫》,《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171页。
[6] 刘棉朵:《你要想象一下我烙油饼的样子》,《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188页。
[7] 刘棉朵:《她整晚都在擦锅子》,《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135页。
[8] 刘棉朵:《一首诗与土豆的关系》,《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174页。
[9] 刘棉朵:《一首诗总会在一些选择上表现出它的犹疑》,《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131页。
[10] 刘棉朵:《一百五十二平方米的女王》,《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158页。
[11]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88页。
[12] 刘棉朵:《我的诗只写给抽屉和地下室》,《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158页。
[13] 参阅[美]莫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14] 刘棉朵:《一首诗总会在一些选择上表现出它的犹疑》,《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130页。
[15] 刘棉朵:《野鸭》,《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7页。
[16] 刘棉朵:《找斑鸠》,《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3页。
[17] 刘棉朵:《回家的路》,《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14页。
[18] 刘棉朵:《一颗洋葱的腐烂》,《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26页。
[19] 刘棉朵:《天鹅》,《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40页。
[20] 刘棉朵:《从跨海大桥上穿过渤海》,《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52页。
[21] 刘棉朵:《隐秘的蜂巢》,《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81页。
[22] 刘棉朵:《我在我的外面》,《呼吸》,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92页。
[23] [罗马尼亚]埃米尔·齐奥朗:《着魔的指南》,陆象淦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24] [美]朱迪斯·巴特勒:《战争的框架》,何磊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
[25] [奥]里尔克:《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林克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9页。

张媛媛,蒙古族,1995年出生于内蒙古通辽市。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诗歌与评论见于《诗刊》《民族文学》《星星诗刊》《当代·诗歌》《作品》《青年文学》《江南诗》《诗探索》《上海文化》《当代作家评论》等。著有《耳语与旁观:钟鸣的诗歌伦理》《过敏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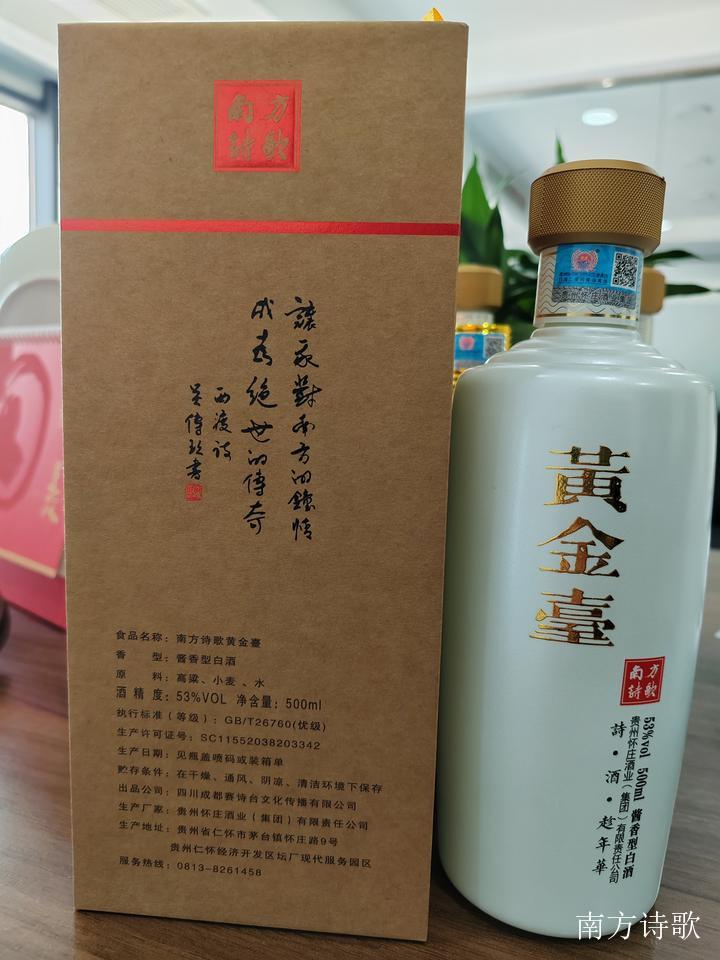
让我对南方的钟情
成为绝世的传奇
——西渡
南方诗歌编辑部
顾问:
西 渡 臧 棣 敬文东 周 瓒 姜 涛
凸 凹 李自国 哑 石 余 怒 印子君
主编:
胡先其
编辑:
苏 波 崖丽娟 杨 勇
张媛媛 张雪萌
收稿邮箱:385859339@qq.com
收稿微信:nfsgbjb
投稿须知:
1、文稿请务必用Word 文档,仿宋,11磅,标题加粗;
2、作品、简介和近照请一并发送;
3、所投作品必须原创,如有抄袭行为,经举报核实,将在南方诗歌平台予以公开谴责;
4、南方诗歌为诗歌公益平台,旨在让更多读者读到优秀作品,除有特别申明外,每日所发布的文章恕无稿酬;
5、每月选刊从每天发布的文章中选辑,或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