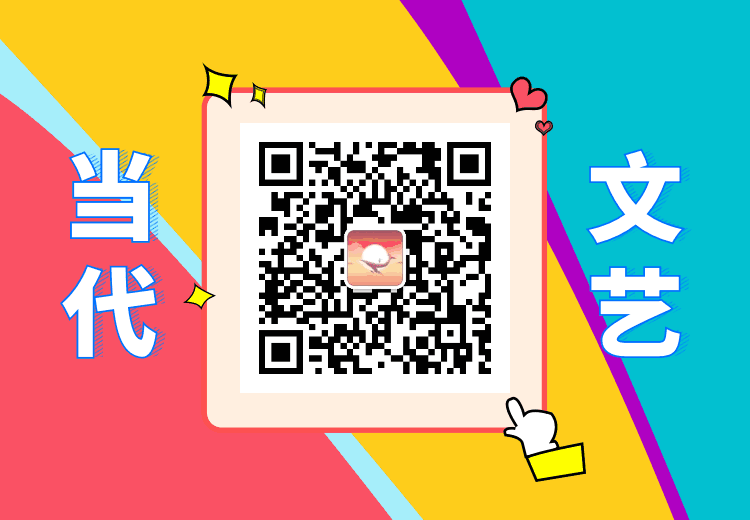乡 音
作者:王玉权
五一例假,下乡潇洒。
走到村头,恰逢二呆子骑辆破旧的机动三轮上街。一见我连忙停下。
“大先生,嘎(家)来啦!好下(些)时不见啦!”胡子拉碴的二呆子迅速地掏出包《红南京》抽出一支敬我。“丑烟,丑烟。老邻居啦,回头到嗯嘎(鼻音,我家的意思)来玩噢!"说着发动了车,扬了扬手,向三垛镇方向匆匆开去。
算来,他比我小几岁,也该近八十的人了。仍如从前,一天苦到晚,没个闲时。
听大女儿说,大冷天的,也不怕冷,下河摸歪歪(河蚌)卖。一有工夫,就上街收破烂。一院子塑料瓶罐,黄版纸片什么的堆满了。一刻闲不住的典型的老农民。
才走几步,后面一辆摩托风驰电掣般从身旁滑过。来人立马刹车。惊喜地叫了起来,“这不是王老师吗?快到嗯嘎坐坐!”异常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握了又握,摇了又摇。他家就在村前头一排,柳南路旁。门前花木扶疏,装潢考究,四开间大门大院,很显气派。看来小日子过得不错。
我说,“何的(以后的意思)来玩。”他不由分说,拉着我开门进屋,安排我在大客厅沙发上就座。忙不迭地,又是沏茶,又是递烟(软中华)。又抱怨说,“老奶奶(后一奶字读如耐音)不晓得到哪块充(读第四声)魂去了。老师阑板(极少)来,不见一口汤水,才叫人过意不去哩。”我说不必客气。
环顾一下室内,我连声称赞。他说,马马虎虎(读若乎音),瞎混。带我粗略参观了大大小小十几间房。卧室厨房书房卫生间,家电齐全,衣被崭新,窗明几净,装饰华丽。他说,就我们老俩口守着这一帐空落落的大房子。儿子媳妇孙子都到大城市去了。我在邻镇打份工,天天早出晚归。庄上田都流转出去了,没田种。不得劳事做,闲着也是闲着,打麻将也不是个交易,就找点事做做。一晃七十出头了,再混年把吧。
庄上七十左右的,差不多都曾做过我的学生。他叫顾仁美。父亲顾汝槐,成天眯着眼笑模悠悠的老支书。母亲周兰子,刷刮俏正一农妇。大哥顾仁华,怕有八十了。小弟顾仁忠,印象深刻。六七岁在我手上开蒙,聪明伶俐,小名三毛。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办了家企业,成了大老板。仁义,很讲手足情。慷慨解囊资助大哥续了弦,资助二哥砌了这所好房子。这种弟兄亲情目下是不多见的。可惜好人天妒,英年早逝,令人嗟叹。
进了村,老家那条巷子里,十家有八家关门上锁,背井离乡打工去了。街巷全铺了水泥路,异常整洁。就是见不到袅袅炊烟,听不到鸡鸣犬吠,空旷阒寂不见人,没了生气,冷冷清清。
一处掩着门的院内,传出了熟悉的乡音。从掩着的门缝中可见老顾许大娘老俩口在家好似绊口舌。不敢贸然闯入,只是好奇地驻足听了一会。
许大娘的声音,老了依然清脆。虽是骂人,但口气不刻毒。“你个老军犯(江淮一带独有诅咒语。元蒙时将退役老军安插在南人家中供养,作威作福苛虐南人,世代传下的历史遗响。)啦嘎(哪个)瞧得起你。当初,我那娘老子看走了眼,把我许配给你。我一朵花插在你这一沱牛屎里,跟你吃了一世瞎头苦。那刻儿虽说是新社会了,也由不得自俺作主。苦命!
你个丑八怪,一脸骚颗子,像张猴子屁股。自俺认不得自俺,卵本事不得一个。就会个盘泥巴捧牛屁股的屌本事。猪鼻子插大葱,装得像太公。一天到晚指五责六的,儿子女儿哪个欢喜你啊。癞猴子跳戥盘,自称自贵,跩得二万似的,也不撒泡尿照照。癞蛤蟆吃天鹅肉,生米煮成了熟饭,我只好眼一闭,泪往肚里流。不情愿有什么法子,苦命!偏偏你这老八怪不知足,花心大萝卜。你道我不晓得?个梦!你偷偷摸摸跟老相好鬼混,说不够笑不够的。我又不瞎不聋,看在眼里听在耳里闷在肚里不啧声罢了。你个不要脸的老军犯,老囚犯,老狗日的!骚牯子,骚鸡公,骚种猪!哪天惹老娘火起,把你那东西掐下来喂狗,省得折磨人……
不得了啦,这个许大娘像是真的动气了,洪水滔滔似的。
老顾还嬉皮笑脸哩,打断了许大娘的话,央求说,求求你,少念遍紧箍咒吧!老念这本灶王经,耳朵都长茧了。烦死人!孙子都半茬子高了,还吃哪门子醋?菩萨,向你作揖磕头了!水有面子树有皮,在嘎里听你数落倒也罢了,千万别在外场敲锣。做一世夫妻了,男人跟女人佮张脸呢。
说罢,当真跪下作揖,像个犯错的伢子。
见状,我差点笑出声来。自责成了听壁脚的小人。不能再逗留的,赶紧开路。
村里,老人不多了。我的发小,大都一一凋谢,令人伤感。女人天生比男人长寿,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不少。我那庄上的老亲家,地处十字路边,自然成了老女人俱乐部。
两间小屋,堂屋里支了两间土灶,抵墙放张八仙桌,空间已不多。七八个年纪大的,长凳小杌甚至灶台下,高朋满座,济济一堂。
见我进来,纷纷向我打招呼。大先生,嘎来啦,嘎来啦,到姑娘嘎过过啊。
驹子女人说,城里乡下两头跑跑,蛮好的。师娘走了后,你是跟儿子过,还是一个人单过?我说,老狗恋穷窝,习惯了,还是一个人清闲自在。
驹子女人说,不心慌啊?自俺烧煮自俺洗刷,多烦杂。你又不差钱,找个五六十岁女人来,日里替你烧煮,晚上陪你睡觉,多好!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我说,由儿女轮流送饭,用不着烧煮。看看书写写字逛逛街,没事找事,打打岔扯扯雅子(土语,分分心的意思),就一点不心慌了。就像你们大家伙聚聚头,东拉拉西扯扯,就忘了烦恼,打发了时光。这个年纪的女人都有儿孙了,惹一身臊气,那麻烦可大了。不能玩!你们说呢?一个个都说,是待(的),是待(土语,表示应答)。指着我拍着巴掌笑得前俯后仰。说到这方面话题,她们顶来神儿。
听一班老女人闲扯,比在手机上获取的信息量有益得多多。手机上信息如天上云朵。这里靠谱。虽家长里短,但接地气。
庄西头疙瘩鼓大孙子在外头发财了。这小伙有出削(出息),仁义。庄上的路灯全是他出钱装的。光是修土地庙一笔,就捐了三万块。有的人越有钱越小气,啬皮沟子,把个小钱看得比磨盘还大。
巧兰的两个丫头也能干。一个在杭州,一个在街上开店,都混得不错。
有出削的多呢,过年那会,小汽车、大卡车开会啦,真开了眼。小辈子胎咍子孙多了,比我们老辈子种死田灵光。
也有不胎咍的,大驹子家老二流浪在外多少年了,从小光棍熬成了老光棍。怕有五十大几了吧,这刻儿还不知是生是死呢。
也有人叹气咳脑的,说子侄们从外头嘎来,连个芝麻屑子都不曾见过。什么为奇宝?眼睛长到头顶上去了。
有的老人牢骚满腹。孝顺子孙有,忤逆的也不少。嗯虽说有几个儿子,有幺子用!三个和尚没水吃,哪个茄子好做种?想想伤心。
人的心窝塘子不得满,哪嘎(个)知足!我说现时的日子算天字第一号了!过去地主也不见得天天见荤腥。现在的人,无荤不下饭,比地主还地主。不晓多快活了,还叽咕碌碡的,(方言,发泄埋怨不满情绪)真正折福!
我们呐,老了。噜苏两句,小的就烦了。他们不晓得从哪块学来的歪风,过生日吹蜡烛,多不吉利。结婚穿白纱,多晦气!死人才穿孝呢,长命灯要亮着才好呢。跟这代人作不了的气。
大姑娘不怕丑,穿件短抓抓(zhua读第二声,土音)的褂子,露出肚脐眼子。更丑的是,那个什么玩意儿,紧箍箍的,勒出两个奶子,露出大半边屁股。哈美呢,呸!
顶看不惯吃肉骂娘的那班骚怂,叽毛碌碡的(较叽咕碌碡升级了),说政府坏话。当家的是个泔水桶,十个指头不一样长,哪能个个都中意。有碗饭吃就不错了!有肉吃更是天堂日子!
……
玩了几天,舒了心,怡了情,收获了几抬笆。从心底里赞叹,好善良的底层百姓,多朴素的感恩情结,多自觉地维护传统文化!愤青愤老们该扪心自问,你心头少了些什么?
方言土语,形诸文字很困难。比如碌碡是农民最熟悉的农具,压在它下面的东西总会发出不同声音的。叽咕碌碡这一方言便很生动形象了。不一定对。还有许多,敬请方家指正。
【作者简介】
王玉权,笔名肃月。江苏高邮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退而不休,码字怡情。不钓名和利,只钓明月和清风。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