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孙玉芬
妈妈心灵手巧,不管是农活、家务,还是针线活,样样都是里手。今儿就说说妈妈的针线活吧。
妈妈的柜子里珍藏着两个崭新的小针线簸箩:白色的柳条编的,精巧细致,很是美观。那是妈妈的嫁妆,妈妈的心爱之物。里面有大大小小的绣针、五颜六色的绣线,崭新的顶针;有一个粉盒子,里面盛着一只漂亮的银镯子,做工精致,滴溜当啷的,叮咚作响,很是悦耳,可爱极了!可能我小时候戴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鞋、靴样子分门别类地夹置于一本发黄的旧本子里。那旧本表皮是灰蓝色的贴布粘连,厚厚的一本,长方形的,纸上没字,有几道横格,大人、小孩各种鞋样夹在其中。此物件我已见证它30多年了。至今历历在目。平时,妈妈一般不用它。而平时用的则是随意放置于在窗台或是床上的一个自制的针线“簸箩”。它是用旧纸壳制成的:底部为圆形,周边为六边形,下窄上宽。它是妈妈用麻线精心缝制而成的,美观大方,结实耐用。里面放了妈妈所有的针线家当:一把木制的一尺长的尺子,一个两米长线的粉袋子(做被褥或棉衣打直线用),剪子、两把锥子(一把是铜把子,一把是木把子)、顶针、大小不一的针,白的、黑的粗棉线,各色化纤细线,还有专门缝被褥的混纺白色粗线……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一双棉靴
记得小时候,1971年冬,我上一年级。那年连下几场雪,地面上厚厚的有一尺的雪。胡同里中间用锨铲出一尺宽的人行道。我穿着棉衣棉裤,妈妈还把我的裤脚系结实,围着围巾,穿着妈妈做的新棉靴,“咯吱,咯吱”地踩在雪路上,一步一步往学校走。我的心像飞起来一样,甭提多高兴了!因是新棉靴,暖乎乎的,靴底有小小的凸起,走起路来不滑。我像只欢快的小鸟,很快又很酷地到校了。心里美滋滋的,小确幸。一般我穿新的,过两年穿小了,妹妹老二、老三再穿。我还记得妈妈是怎样给我做新棉靴子的。
1、打袼禙(家乡话,打quezi)。制作鞋底需先打“袼禙”。夏天闲暇时此项工作由姥姥担当。袼禙是用糨糊将棉布一层层粘合而成。姥姥总是将拆洗的旧棉布拼接糊在木板上,一层一层的,3层~5层棉布粘合在一起,置于阳光下晒干即可。
2、粘靴底子。第一步,先拿鞋底纸样按在袼禙上,拿圆珠笔画下来,再按线准确地剪齐。如此这般,每一只鞋底备3层~4层。第二步,用新平纹白布(我们常用现成的白色“寸带”),斜向剪成宽6分左右的鞋掩条。第三步,用糨糊将这些掩边、包裹的袼褙粘合在一起,粘好后的鞋底放在热炕头,上压重物煲干。
3、纳靴底子。纳底子是个功夫活,我妈只要有空闲总要见缝插针,纳上几针。鞋底的针脚需要整齐划一,大小一致,松紧度一致。只见妈妈右手拿着铜把锥子扎眼,然后递针,用麻绳绕锥子把缠几圈勒一勒紧,(吕剧李二搜改嫁中的李二嫂纳鞋底,表演的就很到位)。再翻过靴底,进行下一针。通常称纳好的鞋底为“千层底”。
4、做靴子。按靴样子下料,靴面是蓝色灯芯绒布;絮棉,棉花帮各部件
先缝制(引一下)以固定,再将棉花帮与底缝在一起,成为棉靴套;纳帮,掩边,上鞋(靴,放进絮棉套)把鞋帮缝合在鞋底上,称上鞋。我的靴子是明上。最后,楦鞋,即为鞋(靴)整理定型,大体分两种形式,一是用鞋楦头,一是用碎布团用力塞入鞋(靴)中,使其撑开。我的用后者。一双靴子做好了。钉上几个铆钉,穿上鞋带,大功告成。呵呵!靴子就可以上脚了!哎呀!妈妈做一双棉靴太不容易了,好佩服、好羡慕!
一床被子
1980年9月,为了考学,我要配戴眼镜;我要住校。周末爸爸陪着我去博山淄博第一医院看眼,验光;第二周复查,配眼镜。后来眼镜由张哥替我取回。要住校,需要准备一床被子,褥子或毯子及床单。妈妈买了一床白色棉质里子,一床红色碎花表子,拿着旧棉絮网了一下,开始做被子。被里、被表下水 晾干。先在地下铺一张大席子,两个人拽着白被里两头铺好,再将旧棉絮一小块一小块絮在白被里上面。絮棉花是个技术活,要续得均匀。接着将新被表铺在旧棉絮上。妈妈右手中指戴着顶针,大拇指与食指捏着大针,穿好混纺粗白线,开始缝制被子四周。之后,我帮妈妈用粉包打好三行直线。妈妈就将带线的大针头,以斜穿的方法从被子上面穿到下面,空适当距离(1.5-2寸的长度),再从下面回穿到上面来,大拇指稍用劲捏着前面,再用中指上面顶针小孔,顶着针尾。顶过后,再顺手一拽,针线就全部出来了,这样就是走直线。又竖着引了三行。就这样,不过半小时一床“新”被子做好了!加上一条打了一个补丁的旧毯子和半新的小床单。这就是我上学住校的的全部家当了。就这样,求学的“包裹”或家当从高中到大学跟了我整整五年。之后我被分配到辛店电厂工作,结婚,生子,那床被子一直使用着,只不过后来它由被子变成了“褥子”,在小床上发挥着它的“余热”。

再后来,大概2013年儿子结婚,我们搬新家。因为太旧了,也不知丢在何处了……但它一直在我的心里藏着,暖着,爱着!结婚前,那被子妈妈总要一年为我拆洗一次;结婚后,我自己也会拆洗了。只要看着妈妈做过一次,我就会比着葫芦画瓢,自己动手。拆洗后,自己做被子,做褥子;孩子的棉衣、棉裤等。后来做起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90年代,我还能看图裁剪衣服:可体的玫红人造棉百褶连衣裙。因缩水,穿了几次变小了,又改成上下两件套;褐色碎花人造棉两件套。最有成就感的是1.1米白色真丝印花连衣裙。穿着它美了好几年!满满的成就感、自豪感和幸福感。这一切的起因,都来自妈妈为我做的那一床被子……

自做的连衣裙(1.1米白色真丝)
“老衣裳”——寿衣
老人死去才穿的衣服叫寿衣,也称为殓衣或遗衣,都是为老人提前做好的。一般是棉服,是希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吃饱穿暖。对于做寿衣,妈妈60岁之前,是给亲人做过好几套。每次做都分外虔诚,怀着崇敬和爱戴之情。姥姥的,爷爷的,我爸爸的(爸爸突然病逝,做的有点急,妈妈悲痛欲绝,含着泪,手颤抖着……在婶婶、大娘的协助下完成)还有其他孙家老人的。妈妈过了60岁,就开始准备自己的“老衣裳”了。拿出柜子里的两个宝贝——针线簸箩;拿出两身做寿衣的紫灰色、浅灰色的有点滑溜溜的布料;拿出做鞋、靴的各种材料。有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夹衣、棉衣两套寿衣;单鞋、棉靴两双寿鞋。鞋面上还有绣花。断断续续,为此妈妈花费5年时间,终于完成为自己做的“老衣裳”,心满意足,没有一点遗憾。妈妈50多岁时,得到了姥姥的水晶老花镜。铜色镜框,小小的圆圆的水晶镜片。右侧那条镜腿还缠着线固定,后来掉下来了,妈妈直接用结实的粗线代替,挂在右耳上。再后来,2000年8月31日妈妈去世后,那副水晶老花镜被我大姨家的大表姐拿走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1995年的暑假我回家看妈妈时绣鞋面的情景。妈妈戴着水晶老花镜,一手捏着绣花针,一手拿着鞋帮子,按花样子一针一线地绣着。先是用褐色的绣线绣枝干,就像斜着刀切土豆丝一样,密密的细细地排列着,绣完枝干。我迫不及待地用手摸一摸,软软的绒绒的滑滑的,好看!再换绿绣线绣绿叶。绣线有深绿有浅绿,一针一针的一片一片地绣,要绣出层次感。绣完,我又禁不住摸一摸,好看!最后绣花朵,绣线有红色、紫色、粉色,还有黄色与白色。花瓣由深到浅,花蕊黄色兼有白色。妈妈极有耐心,极有舒心。因有娇女陪着,一边说着,一边绣着,那么自如,那么娴熟;那么亲切,那么温馨!那镜头,那画面,历历在目,仿佛如昨。“电影”般永远定格在那年,那天,那时……“老衣裳”在她65岁时做好,之后,就恭恭敬敬地放在柜子里了。每年六月六总要拿出来晒一晒,再收到柜子里。没想到三年后(2000年8月31日)妈妈就穿上了自己做的“老衣裳”驾鹤西去。那天我看到了妈妈身上的那寿衣,那寿靴。享年68岁的妈妈走了,永远地走了!我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喉咙……


妈妈尊老爱幼,善良泼辣能干,针线活是那样的棒:不仅被褥,大人小孩衣服、鞋,而且还会踩缝纫机,会盘扣(这个较复杂,我没学)。在农村家家都有针线簸箩,簸箩里盛着的不仅仅是针线,也盛着勤劳,盛着心灵手巧,更盛着全家的针线活。银针深入的是心底,针线连接的是关心。有慈母言传身教的帮带,更是深深地吸引、鼓舞和影响了我。我的针线活也是蛮不错的!
再也不见了——装满情装满爱的妈妈的针线簸箩……
作者简介:孙玉芬,淄博市淄川区人,淄博师专中文系(后曲师大)毕业,在山东辛店电厂工作32年。其中从教21载。写过教学论文和“豆腐块”。余暇喜欢看书、朗读、撰文、赏景、拍照。在公众号发表作品40多篇。像蚂蚁般工作、蝴蝶般生活,乐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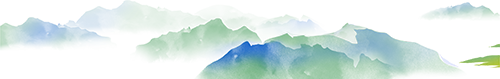




玫瑰手绘折扇、玫瑰国画
订购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