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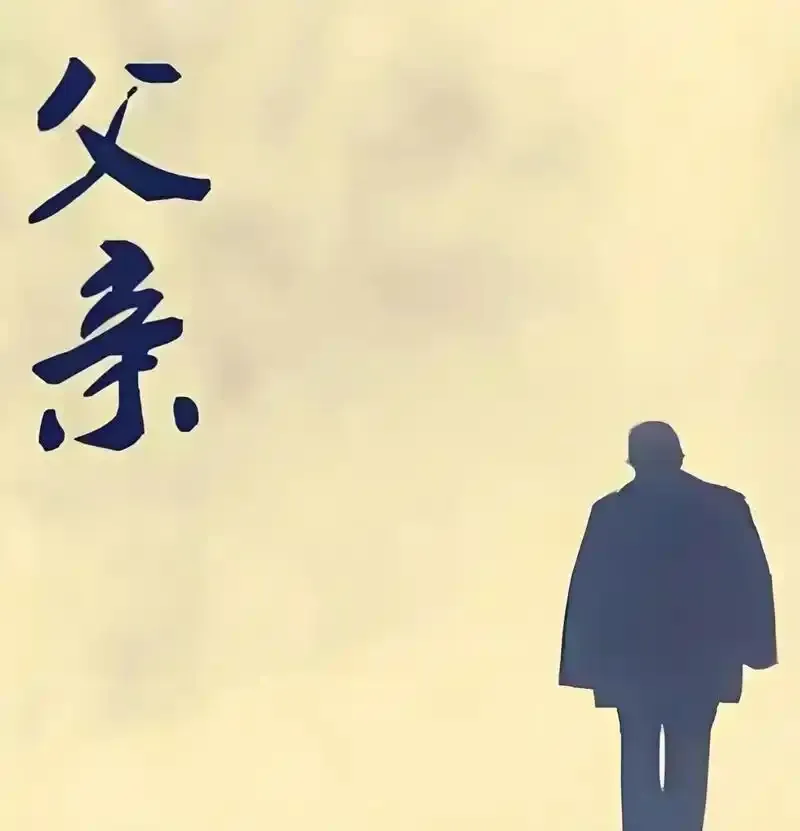
父亲
文/丛正
小时每当和父亲回老家时,总能听到乡亲们亲切地喊父亲的小名,就像喊着漂泊异乡的亲人,充满乡愁的情丝。父亲是寡妇带大的,很小时亲爷爷就去世了,奶奶带着还小的三个儿子艰难生活,困难时据说是要过饭,即使经济发达的现在,一个寡妇养大三个儿子也绝非易事,我长大后回想奶奶身高足有170cm,山沟里生活什么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干净漂亮,父亲31岁有我,我长大有记忆时奶奶已接近60,我感觉她十分符合现在美女的标准,皮肤白皙身材高挑,这是我十几岁而他60多时的印象,试想她30-40岁时该是多么魅力十足。大爷为人处世沉稳,谨言慎行那种,直到后来当了一辈子乡村学校校长,始终被上下级亲朋好友所称道,我印象中他不说话很有威严那种,而父亲却为人开朗口才极佳,可想而知他俩小时,奶奶对爸爸发自内心的喜爱,可能正是这种寡母的宠爱铸成爸爸那种狗见烦的性格,家乡是个封闭的小山沟,九曲十八弯的山路通向乡里,然后再去县城才能连上火车,整个山沟人数不多我们姓氏是绝大多数,据说最早一对夫妻挑着扁担从山东而来在此繁衍生息,每次回大爷家都能看见流传几百年的家谱,传言我们最早来自匈奴王子,来自漠北草原,但我看同宗人的长相没有任何草原民族的痕迹,汉人特点却很突出。
由于家里穷,爸爸去帮同村的刘姓地主放牛管吃,每年好像还给点粮食,在穷乡僻壤困苦时期,人最大负债就是鼻子下的嘴,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常常给我们展示扔石子打死叼鸡的黄鼠狼的本事,作为兽医保护鸡免遭黄鼠狼咬死,打死后他常常把它挂在高处示众,这些都是放牛娃的绝技。他常说放牛锻炼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试想一个十几岁山村娃娃赶着一群牛在山里,怕又有什么用呢,只有什么都不怕才有条活路。跟别人童年一样,爸爸童年也十分顽皮,甚至可以说顽劣,看到正在繁衍后代的狗夫妻,他们会抬着全村示众,别人经常找到家里,奶奶总是护着自己的儿子,作为村里大姓,又是寡妇宠孩子,一般人也就不了了之了。
庆幸的是奶奶娘家本来有文化人,在那个大多数人都文盲的时代里,13岁时送他去上学,可能聪慧是天生的,干过放牛这种低技术工作的孩子,学习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奶奶很有远见,含辛茹苦也要让孩子读书,山沟里一年能打多少粮食呢,农业经济学有句话:农业剩余生产力是其他行业发展的基础,薄薄一层土的山沟,供了两个高中生确实不易,读完中学通过招考进入了兽医学校学习,这对于乡村孩子来说绝对是千载难逢的契机。
父亲也就170左右,他常常说小时缺营养没长起来,看着奶奶的身高,我相信缺营养可能真会个矮。父亲说他兽医学校时期当班长,我其实一直以为他是吹嘘,但大爷却也充满佩服得说他弟弟曾经是班长,大爷性格很稳健,我的性格和大爷很像,大爷退休后教育颁给他从教在党好像是40年的证书,但他内心深处也佩服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弟弟。兽医学校中专还是大专不得而知,但现在已经是医科大学的一部分了,过去教学十分严谨,父亲常说老师因为女学生怕解刨尸体而大发雷霆,当时粮食定量供应的,正在长身体的男孩显然不够吃,总有女学生把吃剩的饭票给他,爸爸每每回忆起来,总觉得错过一段美好姻缘,也引来妈妈很多抱怨。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文攻武卫在校园里蔓延开,父亲卓越的口才和公开演讲能力,可能加上原来是班长,被推举成一号服务员,我大学毕业后估计也就是现在的大学生自律委员会负责人的意思,说实话我从小听他说这段经历一直认为是吹嘘,这么好的位置为啥没留校而分到国营农场做兽医师呢?但是做校长的大爷说这是真的,后来父亲参加工作的同事证实爸爸报到的行李里居然有20几颗手枪子弹。这个在当时可是大事,农场成立调查组回学校调查,我想是寡妇带的孩子心地善良,在武斗的时候保护了许多老师干部,大家都是极高的评价,而且说想调回来留校的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这很不容易的,当时的人十分较真的,国营农场不允许家属捡大豆地里剩下的豆子,物质短缺的年代很多家属偷偷去捡,看地的真会向人群开枪,真是出自对共有财产违纪私有化的痛恨。
毕业时正是文革动乱时期,父亲代表学生去农业部谈分配的事,等了好久才见到主管部长,当时的部长显然予视到个人未来命运多舛,但还是极负责任得告诉学生们,选择黑新蒙包国家分配,其余回乡分配,爸爸年轻时极度反感偏远山沟的穷苦,毅然选择了黑龙江三江平原的农垦局建设兵团。当时的三江平原即北大荒确实荒凉,很像现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它们本来也是相连的,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个和远东地区资源丰富很像,还有个极大的资源优势就是黑土地,从我小时候放假出去钓鱼,所见之处皆为黑土,我的头脑中土就是黑的,但是读研通勤有个土壤学研究生,他说除了黑龙江东部地区,国内其他地区黑土很少。我是文科生我不懂土壤有机质和颜色关系 ,但是小学时班级集体去割豆子赚班费,粗壮的豆秸像小树干一样非常繁茂得长在黑黑的土壤上,人在陇间干活根本看不见,而且早期土地也不用怎么施肥。
父亲从小在穷山沟长大,山地上面一层薄土产的粮食极少,主粮都是地瓜玉米高粱,当然现在这些杂粮成为降压降糖的帮手,售价每每比细粮高很多,我每次回老家除了喜欢几顿地瓜外,对高粱米饭极不愿吃。三江平原作为国内最大商品粮基地,粮食单产是极高的,据说4/5是商品粮运出。一次大爷带着孩子来农场看我们一家,看到农场收割被大大惊讶了,作为山区校长的他说你们收割机收完粮食地上剩下的都够我们的亩产量了,这个或许有些夸张,但是承包单干后承包者收完地后常常挖准备冬储的田鼠洞,常常会回收十几麻袋,说明实际亩产十分高,正如远东地区大面积刚开发的黑土地一样肥沃。当时农场是军垦农场,也叫沈阳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主要是建国后转业的军人构成,我记得有铁道兵、航空兵好像还有干校,这些人不打仗了需要安置,而黑龙江东部有大片的未开垦土地,建设了大量的生产建设兵团,但是作为农业生产组织,农业畜牧业等生产技术人员奇缺,父亲这些农校畜牧学校毕业生非常受欢迎。我小时候记得父亲一直很忙碌,有个独立的兽医工作室,工作室里注射器听诊器及各种各样兽药十分丰富,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是资源分配主体,对专业技术人员配给十分充足,而且我家是连队第一家住进砖瓦房的,由于属于新建居民点很多房子是茅草土坯房,这种房子通电后有很大失火的风险,砖瓦房子住起来就舒适安全多了。我记得国营农场机器设备配给现代化程度是可以的,有很多德国进口的拖拉机,我们叫大马力,还有各式各样进口农用车。有时国家统一发展经济也有一定优势,国家从西方统一进口的夏洛克猪身条长抗病性好瘦肉率高,在生产建设兵团首先推广养殖,比土猪出栏快产仔多,很快就解决了吃肉问题。父亲作为为数不多的专业技术人员被抽调去兴凯湖学习养貂技术,国家需要出口创汇,而特色养殖尤其皮毛兽在国际上可以换汇,学习回来后在饶利河附近创办了大型国营养殖水貂厂,具体多少只我不记得,但是儿时我常常和小朋友偷偷钻进貂饲料室偷吃牛马肉,水貂很珍贵的,吃的是肉鱼玉米面混合饲料,稍有异味则不进食,而且各种添加剂维生素不能缺乏,当时人们普通口粮都是馒头咸菜,貂的口粮着实奢侈。作为新开发的垦区,国内各省过来的人很多,我记得我家曾和山东郯城人作邻居,作为技术员家庭,也曾有大量知识青年来聚会,北京上海哈尔滨等青年也有很多,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就在我们相邻的国营农场,著名农业经济学家陈锡文也是从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考到人民大学课堂上的,他的农业经济理论一直影响着国家农经制度。辽宁作为东三省首府,北大荒农垦兵团人数自然也不少,我记得锦州兽校、熊岳农专、铁岭农校的人都很多,我记得爸爸同批来的袁叔叔参军转业后很快走向了领导岗位,父亲也在我上高中时调到了场部附近养鹿连当连长,这倒极大方便了我上学,因为兵团唯一的普通高中就在场部,这样我就不用住校了。其实教育组织培育也是漫长的过程,我一直成绩十分出色,但考高中时三个班学生只有五个人考上高中,而这个高中仅仅是普通高中,高二后我转到附近县城实验高中,我明显感觉到农村的孩子比我们农场的要穷,但是文化教育积淀比我们新建垦区要好,我在县城实验高中文科班以应届生第二的名次考到省城农业大学农经专业班,等我独自去大学后才感觉到肥沃的黑土地农场一个显著缺点是交通不方便,绿皮车时代从农场到省城要先汽车到勃利县福利屯,然后坐一天一夜火车才到省城,大学毕业工作几年我考研究生就选择回老家辽宁读书。父亲当了几年养鹿连连长,在改革开放大潮下在场部办了个兽药饲料店,其实他属于先下海的一批人,96年我大学毕业在家等分配时,一次进货就用2-3万左右,而当时期北京望京附近房价也就几千块钱,父亲是搞技术的对经济学金融理财学思想是缺乏的,后来我们都知道了,北京三环以内房子十年后就接近十万一平了,在讲金融学时我常常给学生讲这个例子,学技术很有用,但是缺乏金融理财意识,你赚多少还会在不知觉中偷偷流失,现代经济信用货币通货膨胀会偷偷流失财富。
父亲退休后随着子女都回到辽宁,他也从工作一辈子的农场出来了,先是在我工作的沈阳买个房生活了几年,后来转去了姐姐工作的营口市,老家盖县山村正是归营口市管辖,恍惚间落叶真是要归根的,看着父亲逐渐衰老的身影,人这一辈子努力求学工作分配到底在追寻着什么呢?是广袤的白山黑水还是无垠的辽河平原都布满了一代代建设者的足迹,现在我们都富裕了,兵团很多人住上了二阶小楼,象西方大农庄里的独立别墅,我在省城工作生活,楼下就是地铁,附近的生鲜超市商品珠榔满目,坐着地铁我可以直接到单位和城市飞机场,便利性不言而喻,但是建设者的足迹永远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力
2025年4月28日随手草成,用手机微信对话框弄完的,大学后再不学中文了,英语考试成了进阶的重要指标,文科生且当年准备学中文的我居然很多别字,不常练习什么都在退化,文学大家讲写东西思想很重要,但写完一定要修改几遍,专业学金融的我早已对文学典故习语陌生了,草草了事有空再修改吧,送给83岁的老父亲。

第十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主题不限,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随到随审。
为期一年,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十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2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左右)
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左右)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人气奖若干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喜欢喝茶,需要购茶的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投稿问题请勿扰,按照征稿启事投稿即可。)
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芙蓉文化出版中心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微信:1075812579
萧逸帆工作室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微信:1075812579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