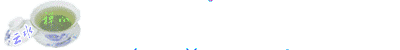雨 窗 行 记
作者:墨染青衣
青弋江的水汽混着皖南特有的梅雨气息,在列车窗玻璃上凝成蜿蜒的水痕。我坐在从芜湖开往杭州的高铁上,看窗外那些熟悉的景致——赭山上的广济寺塔、镜湖边的垂柳、以及青弋江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辆,都在雨幕中渐渐模糊成水墨画般的色块。
邻座是个约莫四十出头的男子,头顶已经呈现出地中海式秃发,却留着两撇过分浓密的胡子。他手里捧着本《养生秘典》,封面上"长寿一百二十岁不是梦"的烫金大字在车厢顶灯下闪闪发亮。
"您说,人真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吗?"他突然合上杂志,两根粗短的手指敲击着封面上的数字。我注意到他的指甲修剪得过分整齐,边缘泛着不健康的青白色。
我望着他衬衫第三颗纽扣处可疑的油渍,想起离家前父亲塞给我的那罐六安瓜片。"我父亲今年八十二了,"我说,"他总说活得久不如活得好。"上周日回家吃饭时,老爷子还在院子里给他的兰花分株,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稳得像年轻时的钳工。
男子怔了怔,浓眉下的眼睛突然变得警觉。他迅速翻开杂志,哗啦啦的纸张翻动声混入车厢广播:"下一站,宣城...…"
窗外,水阳江的支流在雨中泛着银光。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突然出现在月台上,将脸贴在列车窗户上,鼻尖压成扁平的粉白色。我们的目光在双层玻璃间短暂相接,她朝我做鬼脸的瞬间,列车又缓缓启动,将那张鲜活的小脸拉成模糊的色块。
雨势渐大时,我在笔记本上画起速写。线条不知不觉勾勒出芜湖老家的模样——中江塔下蜿蜒的青石板路,雨中的老浮桥,还有父亲常去听评书的鸠兹茶馆。记得小时候,每到梅雨季,父亲就会带我去江边看水,他的大手里总是攥着把旧黑伞,伞骨上缠着电工胶布。
"您去哪儿?"秃顶男子突然又开口,打断了我的回忆。
"杭州。"我简短地回答。
"旅游?"
"算是吧,也去看看父亲的老战友。"我补充道。父亲年轻时在杭州当过兵,至今还保留着和战友们在六和塔下的合影,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1976年仲夏"。
男子点点头,又埋头于他的养生秘笈去了。我注意到他在"五行养生法"那页折了角,旁边还画了几个潦草的星号。窗外,雨中的江南丘陵像被水洗过的青瓷,泛着温润的光泽。
杭州的雨比芜湖更缠绵些,落在从父亲战友那里借来的黑伞上,发出闷闷的响声。我站在湖滨路的人行道上,看雨水在青石板缝隙间汇成细流,倒映出模糊的霓虹光影。雷峰塔在雨雾中若隐若现,与芜湖的中江塔竟有几分神似。
"要藕粉吗?现熬的。"声音来自巷口一个蓝布棚子,老妇人围裙上沾着白色粉屑。她搅动铁锅的动作让我想起芜湖老家的邻居汪奶奶,每年冬至都会熬藕粉分给街坊。
小凳上的搪瓷碗里,藕粉渐渐凝固成半透明的胶状,点缀着桂花与山楂碎。"四十年啦,我在这湖边。"她突然说,树皮般的手背上有块形如巢湖的老年斑,"见过日本人举着刀跑过去,也见过红卫兵砸菩萨像。"
勺尖划过藕粉表面,留下转瞬即逝的纹路。"现在这些举自拍杆的,和当年举火把的,眼神其实差不多。"她笑起来时,露出三颗倔强的黄牙。我注意到她耳垂上小小的金环,在雨幕中闪着微光,让我想起汪奶奶那对从不离身的银耳坠。
沿着白堤行走时,雨势渐歇。垂柳的枝条低垂至水面,宛如女子浣洗的长发。远处一艘摇橹船划过,船头穿蓑衣的船夫突然唱起小调,让我想起青弋江上的摆渡人。我在"平湖秋月"的碑亭下避雨时,遇见个画水彩的少女,她的调色盘里盛着整个西湖的灰色调。
"您挡住我的构图了。"她突然抬头,睫毛上沾着细小的水珠。我挪开半步,看见她画纸上洇开的一抹黛蓝正缓缓吞噬断桥的轮廓。"雨中的桥才真实,"她用笔杆指点,"就像芜湖的老浮桥,晴天那些都是明信片上的假象。"
傍晚时分,我在孤山路的一家茶室歇脚。老板听说我来自芜湖,特意取出珍藏的太平猴魁。"你们安徽的茶,"他推来一只天青色的品茗杯,"配西湖的雨水,别有一番风味。"
茶汤入口的刹那,窗外突然划过一道闪电,将西湖照得通明。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父亲年轻时的身影——1976年的那个士兵,是否也曾站在这样的雨中西湖边?老板正在讲述苏东坡疏浚西湖的往事,他的声音与雷声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知道为什么江南的故事特别多吗?"他忽然问道,手中的茶壶停在半空,"因为这里的水汽养人,也养故事,就像你们芜湖的镜湖,不也出过那么多文人墨客?"
去龙井村的盘山公路上,出租车司机听说我来自芜湖,立刻用蹩脚的安徽话说:"你们那儿的虾籽面好吃!"车子碾过一段被山洪冲毁的路面时,窗外掠过成排的茶树,在雨水中绿得发黑,让我想起芜湖县六郎镇的农田。
胡公庙前的十八棵御茶树比想象中矮小。守园的老陈正在檐下烧水,用的竟是一把芜湖铁画工艺的铜壶。"尝尝?"他推来一只缺口茶杯,"别信那些故事,乾隆爷根本没来过这儿。"
茶水入喉的刹那,山雨突然转急。老陈从木箱里取出本泛黄的相册,指给我看1983年大雪压垮茶棚的照片。"那年的龙井喝起来有松针味,"他缺了无名指的右手摩挲着照片,"就像你们皖南的野茶。"
他带我去看他家的炒茶间,铁锅已经被炭火熏得漆黑。"杀青要掌握火候,"老陈布满茧子的手掌在锅里翻动嫩芽,"就像你们芜湖的瓜子,炒轻了不香,炒过了发苦。"我注意到墙角堆着崭新的电炒茶机,包装膜还没撕干净。"儿子买的,"他顺着我的目光解释,"说我这手艺该进博物馆了。"
茶香渐渐充盈房间时,老陈突然问:"知道为什么老茶客要喝'明前茶'?"不等我回答,他自问自答道:"因为清明前的茶叶,经历过整个冬天的生死,就像你们皖南的老茶树。"窗外,晨雾中的茶树泛着冷光,让我想起去年在芜湖峨山顶见过的野茶。
"三十年前这场霜冻,"老陈指着西边坡地上几株明显矮小的老茶树,"冻死了大半茶园。活下来的这些,根扎得比房子还深。"他摩挲着茶桌边缘的裂痕,那里嵌着半片生锈的采茶刀,"就像你们芜湖的老字号,能留下来的都有真本事。"
正午时分,我在村口遇见收购茶商。他听说我来自芜湖,立刻夸起芜湖绿茶。"不过现在市场喜欢龙井的口感,"他向我展示APP上的品质曲线图,"大数据说今年消费者喜欢偏甜的味道。"他身后卡车上,"传统工艺"四个喷漆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让我想起芜湖老字号"同庆楼"的金字招牌。
下山时我迷了路,误入一片野茶林。突然出现的采茶女背着竹篓,篓底还沾着新鲜泥土。"跟着走。"她简短地说。我们穿过被野藤缠绕的废弃茶厂时,她指给我看墙上的标语——"战天斗地"四个字已被苔藓吃掉半边,就像芜湖老厂区那些褪色的标语。
去灵隐寺的山路石阶被雨水浸成深褐色,让我想起芜湖赭山的登山步道。检票处的年轻和尚正在智能手机上玩消消乐,屏幕彩光映在他灰色的僧袍上,有种奇特的违和感。
大雄宝殿前的香炉里,几支电子莲花灯闪烁着红光。我跪在蒲团上时,想起父亲常去的广济寺,那里的香火总是缭绕着真实的烟雾。殿角的老僧敲击木鱼,节奏竟与芜湖街头卖麦芽糖老人的梆子声莫名相似。
"施主看这个。"知客僧突然递来一片银杏叶,"金佛要贴金箔,虫子却只吃真叶子。"他的僧鞋边缘沾着星巴克咖啡渍,却让我想起芜湖二街早点摊的豆浆痕迹。
子夜的灵隐寺比白日更为神秘。年轻僧人释空正在用平板电脑播放《大悲咒》,屏幕蓝光映着他眉间的戒疤。"施主也睡不着?"他关掉佛学论坛页面,"现代人的通病。"殿角铜钟突然自鸣,他解释说这是装了智能感应装置,"比人工敲击节省0.7秒。"
我们坐在千年银杏树下,他掏出手机给我看昨日拍的"佛光"。"师父说这是着相,"他笑着切换成计算器,"就像你们芜湖的傻子瓜子,包装再花哨,不如原味实在。"
话题转到电子莲花灯时,释空突然严肃起来:"你觉得用充电宝供电的佛灯,佛祖还认不认?"这让我想起父亲常说的:"去庙里烧香,心诚则灵,不在乎香火多少钱。"
破晓前,他带我去看刚修复的摩崖石刻。施工队的激光雕刻机正在作业,"慈悲"二字逐渐清晰。"旧佛像被砸掉时,"他指着地上的碎石,"有人偷偷把碎块埋在后山——就像你们芜湖的老城墙砖,现在都散落在老百姓家里。"
返程的高铁上,我翻开笔记本。茶山老陈送的几片鲜叶夹在纸页间,已悄然氧化。窗外,江南的田野掠过一道道色带,让我想起芜湖到杭州这一路的风景变化。
手机震动,父亲发来消息:"兰花要开了,你妈说等你回来浇水。"照片里那盆建兰确实冒出了花苞,在父亲粗糙的手掌衬托下显得格外娇嫩。我突然想起灵隐寺释空的话:"所谓顿悟,不过是终于看清早就存在的东西。"
列车驶入芜湖站时,那个秃顶男人竟出现在月台上。我们擦肩而过时,他塞给我一个U盘:"里面是佛经电子版。"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光,"现代人要有现代人的修行方式。"这让我想起父亲常说的:"做人做事,贵在坚持。"
出站口的电子屏显示着实时天气。我深吸一口气,闻到了熟悉的青弋江水汽。背包里,老陈包给我的那捧山土正轻轻摩擦着内壁——他说这土最适合种兰花。
回到家时,父亲正在阳台上修剪兰叶。窗台上的那盆建兰确实要开了,紫色花苞上还沾着水珠。"怎么样?"他没问旅途见闻,只是递来一杯六安瓜片,"西湖的雨和芜湖的有何不同?"
我望着杯中舒展的茶叶,突然明白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为了以更清澈的目光回望故乡。那些雨中的西湖、茶山的晨雾、寺庙的钟声,最终都化作了浇灌日常生活的甘露。阳台上,父亲种的兰花正静静等待着绽放的时刻,就像这座江城里,那些我习以为常却从未真正留意过的美好。
【作者简介】
张龙才,笔名淡墨留痕、墨染青衣,安徽芜湖人,爱好文学,书法,喜欢过简单的生活,因为 简简单单才是真,平平淡淡才是福。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追求了过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懂得知足的人,即使粗茶淡饭,也能够尝出人生的美味!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