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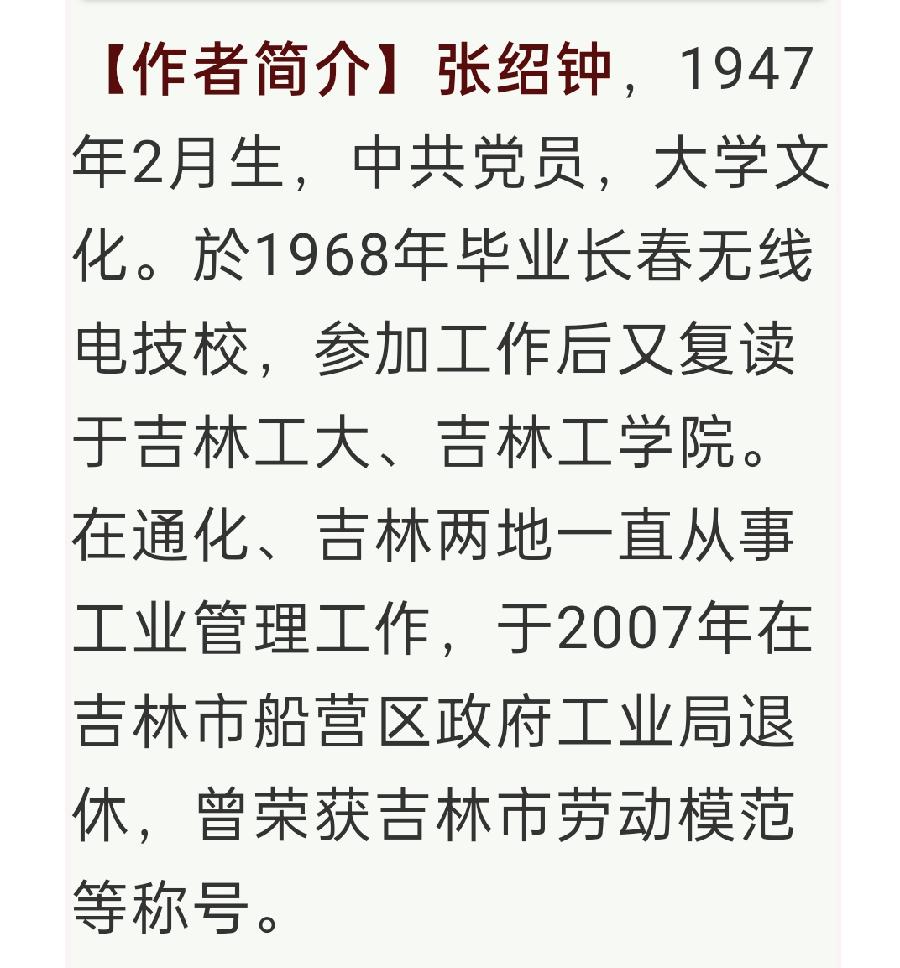
与文为友,逐光而行
张绍钟
我常自谓“文化爱好者”,这称谓无甚光环,却藏着我对文字最赤诚的向往。总觉得散文如春日里的溪流,澄澈间能映见生活的细碎微光;诗词似秋日檐角的风铃,轻响中便漾开千年的心事。这份喜爱,让我格外珍视与文化界友人相处的时光,他们是引我叩开文学之门的灯,也是我在笔墨世界里的同行者。
记得初与他们论及散文,我总局促地捧着自己的草稿,字句间满是生涩的堆砌。一位前辈却笑着接过,不评优劣,只指着文中“晨雾漫过石阶”的句子说:“你瞧,雾是软的,石阶是凉的,若再添一点触感,比如‘指尖触到石阶时,雾气便沾了满手湿凉’,是不是就把读者拉进这晨景里了?”这话如醍醐灌顶,我才懂散文的“真”,从不是辞藻的叠加,而是把自己放进场景里,让情感顺着文字自然流淌。后来我试着写故乡的老柳树,不再只说“树很高大”,而是记下“夏风穿过枝叶时,光影在青石板上跳着,我与好朋友在老柳树下畅谈,竟也得了好朋友一句“有生活的温度”。
谈及诗词,更是让我常感“仰之弥高”。曾和一位老师聊起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我只道“读着觉着凉”,老师却引我细品:“‘兼’字多妙啊,不是雨打梧桐,是细雨裹着梧桐的萧瑟,再配上‘到黄昏、点点滴滴’,把孤独拆成了一分一秒的熬,这才是易安的愁。”那之后,我不再只背诗词的平仄,而是试着走进字句背后的情境——读杜甫“感时花溅泪”,便想他站在残破的长安城里,见春花却思家国,泪落的哪是花,是乱世里的无奈;读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便品他在雨巷里的豁达,竹杖虽简,却比鞍马更自在。友人见我这般琢磨,也常赠我旧诗集,扉页上题着“读诗如见人,见人如见己”,这话我至今藏在书里。
如今想来,我对散文诗词的学习,从不是单向的索取,而是与友人们的“以文会友”。他们不疾不徐地引我看文字里的风景,教我用心灵去感知,而非用技巧去拼凑。我仍常写常改,也常因一句没写好的话蹙眉,因一句读懂的诗雀跃,但这份热爱,早已在与他们的交流里,成了我生活里的一束光,不耀眼,却足够温暖,让我愿意一直追着这光,在文化的长路上,慢慢走,细细品。
煞尾张绍钟赋七律致谢诸友与我陪伴:
幸得群英伴我行,风霜几度总相倾。
谋篇每赖高贤助,举步常承挚友撑。
谊若清弦弹岁月,情如朗月照征程。
今朝把酒铭心处,且以丹心报厚诚。
与部分朋友相聚
绍钟对朋友代表性的感言
我经常与各行的朋友相聚,感慨万千,岁月静好,友谊常在。岁月匆匆,真情永恒。感谢朋友相聚,让我感到无比的满足。
朋友相聚,是一种幸福,让我们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受快乐与温暖。
朋友们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和经历。
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笑声、美食和无尽的欢乐,这才是人生最棒的时刻。
人生最l美好的瞬间就是能与朋友们在一起,互相倾诉心声,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感恩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