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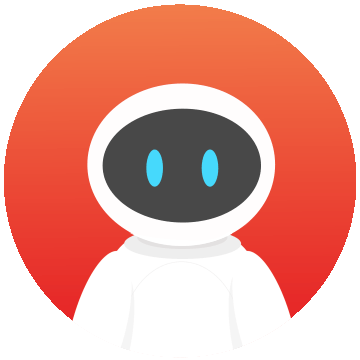
AI小壹
齐鲁晚报智能报料小助手
老土|会飞的村庄(散文)
简刊
10:11


无论在城市的高楼里居住多久,都是一种漂泊。一种流浪与客居的不安稳,会时时在心底浮生起来。也常常会在某个深夜,另一个自己就不由自主地,飘回到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村庄。 太阳还是那个太阳,而夏日已改名秋阳。
一场秋雨和白露,把北方的夜晚,染上了一抹沉甸甸的凉意。此时,是适合去乡下看看的,就像眼前这个叫解庄的村子。尽管她并不是我的故乡。但一定有另外一些人,把她唤作家乡。
无数人的概念里,故乡总是与村庄相连。把别人的故乡,暂且视作自己曾经的村庄,何尝不是对灵魂的别样抚慰。
从县城出发,开车去解庄,十几分钟。而说解庄村离县城很近,并不十分准确。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和解庄一样的许多村庄,像一个个性格怯懦的孩子,委屈地蜷缩在城市的边缘,却又倔强地守护着村庄的原有风貌,和作为村庄的那一丝尊严。她歪着脑袋,执拗地告诉每一个来这里的人,我是村庄。
站在村庄的街口,便可望见不远处工业园区的厂房。城与村,此时在眼前变得模糊起来。不断向外扩展的城市,就是对村庄的吞噬。用“吞噬”这个词,似乎是在讽刺。其实也并非如此,和乡村振兴一样,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两者并不矛盾。吞噬,说明胃口大,胃口大,才能身体壮,才能有力量。
在将来的某一日,解庄就会变成现在人们常说的“城中村”,且面临着观念、价值、生存与习俗的多重改造,这似乎是肉眼可见的。 多去村庄看看,显得很重要。用文字或其它方式,记录一下即将逝去的村庄,则显得尤为重要。城市与乡村,必将在不断求变的过程中,相互融合。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必然会飞生起思想灵动的翅膀。这对翅膀,一边是城市,一边是乡村。而这对并不对称翅膀,但愿不会让我们偏离了航向。
村庄的那种倔强与韧性,是刻在骨子里的,这还体现在一幅巨大的墙体画上。解庄村的街道两旁的村民房屋墙上,用各种彩绘与文化标语装点着这个村子。其中一幅,是火遍全国的“哪吒2”,哪吒脚踩风火轮,手持长枪,身背圆环,形态可掬,旁边大字写着“我命由我不由天”。
吸引我来到解庄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幅“哪吒2”。确切地说,解庄村是因为“哪吒2”电影火了之后,有人突发奇想,请人把电影中哪吒的形象画在墙上,并通过互联网,把解庄变成了网红村,很短时间内,让天下人知道了东阿有一个解庄。这种“借力使力”的玩法,很奏效,解庄村在全网飞翔,也成了无数人的打卡地。
刷手机不是什么好习惯,甚至有人把手机视为精神毒品。可刷手机看视频,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外面的世界,也包括这个村庄被无数人点赞与打卡。哪吒,作为中国民间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可以成就一部电影,自然也可以成就一个村庄。这个爆点,被解庄人敏锐地捕捉并点燃——解庄出圈了。同时出圈的,还有这个村80末出生的支部书记解鸿飞。
关掉手机之后,人们是否会安静下来想一想,表面看这是一次巧合,而里面是不是还隐藏着一些深层次的必然。为什么是解庄,而不是别的村庄?一定是神话中哪吒的某些特质,在现实中与解庄人骨子流淌的基因,实现了某种暗合。墙面上只是彩绘与标语,实际上也是解庄人在行动上的一种映照。努力利用现代互联网,与时代的节奏保持同频,同时又要让村庄更像个村庄。两种看不见的力量,在这个叫作解庄的村子里暗自较劲儿。
三十多岁的解鸿飞,军人出身,回乡创业后,用自己的企业反哺家乡,同时还把村支书的担子扛在了肩上。未来,注定是青年人的,尤其是那些有胆识有魄力的青年。年轻人,有韧性,任由几股力量在他们的身体里较劲,表情里却永远是风轻云淡。这大概就是对“我命由我不由天”诠释吧。
走一走转一转,我努力在解庄村的街巷,找寻自己心中村庄的影子。作为网红打卡地,除去前面看到的,它整体看上去更整洁,一面面红旗插在街道两侧各家各户大门口的上方外,我看不出它与别的村庄有何不同。秋阳里,一些老年人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聊天儿,或者在大门过道下喝茶、打牌。打牌,也打发着各自为时不多的岁月。
而他们的孩子,那些年轻人,都在周边的企业里工作,成了拥有农民与工人双重身份的人。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就回到农村的家里。农忙时节,他们会及时转换角色,走进土地与庄稼。
人们对土地的依恋,是生在骨子里的。曾经的农民,如今虽无法仅仅依靠土地,过上更富足的生活,却也无忧无虑,悠闲自在。就像那些依然生活在解庄里的老人,他们曾经的梦想,早已被现实磨平,如今,他们却能够满足于一缕阳光,和一缕秋风。
四十多年前,从云南金沙江畔远嫁到解庄村的那西族姑娘,如今已经76岁,竟然没有回过一次娘家,思念之情,可想而知。今年,村委帮她订了机票,并亲自陪同她和老伴飞去了云南。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踏上故土,见到了几十年不见的娘家人,那情景,不知让多少人为之泪目。
老人眼里的泪光,和隐藏在她皱纹里的笑意告诉我,她很知足,很满意,这是她今生唯一的愿望。秋阳下的院子里,枣树结满了红枣,随手摘下一颗,又脆又甜。脚下的菜园里,挂在秧上的几只茄子,正泛着嫩嫩的紫光。韭菜花开了,星星点点,一缕清香让人在口齿间生出津液来。
在中国人的灵魂里,永远驻着情怀二字。梦想如果是一棵树,树上的果子最终会有一个名字,它叫情怀。小情怀是家,大情怀是国。家国情怀,不是空泛的一句口号,它需要飞起来,而更多的时候是落地。落在家里,落在村庄,落在乡间的小路,和一片片庄稼。最终,它会落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
支撑乡村走得更远,当然不能依赖于某一个人。而我也相信,总有人在做,也总有人会跟着继续做。将来的解庄,变得不再是现在的模样,而人却终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一代一代,生生不息。就像许学森,一位出生在解庄村的,国家月球和深空探测的90后科学家,他成了解庄村的骄傲,东阿的骄傲。他的父亲不善言语,只是一脸无奈,孩子成了国家的人,回不来呀。
科学家在父亲的心里,依然是个孩子。孩子的梦想一直在月亮之上,在更深远的太空。而他的心里,应该会装着这个解庄,因为村子里装着他的童年与少年,也装着他曾经的梦想。这里,是他梦想起飞的地方。
永远不要小瞧一个村庄,多少人的人生,都是从这里起飞的。也由此,让人理解了那些生活在村里的老人,那么容易就知足了,就幸福了。因为他们从自己孩子的身上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村庄以外更深远的世界。
解庄的解,还是理解的解,解释的解,解放的解。今天,我在努力用自己的文字,探寻一个村庄的密码,可是,我发现自己很无力。只能用文字轻声地告诉大家,请对我们的村庄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善待村庄,善待我们的村里人。
那天,我站在解庄的街口,抬头望向深蓝的天空,几片碎碎的云朵也离得我们那么远,那么高。而有七八只燕子,站在四五根横在空中的电线上,啾啾地呢喃着,并回头用喙梳理着羽毛,伸展着翅膀,像极了几个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秋天到了,燕子们就要飞向南方,要等到明年开春,它们才能再回来呢。此时,它们是在用一场音乐和舞蹈,演绎一场告别,并要开启一次遥远的飞行。就像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探亲的假期满了,他们也要走了。
解庄的解,还是解开的解。敞开胸怀,袒露胸襟,无论未来的村庄是怎样的命运,都需要我们张开双臂,勇敢地去拥抱,去面对。
壹点号 简刊
特别声明:本文为“壹点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个人观点。齐鲁壹点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