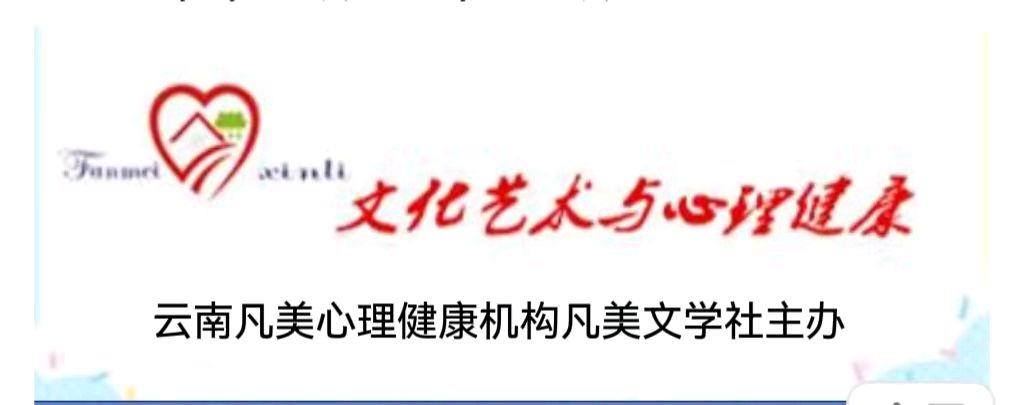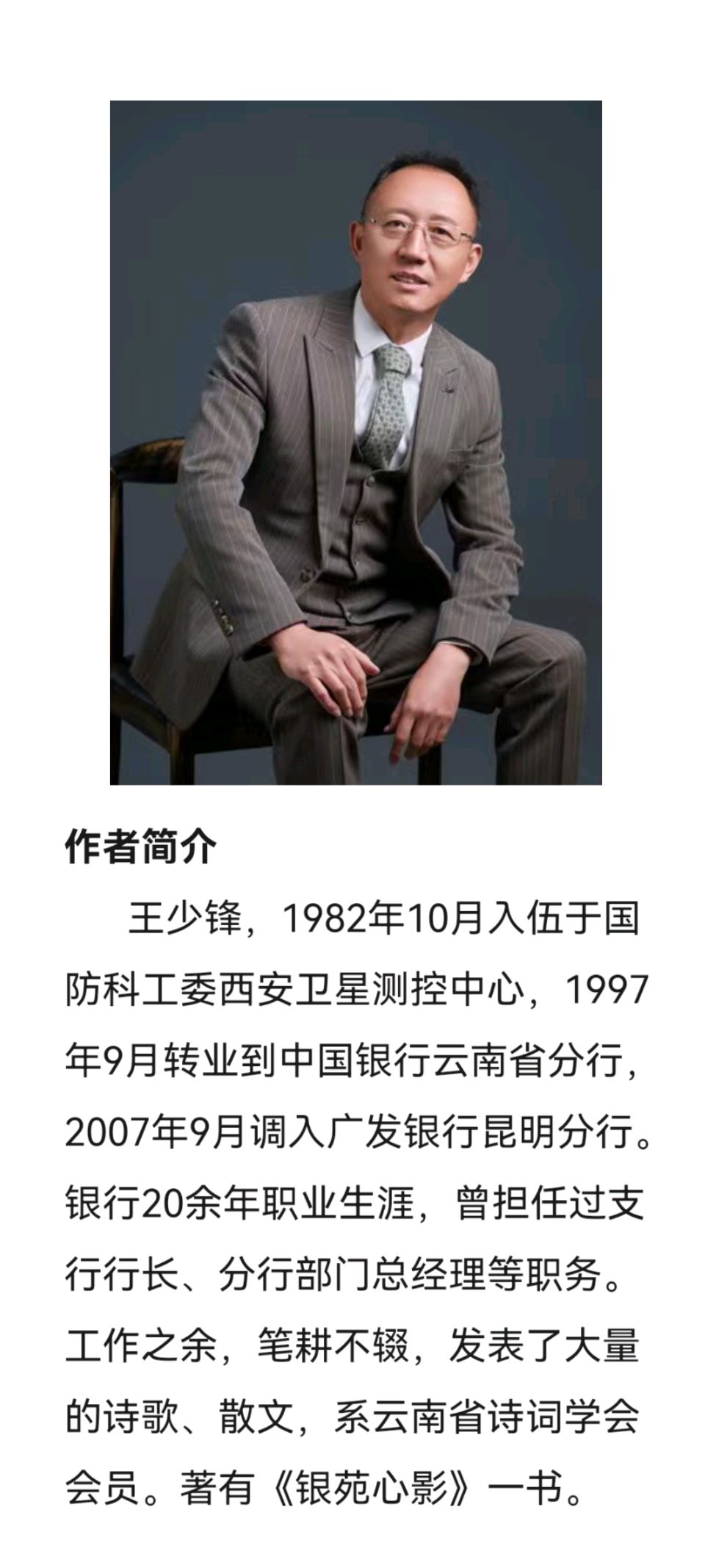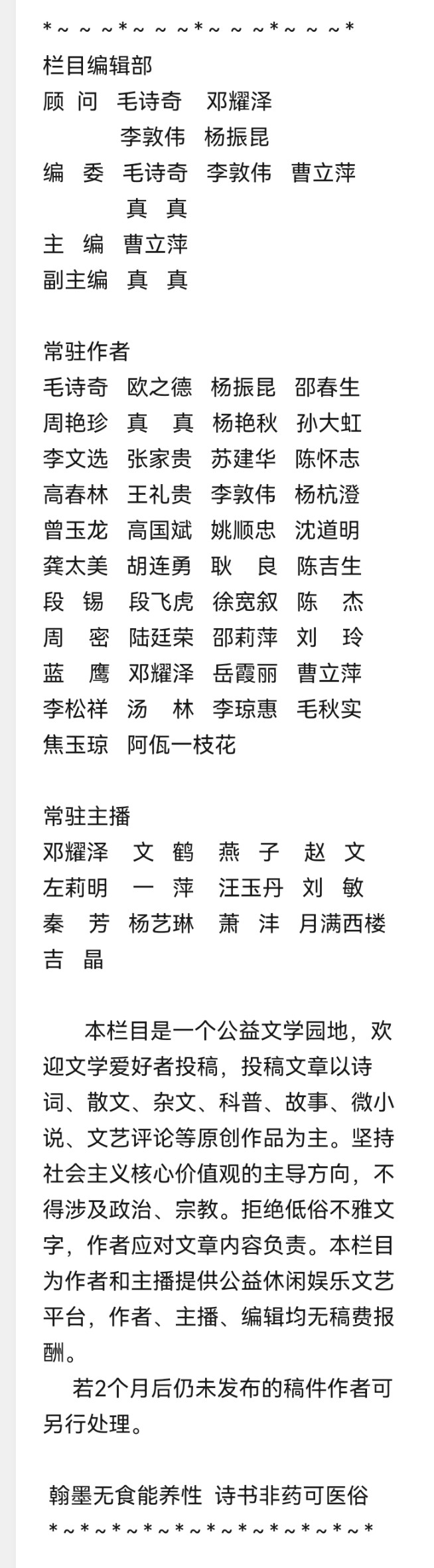滇东南之行
夜宿普者黑
屈指算起来,这是我第4次来丘北普者黑旅游了。第一次是二十年前的2002年的清明节前,当时我还在中国银行工作,全行优化网点布局,我随省分行工作组去撤销麻栗坡中行。任务完成之后,为放松撤销期间紧张的工作状态,工作组一行6人专程开车来普者黑休闲放松。当年的普者黑还处于一种原始状态,景区开发与配套服务没有启动。一行在普者黑湖面上划划船,在船上吃老乡的烧烤,从仙人溶洞出来,由于没有民宿客栈,我们又返回丘北县城找宾馆入住。
这次来普者黑是与几位朋友约定已久,不巧的是就在我们到达普者黑前的早上,景区突然下起了普者黑近年来罕见的一场暴雨。雨后的景区,彩虹复道,秋高气爽,长空似炼,植被翠绿欲滴,沿街青石板一尘不染。遗憾的是,供电设备因水淹浸泡出现了故障,直到当晚九点后才恢复通电。夜晚时分,夜暮笼罩下的普者黑四周黑黝黝的,只有天上的星星在闪烁,此时暮色像一块浸了墨的棉麻布料,慢悠悠地裹住了普者黑的山与水。
入住的民宿的老板是本地人,由于停电,黑灯瞎火的什么事也干不成,于是给我聊了起来。话匣子一打开,就把普者黑的过去与现在都倒了出来。“二十年前哪有什么景区,”他指着窗外的荷塘,“这一片全是稻田,我们靠养鱼、种玉米过日子,路都是泥巴路,下雨天出门能陷到膝盖。”他说,那时候的普者黑,是藏在滇东南的“土疙瘩”,只有山民知道这里的溶洞有多奇,湖水有多清,却没想过能变成今天的模样。我想所谓沧海桑田,就是对普者黑的真实写照。
聊了一会,我信步走到阶下门前空阔处,抬望满天星斗,银河清晰得像有人用银线织过。不远处的青龙山黑黢黢地立着。老板跟着走过来说,以前夜里的普者黑,除了虫鸣就是狗吠,现在虽热闹,却也没丢了本真——那些溶洞还是老样子,青龙山的石阶还是当年山民凿的,连湖里的鱼,都还是用老法子养的。
九点以后来电了,周边亮成一片,灯光洒向湖面,反射出一道道波光。我于是便沿着湖边独自散步,荷塘边的木栈道上,偶尔能碰到三三两两的游客,拿着手机拍远处的孤山与头顶上的星星。此时,我想起第二次来普者黑,坐柳叶舟时的情景,撑船的师傅戴着斗笠,竹篙一点,船就滑进了荷塘深处,荷叶擦着船舷沙沙响,偶尔有粉色的荷花从叶间探出来,美得让人屏住呼吸。师傅说,这些船是照着老样式做的,以前是用来捕鱼、运粮的,现在成了游客体验的“宝贝”。
沿着湖边往前走,又想起前年来普者黑的白天进入溶洞的情景。钟乳石在灯光下五彩斑斓,水滴从石笋上落下来,“嘀嗒”声在洞里回响,像时光的脚步声。导游说,这些溶洞早在几百年前就被山民发现了,他们曾在洞里躲避战乱,还留下了一些石刻。现在,溶洞里修了安全的栈道,却没破坏一点自然景观,游客能顺着当年山民的足迹,感受岁月的痕迹。
回到民宿时,老板还坐在茶台边喝茶。他指着天上的月亮说:“你看,不管普者黑怎么变,这山、这水、这月亮,还是老样子。”我望着远处的青龙山,望着湖里的月影,忽然明白,普者黑的美,不仅在于它的湖光山色、溶洞奇景,更在于它的“变”与“不变”——变的是越来越方便的交通、越来越完善的设施,不变的是山民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还有这片土地独有的宁静与诗意。
夜深了,荷塘里的虫鸣更清晰了,伴着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像一首温柔的摇篮曲。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水声,感觉自己仿佛融进了这片土地,融进了普者黑的过去与现在。
我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沿着景区小巷的青山板来回穿梭,来到湖边,太阳从湖中孤山后面冉冉升起,远方孤山倒影与一望无际的荷花莲叶融合在一起,普者黑绿水青山怀抱之中刚刚苏醒,一幅美好山水画卷迎入眼帘。我想山好、水好、风光好是普者黑的外在美,“始于山水,归于烟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感受天地之大美,才是景区的精髓之所在。也正如此,普者黑就像一颗沧海明珠,以其独特的山水魅力,吸引着天下游客,让人沉醉在十里荷花,三生三世,留恋忘返。
香坪山上的金线莲
我应朋友之邀,今年这是第二次来文山西畴香坪山了,上次是5月末,那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早上,山间寒风让人为之一颤。再次踏入这片土地,也是一个阴雨蒙蒙的早上,时隔半年,旧地重游,此时秋风瑟瑟,秋雨绵绵,感触已非往日。置身群山之中,呼吸着香坪山的雾,那是裹着草木清气的独特味道。空气里飘着松针与腐叶混合的微甜,像大地刚沏好的一壶春茶,我深深吸了一口。而藏在这雾霭笼罩下的大棚珍宝,便是那株株贴着腐殖土生长的金线莲。
香坪山村民初识它,是在山腰的种植棚里。它不同于寻常药材的挺拔,金线莲更像山间精灵,叶片呈嫩润的碧绿色,叶面上清晰的金色脉络,如绣娘用金丝细细勾勒,从叶尖蜿蜒至叶柄,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种植户说,这草“挑”得很,既要有山林间的散射光,又得保持着百分之八十的湿度,连浇水都要用山涧里的泉水,不然那金线便会失了神采。我上次来,走进大棚,悄悄采撷几株金线莲带回昆明插入家中玻璃瓶中,幻想着能像兰草一样,生根发芽蓬勃茂盛生长,想不到没过半月根子就腐烂了,这次走进大棚,再也没有非份之想了。
蹲在棚中细看,每一株金线莲都生得精致。新抽的嫩芽卷着边,像婴儿攥紧的小拳头;老叶则舒展着,叶片背面泛着淡淡的紫红。指尖轻触叶片,薄如蝉翼,却带着韧性,沾在上面的水珠滚落到松软的腐殖土中,悄无声息地滋养着根系。棚外的山风穿过竹林,沙沙作响,棚内的金线莲似也受了惊扰,叶片轻轻颤动,那金色脉络便在绿毯上“流动”起来,恍若活物。
原来香坪山的野生金线莲,多藏在常绿阔叶林的树荫下,与苔藓、蕨类为伴。走在铺满松针的山路上,偶尔能在树根处瞥见一抹青绿——那便是野生的金线莲,比棚里的更显纤弱,却也更有灵气。种植户说,为了保护野生资源,他们才学着人工培育,让这“山中黄金”既能惠及山民,又不破坏山林的平衡。
你只要留心,就会发现生活在香坪山的村民,早上日升时,手里会攥着一小把刚采的金线莲回家。叶片上还沾着山雾凝结的水珠,凑近鼻尖轻嗅,是清冽的草木香,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山脚下的农家里,主人用山泉水将金线莲煮成茶汤,汤色澄黄透亮,入口先是微苦,而后回甘绵长。窗外,晨曦正给香坪山的山脊镀上金边,远处的竹林在风中摇曳,而那株株金线莲,仍在山间的雾气里,用它的金色脉络,悄悄记录着香坪山的晨昏与四季。
在游山玩水的同时,我关注到近年来,西畴县将种植金线莲作为重点产业打造,是从香坪山村开始的。由于金线莲具有较强的药用价值,是护肝制剂的重要原料,市场需要量大,烘干后卖到福建等地,五千元左右一市斤。而西畴香坪山具有适宜金线莲的生长的天然地理环境。为鼓励村民种植金线莲,政府采取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方式,向村民提供幼苗,指导种植,公司以每市斤110元的保底价格收购,政府同时对村民自建的大棚每平方贴40元。此举,极大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村民偿到了甜头,房前屋后的庭院经济应运而生。公司+农户,再加上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各乡镇吹响了种植金线莲的号角,上百亩种植金线莲的规模效益在西畴县已经形成,农民从中得到实惠,积极性非常高。
作者 王少峰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