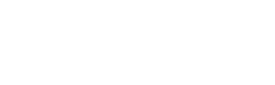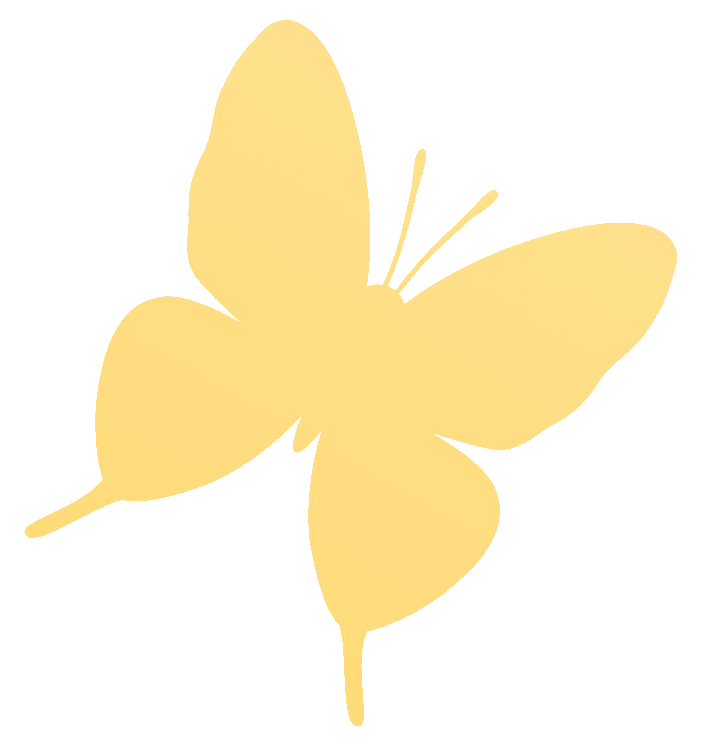想 象
文/阿尔芒
站在河岸上,一条白色的帆船
迎面开过来,船头涌起的漂亮水花
轻轻剥开平静的河流,从水波中
捞出昨晚落在蚌壳上的灿烂星光
让我的身体和思绪深陷水底
——从此,也像一条鱼一样,随便
以什么姿势在水里快乐生活
一支烟吸完了,船也走远了
我既没有下水,也不愿从想象中
出来
(载《成子湖诗刊》2025年第02期)
阿尔芒,江苏成子湖诗歌部落总策划人。出版《象脚鼓的雨季》《美术体的村寨》《转经筒的插图》等14部诗集(合集)。《淮海晚报》“木橹摇云”诗歌专栏作家,《宿迁晚报》“双面绣”诗歌版块A位嘉宾,《现代家庭报》“心意卡”特约供稿诗人,《星星诗刊》“嘉宾诗人”登展作者。长诗《乌骓之卷》(载于《诗歌月刊》)被项王故里收藏。作品入选《扬子江诗歌二十年精选》《江苏百年新诗选》《北极星文学丛书》等数十种读本。
一首诗中的禅意与存在之思
——阿尔芒《想象》赏读
文/彼尧
阿尔芒的《想象》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充满张力的精神场景。诗中,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看着白色帆船驶过,陷入沉思,最后在烟蒂熄灭时选择停留在想象之中。这简单的情节背后,却隐藏着关于现实与想象、行动与静观、瞬间与永恒的生命智慧。
诗歌开始于一个具体的时空:“站在河岸上,一条白色的帆船/迎面开过来”。河岸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点,它是此岸与彼岸的分界,是稳固与流动的交汇处。诗人选择站在河岸而非已经在水中的船上或对岸,这一姿态本身已暗示了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他不是彻底的参与者,也不是完全的旁观者,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临界点上。
白色帆船的意象纯净而富有动感,它“迎面开过来”,带着某种确定的方向性。船头涌起的漂亮水花“轻轻剥开平静的河流”,这个“剥开”的动作极为精妙,它既是对水面平静的打破,又像是对一层遮蔽物的揭开,暗示着表象之下另有奥秘。果然,随后的意象超越了日常视觉经验:水波从蚌壳上“捞出昨晚落在蚌壳上的灿烂星光”。这里,诗人将不同时空折叠在一起:昨晚的星光、此刻的水波、未来的想象,全部交汇于当下这一刻。这种时空的融合已初显禅意,禅宗强调“一念万年”,在瞬间中蕴含永恒,在当下体悟无限。
诗中主角的反应颇为特别:他的身体和思绪“深陷水底”,并渴望“像一条鱼一样,随便/以什么姿势在水里快乐生活”。水底世界象征着另一个维度的现实,它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内在的精神空间。鱼在水中的自由,恰似人在想象世界中的无拘无束。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向往的不是改变外部环境的行动,而是内在状态的转变,他想要的是像鱼一样“快乐生活”,而非一定要成为现实中的航海者。
诗歌的转折点出现在“一支烟吸完了,船也走远了”。烟是短暂易逝之物的绝佳象征,它的燃烧与熄灭暗示着时间的流逝和因缘的聚散。船走了,机会似乎已经消失,但诗人却说:“我既没有下水,也不愿从想象中/出来”。这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也是最富禅意之处。
从世俗角度看,这或许是一种错失良机的遗憾,看到了美好的事物却没有采取行动。但从禅的视角看,这恰恰体现了对“不执着”的深刻理解。禅宗不是简单地鼓励行动或放弃行动,而是超越这种二元对立。诗人没有下水,因为他明白现实中的追逐往往带来失望;但他也不愿离开想象,因为他知道精神世界的丰富同样真实可贵。
这种“既不是A,也不是非A”的状态,正是禅宗“不二法门”的体现。六祖惠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觉悟不在于逃离现实,也不在于沉溺现实,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醒的心。诗中的主角停留在岸边,正是这种中道智慧的生动写照,他接受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张力,并安住于这种张力之中。
进一步思考,这首诗还触及了行动与静观的古老命题。我们通常认为行动才有价值,静观只是行动的预备或休息。但诗中暗示,纯粹的想象本身已是一种丰富的精神行动,它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当诗人想象自己如鱼得水时,他已经在精神上体验了那种自由,这种体验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更深一层,诗中还隐含着对“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哲思。德国哲学家布洛赫曾强调“希望”和“尚未”的重要性,认为人类本质上是由面向未来的可能性所定义的。诗中的主角没有将想象付诸实践,但想象本身已拓展了他的存在维度。他保有了那个美好的可能性,而不必承受它被现实化后可能带来的失望或限制。这种对可能性的珍视,颇有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
回到禅的层面,这首诗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生命态度。船来了又走,烟点燃又熄灭,想象升起又落下,但诗人的心不执着于任何一境。他接受一切现象的生灭,却在其中保持内在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在于改变外部世界,而在于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在我们这个崇尚行动、效率和结果的时代,阿尔芒的《想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静观时刻。它提醒我们,生命的丰富不仅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还在于我们如何体验和诠释我们所遇的一切。有时候,最深刻的生活恰恰发生在行动的间隙,在那些我们允许自己只是存在、只是想象的时刻。
诗的结尾,那个人依然站在河岸上,但他的内心已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航行。他没有下水,但他已在水中;船已走远,但星光永远留在了他的世界里。这种看似矛盾的状态,恰恰是禅意最深的启示。真正的自由,是身在尘世而心游太虚,是接触万物而不为万物所染,是在有限的时空中体验无限的存在。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河岸时刻”,不急于选择,不焦虑行动,只是允许自己在现实与想象的边界上停留,感受生命本身的深沉与美妙。在那里,我们可能发现,最丰富的生命不是一味地向前航行,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刻,停留在想象的岸边。
2025·3·23于继遵道
《成子湖诗刊》2025年9月刊

举报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