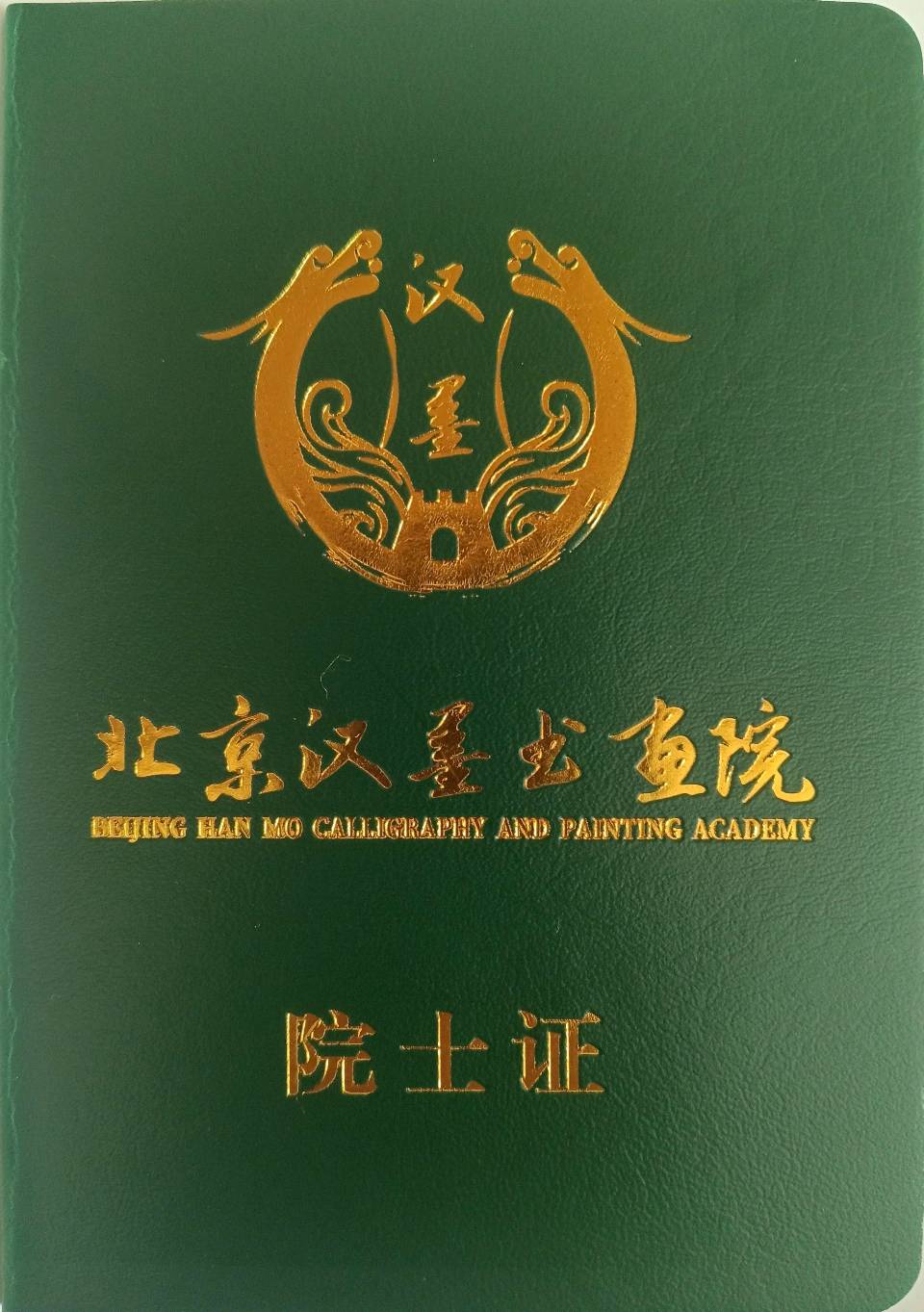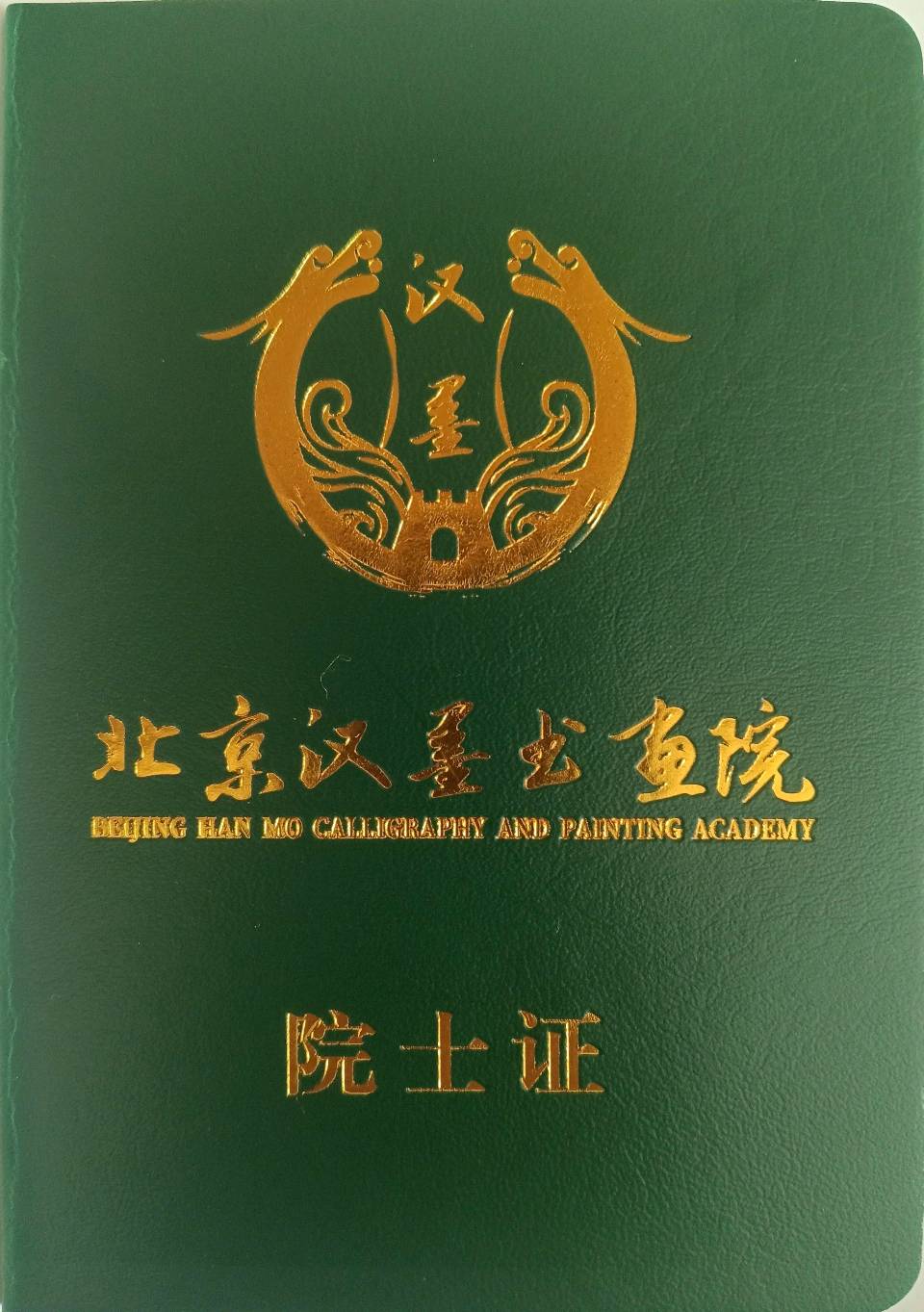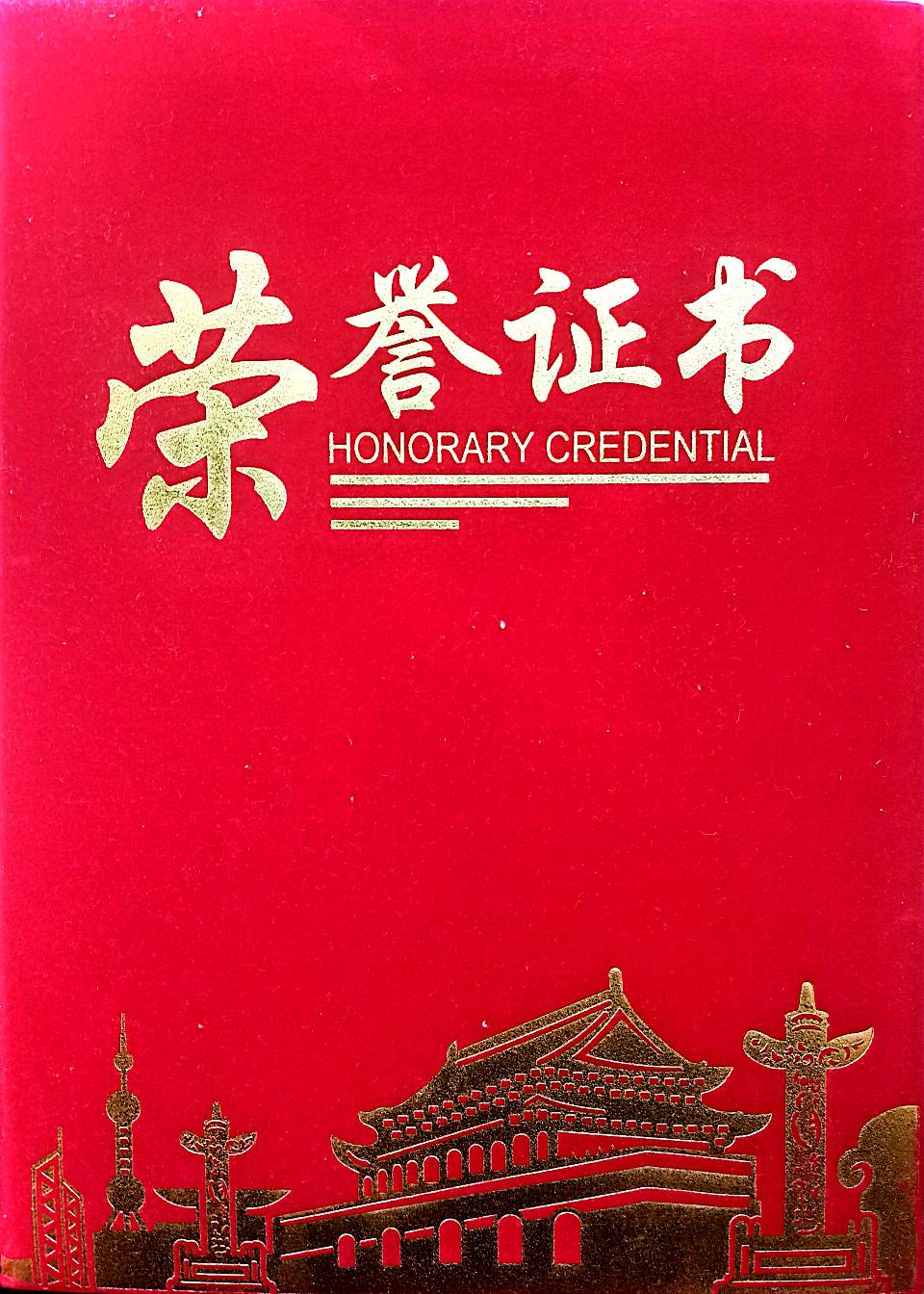第十九章:归葬
返回故乡的路,比秀兰来时更加漫长,更加沉重。
她怀里抱着那个用红布包裹的、冰冷坚硬的骨灰盒,像抱着一段被强行斩断的人生,一块无法融化的寒冰。儿子小远紧紧挨着她坐着,小手死死攥着她的衣角,仿佛一松手,母亲也会像父亲一样消失。孩子一路上异常沉默,只是睁着那双酷似建国的大眼睛,茫然地望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逐渐由城市楼房变回田野的景象。
长途汽车颠簸着,每一次晃动,都让秀兰感觉怀里的骨灰盒硌得她胸口生疼。那疼痛不是物理上的,而是源于心底最深处那个永远无法愈合的血窟窿。她不敢低头去看那块红布,仿佛只要不看,建国就只是又一次去了远方的工地,而不是化作了这盒中一把毫无生气的、轻飘飘的灰。
工友老马和其他几个人凑钱买了车票,执意要送她们母子回来。他们沉默地坐在车厢后部,像一群护送阵亡战友遗骸的、悲伤而无言的士兵。他们脸上带着风尘和愧疚,仿佛建国的死,他们也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那个装着两万块“赔偿金”的旧报纸包,此刻就在秀兰随身的编织袋最底层,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着她的灵魂。
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熟悉。熟悉的丘陵轮廓,熟悉的田间小路,熟悉的那种带着泥土和植物清香的空气。这一切,曾经是她心灵的慰藉,是她在城市感到窒息时眺望的远方。可如今,这片土地在她眼中,也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灰暗。她知道,她不是衣锦还乡,她是带着破碎的梦和冰冷的死亡归来。
车子终于摇晃着停在了镇上的小车站。秀兰抱着骨灰盒,牵着小远,脚步虚浮地走下车。老马几人默默地跟在后面,帮她拿着那个沉重的编织袋。
从镇上到村里,还有十几里崎岖的土路。他们租了一辆破旧的三轮摩托车,突突突地朝着那个名为“家”的方向驶去。越靠近村子,秀兰的心就揪得越紧。她该如何面对公公?那个刚刚失去儿子、自己又病痛缠身的老人,能承受得住这最后一击吗?
村口那棵老槐树依然伫立着,只是在这个萧索的季节里,枝叶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扭曲的枝干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个个绝望的问号。几个在村口闲聊的村民看到这行神色悲戚、带着陌生城市工友归来的人,尤其是秀兰怀里那个刺眼的红布包裹时,都停下了话头,脸上露出惊愕和了然的神情,随即便是低声的议论和叹息。
“是建国家的……”
“唉,听说在城里出事了……”
“真是造孽啊……老木这可怎么受得了……”
那些低语像风一样钻进秀兰的耳朵,让她更加无地自容。她低着头,加快了脚步,几乎是小跑着冲向那个熟悉的、低矮的院门。
院子比记忆中更加破败。篱笆歪斜,地上散落着枯叶。堂屋的门虚掩着。秀兰在门口停下脚步,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积蓄面对一切的勇气。她示意老马他们在外面稍等,然后,用颤抖的手,轻轻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堂屋里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和老年人房间里特有的暮气。老木,她的公公,正佝偻着背,坐在一张旧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杆旱烟袋,却没有点燃。他看起来比秀兰离开时更加消瘦,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眼窝如同两个枯井,里面是死寂的、没有任何光彩的浑浊。他听到开门声,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抬起头。
他的目光先是茫然地落在秀兰脸上,似乎一时没有认出这个憔悴不堪、风尘仆仆的儿媳。然后,他的视线下移,落在了她怀里那个用红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方方正正的盒子上。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老木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那个红布包裹。他脸上的肌肉开始无法控制地轻微抽搐,拿着旱烟袋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烟袋锅磕碰在椅子扶手上,发出“哒、哒、哒”的、令人心悸的声响。
他没有问“回来了?”,也没有问“建国呢?”。
他似乎已经从那不祥的红色,从秀兰那悲恸欲绝却又强行压抑的神情,从后面跟进来的、陌生而局促的工友脸上,读懂了一切。
他就那么死死地盯着,仿佛要用目光将那红布烧穿,确认里面是否真的是他不敢想象的真相。
秀兰的嘴唇哆嗦着,眼泪再次不受控制地涌出。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将怀里的骨灰盒高高举起,喉咙里发出破碎的、泣不成声的音节:
“爹……建国……建国他……他……回来了……”
最后三个字,用尽了她全部的力气,也抽干了她最后一丝支撑。
老木的身体猛地一僵。
然后,他像是被一柄无形的巨锤迎面击中,整个人向后猛地一仰,靠在藤椅背上。那张饱经风霜、布满沟壑的脸,在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变得如同脚下的土地一般灰败。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如同破风箱般艰难抽气的声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没有去看跪在地上的儿媳,也没有去看那近在咫尺的骨灰盒。他的目光越过堂屋的门,茫然地投向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投向更远处那片他守护了一辈子、如今也即将失去的田野。
一滴混浊的、滚烫的老泪,从他干涸的眼角挤了出来,沿着深刻的皱纹,蜿蜒而下,滴落在他青筋毕露、微微颤抖的手背上。
他没有发出任何哭声。
但那无声的……
悲恸,
却比任何嚎啕大哭,都更加……
震耳欲聋。
这不再是归途。
这是一场注定没有生气的……
归葬。
将青春,将希望,将一个家的顶梁柱,埋葬在这片生育他们、却又无法承载他们命运的……
土地之上。
---
(第十九章 完)
第二十章:绝地
建国的骨灰,暂时安置在了堂屋角落一张铺着白布的方桌上。前面点着一盏小小的、火光摇曳的长明灯。那一点微弱的光,在这充满死寂和悲伤的房间里,非但不能带来温暖,反而更添了几分阴森与凄凉。
秀兰强撑着料理完这一切,只觉得浑身像散了架,每一个关节都在发出呻吟。不仅仅是身体的疲惫,更是那种从灵魂深处弥漫开来的、无边无际的倦怠。小远似乎被这接二连三的变故和家里压抑的气氛吓坏了,变得异常安静,只是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后,用那双大眼睛怯生生地观察着一切。
老木自那天在堂屋里那无声的崩溃之后,就变得更加沉默。他几乎不再说话,只是整天坐在那张旧藤椅上,要么盯着建国的骨灰盒和长明灯发呆,要么就望着窗外那片土地,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随着儿子一同逝去。他咳得更厉害了,那声音撕心裂肺,常常憋得脸色青紫,让人听着揪心。秀兰熬好的中药,他有时喝,有时就任由它凉在一边。
秀兰知道,公公的心,已经死了一大半。儿子是他的命根子,是他所有的希望和寄托。如今这根顶梁柱轰然倒塌,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也走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
然而,生活并不会因为悲伤而停下它残酷的脚步。或者说,它惯于在人们最脆弱的时候,给予最沉重的一击。
就在建国“头七”那天的下午,村里那个总是趾高气扬的会计,带着两个穿着不合身西装、像是开发商手下的人,再次来到了这个被悲伤笼罩的家。
他们没有进门,就站在院子里。会计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刻意拔高、试图显得公事公办却难掩优越感的语调喊道:“老木!老木叔!在屋里吧?出来一下,征地的事情,最后再跟你确认一遍!签字的期限可就到这月底了!别给脸不要脸!”
那声音像乌鸦的聒噪,打破了小院里死水般的寂静,也像一把盐,狠狠地撒在了秀兰和公公鲜血淋漓的伤口上。
秀兰从灶间走出来,手上还沾着洗菜的冷水。她看着院子里那三个人,看着他们脸上那种混合着不耐烦和势在必得的神情,一股强烈的、带着血腥味的愤怒猛地冲上头顶。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家里刚办了丧事吗?难道没有一点起码的同情心吗?
“会计叔,家里……家里刚出了事,能不能……缓几天……”秀兰强忍着怒火和泪水,试图哀求。
“缓几天?”会计三角眼一翻,“我跟你说,秀兰,这事儿缓不了!这是上面的政策!全村就剩你们家这几户钉子户了!别以为拖着就有用!到时候强制执行,一分钱你们都拿不到!”
“可……可这地是咱家的命啊!建国他……他才刚……”秀兰的声音哽咽了,后面的话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命?哼!”会计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嗤笑一声,“命值几个钱?我说大姐,别那么死心眼儿!拿了补偿款,去哪不能活?非守着这几分破地?”
“破地?”一个沙哑、低沉、却如同受伤野兽般充满戾气的声音,从堂屋门口响起。
老木,不知何时,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倚靠在门框上。他的身体佝偻得厉害,需要用力抓着门框才能站稳。但他的眼睛,此刻却不再是空洞无神,而是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令人心悸的光芒。他那张灰败的脸上,因为极致的愤怒而泛起一种不正常的潮红。
“你说……这是破地?!”老木死死地盯着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血丝,“这地里……埋着俺爹,埋着俺爷!这地里……长出过养活建国、养活他姐、养活这一家老小的粮食!这地……是俺老张家祖祖辈辈的根!你……你们这些……这些吸人血的畜生!仗着有点权势……就要断俺们的根啊!!”
他越说越激动,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剧烈的咳嗽再次爆发,让他几乎喘不过气,但他还是用手指着那三个人,用尽最后的力气嘶吼:
“滚!你们给俺滚!!想要俺的地……除非……除非你们从俺这把老骨头上……碾过去!!把俺……和建国……一起埋在这儿!!”
那绝望而凄厉的吼声,在破败的小院里回荡,震得屋檐下的灰尘都簌簌落下。
会计和那两个开发商手下被老木这突如其来的、如同回光返照般的疯狂气势镇住了,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脸上闪过一丝恼怒和尴尬。
“老木叔,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会计色厉内荏地撂下一句,“月底!就月底!到时候别怪我们不留情面!”
说完,三人像是怕沾染上什么晦气似的,匆匆转身离开了院子。
院子里,重新恢复了寂静。只有老木压抑不住的、破碎的咳嗽声,和秀兰低低的、无助的啜泣声。
老木靠着门框,喘着粗气,那刚才支撑着他的疯狂怒气仿佛瞬间被抽空,他的身体沿着门框缓缓滑落,最终瘫坐在冰冷的门槛上。他抬起头,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望着那片在冬日阳光下显得格外荒凉的土地,两行混浊的泪水,再次无声地淌下。
前有丧子之痛,后有夺地之危。
这个家,已经被逼到了……
悬崖边缘。
脚下,是万丈深渊,看不到任何……
生机。
---
(第二十章 完)
下一章预告: 内忧外患,绝境之中,秀兰将做出怎样的抉择?是顺从命运,还是奋起反抗?那微弱的“月嫂”技能,能否成为黑暗中的一缕萤火?活下去的路,究竟在何方?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奖。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