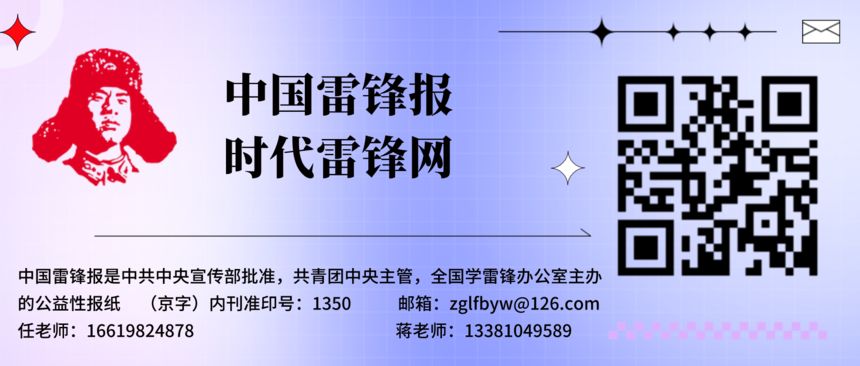【作者简介: 燕语信,亳州市文明办四级调研员,亳州市第八批、第九批选派干部,现任涡阳县标里镇李大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多年扎根乡村一线,以脚步丈量民情,用文字记录变迁,将驻村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村民的质朴与期盼,凝练成一篇篇饱含温度的驻村手记,成为乡村振兴实践中鲜活的“基层注脚”。】
刚到黄庄驻村那年,秋阳把玉米秸晒得发烫,空气里飘着芝麻的焦甜香。村部台账本上,“汪萌香”三个字旁的墨渍还没干透,备注写得明明白白:父亲患尿毒症,母亲智力残疾三级,已办理孤儿救助,在涡阳城东中心校读八年级,村东头三间平房院角,那口压水井锈得厉害,却还在稳稳往外冒水。窗台上几盆绿萝顺着瓷盆边往下垂,绿秧子蹭着台账纸,给满是文字的屋子添了点活气——只是每次翻到这页,我总忍不住摩挲纸边,想起接下来三个月里,为这孩子跑遍的部门、拨通的电话,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
一、灶火画稿:藏在纸箱里的期盼
汪萌香蹲在灶洞前,借着火苗的光在纸箱皮上画。铅笔头磨得只剩一小截,却一笔一划勾着院角的压水井——井身画得歪歪扭扭,井绳上的结倒用重笔描了又描,旁边小人咧嘴笑着,手里端着碗冒热气的药。听见脚步声,她慌忙用秫秸盖住画纸,校服肘部的毛边蹭过地面,作业本上的红叉像枯树枝似的横在分数栏。里屋药罐突然“咕嘟”冒起了泡,她猛地站起来:“俺爸的药熬好了!”
第一次见她这样慌慌张张,是在2023年8月初。我和邵比比踩着田埂去她家,刚到院口就看见满院杂物,她蹲在井边洗校服,水溅得裤脚全湿,却没舍得把画着压水井的纸箱皮挪开。“孩子,想不想接着读书?”邵比比蹲下来跟她聊,从庄稼收成说到外面的世界,近一个小时里,她只偶尔点头或摇头,始终没开口说一句话。回去的路上,邵比比叹着气:“这孩子心里的结,得慢慢解。”
那天起,我开始往城东中心校跑,找她的班主任王永前老师。第一次微信聊起汪萌香,王老师的消息带着无奈:“燕书记,这孩子成绩不太理想,生活学习都没目标,我试着激过她学习的念头,可真不敢保证她能坚持。”我盯着屏幕回复:“成绩差不要紧,先让她愿意抬头说话。你看她总蓬头垢面,家里也乱糟糟,能不能先从个人卫生教起?”后来王老师说,学校里劝了无数次,甚至请心理老师跟她谈,可她还是不开口,有次急得老师忍不住说“神仙难救该死的鬼”——我知道,这话里藏的不是放弃,是急着帮她却没辙的心疼。
日子就像这灶火旁的纸箱皮,糙是糙了点,却藏着细碎的盼头。她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喂鸡,放学先给爸熬药,忙完所有活,才能凑着灶火的微光在纸箱皮上画。画里的压水井总在出水,画里的小人总在笑,好像这样,现实里的苦就能少一点。同村的施素云路过院门口,总忍不住多望两眼——那时我们已经商量好,让她帮忙管着后续筹集的善款,专门给汪萌香办张银行卡,每笔支出都记台账,可孩子连学都没说愿意上,这张卡暂时还没交到施素云手里。
二、井台微光:照亮前行的暖意
9月初的天还透着热,抗旱队的皮管刚盘进汪萌香家院子,就撞见她把月考卷撕得粉碎——59分的墨迹溅在压水井旁的水洼里,慢慢晕开。“这可不行……”她爸支着浮肿的腿想下炕,被我按住:“您别操心,我们来劝。”其实那天早上,我刚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守雨汇报完帮扶计划:物质上筹善款、找村干部代管银行卡,精神上联系亳州雷锋车队、亳州市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涡阳县爱心者协会搞“多对一”结对,心理疏导和学习辅导也都找好了志愿者。张部长在电话里说“全力支持”,可眼下这孩子把试卷撕了,我心里又沉了沉。
傍晚,村部门口多了只塑料桶,桶里鲫鱼尾巴甩着水珠,桶底压着张歪扭的纸条:“谢谢叔叔们帮俺家浇地,鱼是俺爸让俺捞的。”我捏着纸条往她家走,远远看见邵比比蹲在槐树下,正跟她比划着什么——后来才知道,邵比比是在说自己种花生的事,说机械化播种多省力,说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就像他种的300亩花生,只要肯下劲,总会有收成。
没过几天,涡阳县副县长王亚彬(挂职)特意跟着驻村工作队去看她。王县长没说大道理,就坐在炕沿上跟她聊家常,说自己小时候也吃过苦,说生活里的难都是暂时的,只要愿意学,会有好多人帮她。十多分钟里,汪萌香还是没说话,只偶尔点头,可我注意到,她攥着衣角的手,慢慢松开了些。王县长走前跟我说:“这孩子心里有数,再给她点时间,咱们多找条路试试。”
就是这天下午,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停下车,从三轮车座底拽出个新画板:“这是亳州雷锋车队的师傅们凑钱买的,以后不用在纸箱皮上画了。”汪萌香指尖摸着画板边缘的木纹,眼里亮了亮,又很快暗下去——她还惦记着爸的医药费,觉得这些“闲东西”是负担。这时,邵比比的声音从老槐树后传来:“王县长特意交代,给你争取了技校护理专业的名额,学费有补贴,以后能给你爸治病。”她转身时,肘部不小心碰掉了窗台上的油纸包——那是陈明明前几天送的中秋月饼,滚进车辙里碾成了泥饼,她眼圈红了红,却没掉眼泪,蹲下身把碎渣拢到手里。
周末课堂的水泥地还沾着拖把水,王永前老师特意过来,捏着她的手腕教她运笔:“你看这向日葵,得转着圈长才精神,日子也一样,慢慢熬就有盼头。”那天王老师还带了本笔记本,里面记着学校老师轮流帮她补功课的计划,语文老师帮她改作文,数学老师帮她补基础,连美术老师都愿意教她画画。窗外,施素云举着电话跟县妇联的人聊:“孩子要是愿意上学,咱们的‘春蕾计划’也能帮上忙。”直到有天,我们在她满墙的涂鸦里看见幅特别的画:压水井喷着彩虹,彩虹下的玉米地绿油油的,虹光尽头,坐轮椅的老人捧着药碗笑,画角还写着“谢谢明明姐的月饼”。那道彩虹,是她藏不住的希望,也是我们跑了无数趟、说了无数话,终于盼来的微光。
三、雪夜心愿:白衣天使的憧憬
腊月修屋顶那晚,电池灯的光落在灶棚墙角——“温暖过冬”的红纸箱上粘着试卷碎片,底下压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单子:
“透析四次×380元”
“白蛋白两支×220元”
茅草檐上的雪粒子掉下来,砸在药罐盖上“当当”响。她踮着脚给药罐添水,脚边碾着冻土块,小声说:“俺想念护校,三年就能当护士,就能给俺爸治病了,不用再求别人帮忙。”
听见这话时,我手里的锤子差点掉在地上。这是三个月来,她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这么长的话。我赶紧掏出手机,给张守雨部长发消息,给王亚彬县长报信,给王永前老师、施素云、陈明明都打了电话——那天晚上,驻村工作队的灯亮到很晚,我们把之前的帮扶计划又细化了一遍:县民政局的“特困学生助学补助”要尽快申请,街道志愿者每周上门做饭、测血压的时间要定好,施素云管的台账本得提前准备,连她上学后的生活费,都联系好了涡阳县爱心者协会的临时救助。
没过几天,专项帮扶会在村部开起来,陈明明、星园街道包点干部张建宏、朱兴茹都来了。陈明明先翻开笔记本:“我从民政救助站争取了‘特困学生助学补助’,你读护校每年能有点补助费,生活费还能走‘临时救助’。另外,20件军大衣留了两件,冬天给你爸妈用。”张建宏摸着下巴琢磨:“光有钱不行,你上学后家里老人没人管,我联系街道志愿者服务队,每周派两人来做饭、测血压。”朱兴茹接着说:“我懂财务,后续爱心捐赠的钱物,施素云同志帮忙建台账,每笔支出都公开,你也能安心。”
施素云坐在旁边,立刻点头:“我早把账本准备好了!之前没帮上忙,这次一定把账记好,让捐助人放心,也让你能专心读书。”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帮扶方案越聊越细,汪萌香坐在角落里,虽然没怎么说话,却偶尔会抬眼看看我们,眼里的光比之前亮多了。
开春后,老槐树抽了芽,技校招生简章摊在炕桌上。“你看,护校包分到县医院,实习期每月有工资,以后既能照顾爸爸,又能自己挣钱。”我指着招生页上的白衣天使图案说。她爸颤巍巍伸手想按手印,却被“啪”的一声拦住——汪萌香把储蓄卡推到爸面前,卡面还沾着点废品站的灰,里面是她卖塑料瓶、旧报纸攒的800元,卡下压着张画:穿白大褂的姑娘推着轮椅,轮椅轮子转成两朵金向日葵,阳光洒在上面,亮得晃眼。
“俺攒的钱够交第一年杂费,以后还能勤工俭学。”她低着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后来志愿者每周都来,施素云也常带着台账本上门核对捐赠物资,她总拉着大伙的手说:“谢谢你们这么帮俺,俺肯定好好学,不辜负大伙的心意。”我知道,这话里藏着的,不仅是感谢,还有她终于肯向生活敞开的心意。
四、画板晴空:梦想绽放的模样
开春后,晒场的水泥地上满是汪萌香的画——火箭飞船、白衣天使,都画得有模有样。她缩在槐树下勾速写,画的是九个红马甲抬着轮椅过田埂,车辙深得像垄沟,却没挡住脚步。那红马甲里,有亳州雷锋车队的师傅,有亳州市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涡阳县爱心者协会的志愿者,也有驻村工作队的人——我们总说帮她,其实是她让我们知道,每一点微小的努力,都能在孩子心里种下希望。
亳州雷锋车队副队长刘兴伦春节前带着慰问金和学习用具专程到汪萌香家看望慰问,涡阳县爱心者协会会长尹冬冬带领志愿者们携着节日礼品也到了汪萌香家,两股暖流汇聚,为这个困境中的家庭增添了更多暖意。院角的压水井被志愿者刷了天蓝漆,旁边钉着块铁牌:“筑梦井 癸卯年秋”,铁牌旁还挂着施素云帮忙钉的小木箱,里面放着爱心人士捐的画笔。张建宏来村里时,特意给她带了本《基础护理操作手册》;王永前老师也常来,给她带学校的复习资料,跟她聊班里的趣事。她抱着书坐在井台边读,阳光落在书页上,暖得像画里的光景——有次我路过,听见她跟爸说:“王老师说,我要是好好学,以后也能考护士资格证,跟医院里的护士一样厉害。”
晌午,一群娃娃踮着脚往槐树枝上系画板,风一吹,纸页飘得像白鸽振翅。最顶上那幅画里,穿白大褂的人胸前别着向日葵徽章,背景是蓝天和彩虹,彩虹下写着“谢谢所有帮俺的人”。村里人路过,都停下看两眼,笑着说:“这是咱村的小画家,以后要当大护士哩!”陈明明来送救助款时,还带着潘莉的小儿子——小家伙一进村就扯着陈明明的衣角问:“明明姐,萌香姐姐在哪?我要给她看我的画。”
后来收到她寄的快递,驻村办公室的旧景好像就在眼前:台账本上压着半块干硬的馍,铅笔屑洒在“汪萌香”的名字上,画角的小字写得清楚:“护理考试考了第三,俺爸的透析从每月四次减到两次,谢谢大伙一直帮俺,也记着‘大苇子’叔叔之前修过俺家的压水井。”信封里还夹着张新画:井台边,蓝漆压水井旁,穿白大褂的姑娘给轮椅上的老人喂水,旁边站着举画笔的小孩,天边的彩虹跨过大田,把整个村子都染得暖暖的。
这道彩虹,不仅映在画板上,更照进了汪萌香的日子里——从最初的沉默寡言,到后来的主动说心愿,从在纸箱皮上画画,到有了崭新的画板和明确的目标,她的变化里,藏着市委组织部、县教育局、民政局、妇联,还有学校老师、志愿者、村干部们的心血。有时候我会想,驻村工作就像给乡村播撒微光,也许单个人的力量很小,但当这些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像汪萌香这样的孩子的路,也能照亮乡村振兴的路。而那些跑过的路、说过的话、付出的努力,不管有没有立竿见影的结果,只要能在孩子心里种下一点希望,就不算白费。
(燕语信)
编辑/刘兴伦
审核/蒋国辉
监制/任安广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