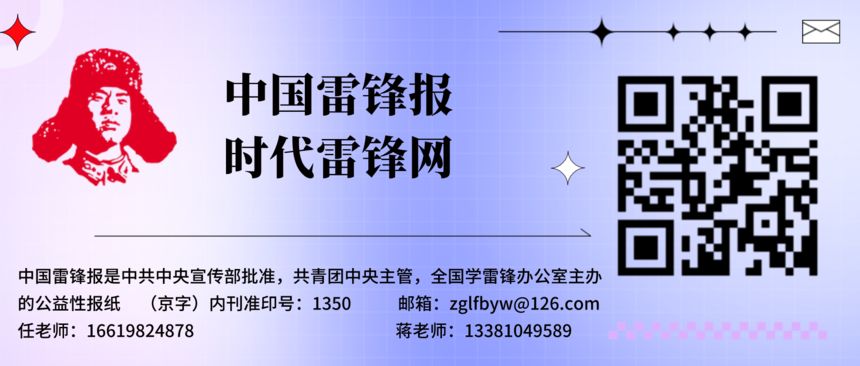曾踏雪往当涂,拜谒李白墓。墓前无香烛,却满是各式酒瓶——玻璃的、陶土的,空的、剩着残酒的,都是寻踪人借酒致意。我揣着一瓶古井贡酒来,红瓷瓶身映着雪光,倒酒时酒香漫开,混着雪气钻进鼻腔。忽然懂了:千年前李白“举杯邀明月”,是借酒抒怀藏山河意气;如今我们以古井相敬,是让皖地醇香勾连古今文脉——这杯酒里,不只有盛唐的月光,更有当代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阔回响,正顺着酒液,融进崛起大国的万家灯火里。
第一层酒,是故友围坐的暖:齐家之温藏酒里,匠心映得家常亮
不必刻意邀约,老友拎着刚出窖的古井贡酒敲门时,粗粝指缝还沾着酒曲碎末,一句“新酒酿成,来尝尝”,便把烟火气拉满。他说车间里的日常:老师傅凌晨三点蹲在窖池边,用手捻起酒醅闻发酵的香;年轻人跟着学“九酝酒法”,记不住步骤就把要领写在围裙上;连董事长梁金辉都常往班组跑,蹲在地上和工人聊“高粱的水分要控在13%才好”——古井人酿酒,从不是冷冰冰的工序,是把“守艺”当日子过,把“品质”揉进家常里。
就像曹操在亳州煮酒论英雄,当年的酒或许简陋,却藏着“以酒明志”的赤诚;如今梁金辉带着团队酿的酒,多了百年工艺的沉淀,却仍保着那份实在。我们围坐小桌,酒杯满上时,酒液晃出的光里,映着少时巷口追跑的泥点,也映着初入社会挤出租屋、就着咸菜抿古井的夜晚——那时一杯酒分三口喝,却能把日子里的苦聊淡。这杯酒暖的不只是胃,是朋友的情、家人的牵挂,更是古井人“以诚酿酒、以情待人”的赤子心,恰如千万家庭窗里的灯火,一盏亮着,就暖了一片人间。
第二层酒,是孤身对影的悟:修身之思浸酒香,守艺如攀万仞山
独对明月斟古井时,看酒液在杯里漾出琥珀色的光,像把亳州的日月星辰都装了进来。酒入喉的瞬间,忽然想起梁金辉说的“酿酒如修身,急不得、躁不得”——他刚接手古井时,为摸清古法工艺,跟着老师傅学制曲,手上磨出的茧子比工人还厚;为守住“九酝酒法”的精髓,哪怕现代机器能提效三成,也坚持手工翻醅,说“老祖宗的法子,是熬出来的真味”。
这清寂里藏着的通透,恰如苏轼“把酒问青天”的叩问:人生起落间,如何守得住本心?答案或许就在这杯酒里——“高处不胜寒”是不贪快的清醒,像古井拒绝用添加剂缩短窖藏时间,宁肯让新酒在地下待上三五年,熬去辛辣留回甘;“无言独上高楼”是沉下心的蓄力,如同梁金辉推动“数字化酿酒”时,一边引进智能监测设备,一边保留手工品鉴环节,说“科技是工具,匠心才是根”。这杯独酌的酒,饮的是寂寞,悟的是“格物致知”的踏实:做人如酿酒,得一步一步磨;做事如攀山,得一寸一寸登,才能在时光里酿出自己的味道。
第三层酒,是笑看浮沉的定:治国平天下的酒魂,酿出大国好风光
酒喝得越久,越品出古井贡酒里裹着的千年分量——从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豪情,到唐宋文人“大江东去”的豁达,再到如今梁金辉带领下,古井扛起的“产业报国”担当。他常说“企业要扎根土地,要带着乡亲一起富”,如今古井周边,高粱种植基地连成片,农民跟着学科学种植,亩产提了三成;包装厂、运输队、酒文旅项目围着酒厂转,上万个家庭靠着这杯酒,日子越过越红火。亳州人说“古井兴,亳州兴”,不是虚话:古井每年纳税额占当地财政近两成,还出资建学校、修敬老院,把企业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分给了这片土地。
这杯酒早已不只是饮品,是撑起一方经济的“支柱”,是连接城乡的“纽带”,更映着大国崛起的模样。如今古井从亳州小酒坊走到国际舞台,梁金辉在海外展会上亲手斟酒,对外国友人说“这是中国的味道,也是中国的文化”;乡村振兴的路上,古井搞“酒旅融合”,让游客走进酒文化博物馆,看传统技艺如何在现代焕新。就像孔子叹“逝者如斯”,时光抓不住,但酒能把瞬间酿成永恒——唐人用酒写就唐诗豪迈,宋人用酒填出宋词深情,而今天的古井人,用一杯酒承载匠心,用一份担当助力复兴,恰如千万盏亮着的灯火,一盏连着一盏,就汇成了大国的星河。
离开当涂时,雪仍落着,我把空了的古井贡酒瓶轻轻放在李白墓前。风裹着酒香掠过,忽然想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千年前李白举杯时,或许不曾想,千年后的中国,会有这样一杯酒,装着匠心、藏着担当,连着万家灯火,映着大国风光。而我们,正捧着这杯酒,在民族复兴的路上一步一步走得踏实:个人修行如灯芯,点亮自己;企业担当如灯盏,照亮一方;国家崛起如星河,温暖人间。这杯酒里的故事,还在继续;这万家灯火的辉煌,还在续写。(燕语信)
编辑/刘兴伦
审核/蒋国辉
监制/任安广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