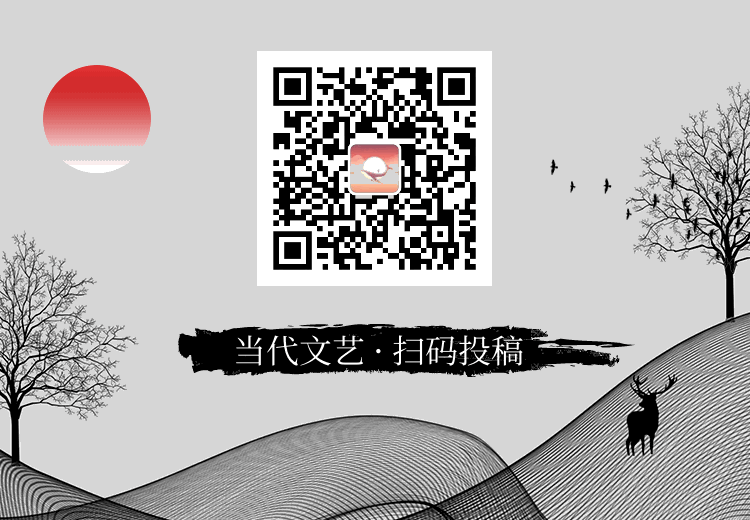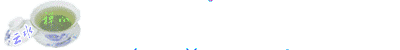江 畔
作者:张龙才
七十年代中期的芜湖,夏末秋初的燥热尚未完全褪去,但比天气更炽热的,是弥漫在全城上下的“上山下乡”运动热潮。红色的标语贴满了古老的中山路和十里长街的灰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激昂的口号,像青弋江的潮水,拍打着无数江城家庭的心。
赵卫东和李援朝,这两个在青弋江边一同光屁股长大的伙伴,就生活在这片临江的街巷里。两家都住在十里长街那排颇具徽风韵味的老门面房的后进,逼仄而潮湿,但邻里关系紧密。父辈同在颇具规模的芜湖造船厂工作,赵父是钳工班的老师傅,李父则在厂宣传科,算是个文化人。两人从小一起在江边摸鱼捉虾,在镜湖畔的柳树下追逐嬉戏,一同读完了芜湖一中。少年时代的友谊,如同江畔坚韧的芦苇,根须紧紧缠绕。
当动员的号角吹响,两个刚满十八岁的年轻人,胸中澎湃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相约报了名。学校里组织的报告会,那些先期下乡的知青代表口中描绘的“战天斗地”的图景,让他们心驰神往。两家大人心里自然是沉甸甸的。赵母和李母私下不知抹了多少回眼泪,芜湖是鱼米之乡,日子虽不富裕但也安稳,想到儿子要去那陌生的山区吃苦,心里是一万个不舍。但赵父沉默地抽着烟,最后说:“让孩子们去吧,响应号召,出去锻炼锻炼也好。”李父则叹了口气:“他俩在一起,总能互相照应。”最终,那份写着“同意”的表格,带着父母的忧虑与期望,交了上去。
分配结果下来,他们被安排到宣城地区泾县的山区。这算是不错的结果,毕竟泾县属于皖南,离芜湖不算太遥远。两人又主动要求,被进一步分配到了离县城几十公里外,更具革命传统的云岭公社向阳大队。那里是当年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下乡行动,更增添了一份神圣的色彩。
离别的日子终于到来。芜湖客运码头,人声鼎沸,锣鼓喧天。江风带着湿气,吹拂着即将远行的青年们胸前的大红花。岸上,是父母亲人殷切又不舍的目光,以及街道干部们挥舞的红旗。扩音器里播放着激昂的乐曲。赵卫东作为知青代表,登上了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他身材挺拔,面容带着年轻人的锐气,用略带芜湖口音的普通话,声音洪亮地念着决心书:“我们坚决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告别城市,奔赴农村,扎根山区,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请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放心!”台下掌声雷动。李援朝在人群中,使劲为自己的伙伴鼓掌,脸上洋溢着兴奋与对未来的憧憬。
“东方红”号客轮拉响了汽笛,缓缓离开码头。甲板上挤满了知青,朝着岸边挥手,呼喊声、哭泣声、鼓励声交织在一起。赵卫东和李援朝扒在船舷,看着熟悉的中江塔渐渐模糊,看着滚滚东流的长江,心中第一次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离愁。船,沿着青弋江,逆流而上。
水路漫长,起初两岸还能见到平坦的田畴和村落,越往南,山势渐渐隆起,绿色变得浓重。到了泾县码头,早已等候的公社干部将他们接上岸。没有片刻停歇,一群知青又被赶鸭子似的塞进了几辆破旧的“丰收”牌拖拉机后斗。拖拉机喘着粗气,在崎岖不平的盘山土路上颠簸前行,扬起的尘土几乎让人窒息。路的一侧是陡峭的山崖,另一侧则是深不见底的山涧。城市青年们哪见过这阵势,一个个被颠得七荤八素,脸色发白。
当夕阳将西边的山峦染成金红色时,拖拉机终于在一个山坳里停了下来。几排低矮的土坯房散落在山坡上,炊烟袅袅。这就是向阳大队。大队部门口,聚集着一些看热闹的村民,他们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皮肤黝黑,眼神里带着好奇与审视。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此刻才真正无情地展现在他们面前。向阳大队地处深山,可用耕地稀少,多是陡峭的坡地,主要种植茶叶和毛竹。知青点被安排在一处废弃的旧祠堂里,阴暗、潮湿,墙壁上斑驳陆离。睡的是大通铺,铺着新晒的稻草,散发着植物和霉味混合的气息。第一顿饭是糙米饭、缺油少盐的炒青菜和一碗看不见油花的南瓜汤。对于吃惯了芜湖米市香米、江鲜的年轻人来说,这简直是难以下咽。
第二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就开始了。学习砍柴,手上立刻磨出了血泡;跟着社员下田插秧,弯腰一天,累得直不起身,蚂蟥还会悄无声息地叮在腿上;上山采茶,要在陡峭的梯田上站稳,小心翼翼地采摘那细嫩的芽尖,一天下来,眼睛发花,腰酸背痛。晚上,躺在坚硬的铺板上,听着山风吹过竹林发出的呜咽声,以及不知名虫豸的鸣叫,思乡之情如潮水般涌来。有人开始低声啜泣,这哭声像传染病一样,很快在黑暗中蔓延开来。赵卫东和李援朝的铺位挨着,黑暗中,李援朝轻声问:“卫东,你想家吗?”赵卫东沉默了片刻,瓮声回答:“想有啥用?睡吧,明天还要出工。”语气里带着一丝倔强,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迷茫。
长话短说。时光如水,几度寒暑,几番风雨。山里的杜鹃花开了又谢,田里的稻谷黄了一茬又一茬。当年的城市青年,皮肤被山里的日头晒成了古铜色,手掌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肩膀也变得宽阔有力。他们逐渐学会了这里的方言,习惯了糙米饭的口感,甚至能分辨出不同季节茶叶的细微差别。他们开始真正了解这片土地和这里淳朴的人们,知道了谁家老人需要帮衬,谁家孩子上学困难。山里人的善良和坚韧,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他们。赵卫东和李援朝,在生产劳动中依旧互相鼓劲,生活上互相扶持。赵卫东力气大,常帮李援朝扛重物;李援朝心思细,会帮赵卫东缝补磨破的衣衫。因表现积极,肯吃苦,两人都被评为公社的“知青积极分子”,奖状虽然只是一张红纸,但在那时,是莫大的荣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的那点激情和荣誉感,逐渐被日益强烈的思乡情绪所取代。回城,成了深藏在每个知青心底最迫切的渴望。远在芜湖的父母们更是日夜悬心,书信往来中,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招工的消息,字里行间充满了能让子女早日回到身边的期盼。赵、李两家作为老邻居,聚在一起时,话题也早已从过去的家长里短,变成了“哪个单位有内招名额”、“今年有没有返城指标”这些沉重的内容。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焦虑。
转机出现在他们下乡的第四个年头。政策似乎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传说表现特别优异的知青,可以通过极少数量的“招工”名额返回原籍城市工作。这个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山塘的石子,在所有知青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希望,如同暗夜中的一点星火,瞬间点燃了每个人压抑已久的渴望。人人都在暗中较劲,期盼成为那个幸运儿。
命运似乎开了一个玩笑。那一年,一个珍贵的返城招工指标,竟然真的分配到了偏远的向阳大队。指标只有一个,而符合条件的知青却不止一人。平静的知青点瞬间暗流涌动。大队党支部为此开了几次会,争论不休,难以定夺。论表现,赵卫东和李援朝无疑是最突出的,劳动态度好,群众关系也不错,历年评先进都有他们。手心手背都是肉,给谁都不合适,都意味着对另一个人的不公。
难题被上交到公社。大队书记老周,一个满脸沟壑的老农,蹲在公社革委会主任办公室门口,吧嗒吧嗒抽着旱烟,小心翼翼地汇报了情况,希望能多争取一个指标。公社主任听完,眉头拧成了疙瘩,语气严厉:“老周啊老周,你也是老同志了,怎么这点觉悟都没有?指标是按计划严格分配的!全县才几个?公社照顾你们大队是先进,才把这个指标给你们!你们要是推荐不出来,那就说明你们工作没做好,或者知青表现都不够格!那就把指标调剂给其他更需要的大队!”
碰了一鼻子灰的老周,垂头丧气地回到大队。无奈之下,他只好把赵卫东和李援朝叫到大队部。昏暗的煤油灯下,老周的脸上写满了为难:“卫东,援朝,你俩都是好样的,是咱们大队知青的标杆。可指标就这一个,厂子是芜湖造船厂的,你俩家都在那儿,正好对口。按理说,给谁都不为过。你俩关系一直挺好,能不能……私下商量一下?谁先走,谁再等下一次机会?我老周保证,下次有名额,一定优先推荐留下的那个!”老周的话语充满了恳切,也带着一丝无力。
最初的沉默之后,是激烈的争执。起初,两人还能保持着表面的客气,但涉及到切身命运,往日的兄弟情谊显得如此脆弱。
“援朝,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是长子,下面还有弟弟妹妹,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我早点回去,也能帮衬家里。”赵卫东率先开口,语气急切。
李援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他是知青里少有的戴眼镜的人,显得有几分书卷气:“卫东,我理解。可我爸妈就我一个儿子,他们……他们也日夜盼着我回去。而且,上次我妈来信说,我爸在厂里好像遇到点麻烦,心情很不好,我回去也能宽慰他们。”
“你的意思是,我爸妈就不盼着我回去了?”赵卫东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能不能更公平地竞争?看谁对大队的贡献更大?”
“贡献?年年先进我们都是一起拿的!砍柴我比你砍得多,修水渠我挑的土方也比你重!”
“劳动不是唯一的吧?我还帮大队办黑板报,教社员识字呢!思想建设就不重要了?”
争吵越来越激烈,往日的默契与谦让荡然无存,尖锐的话语像刀子一样刺向对方。全然不顾老周在一旁连连叹息:“唉,别吵了,好好说,好好说嘛……”
这裂痕,也迅速通过书信,传到了芜湖的家中。两家父母本就为孩子的归宿焦心不已,得知情况后,关系骤然紧张。一次在厂区宿舍的公共水房相遇,赵母忍不住含沙射影地说:“有些人啊,就是会耍嘴皮子,实际干活不出力,还想抢机会。”李母一听就火了:“你说谁呢?我儿子是文化人,动笔杆子也是贡献!不像有些人,只会使傻力气!”多年的邻里情谊,在“谁家孩子先回来”这个残酷的现实问题面前,变得岌岌可危,濒临破裂。
矛盾在不断升级。从最初的暗中较劲,发展到公开的互相埋怨。终于,在一次两家大人因为公用厨房占地问题发生口角时,积压的怒火彻底爆发了。李援朝的母亲情急之下,指着赵父喊道:“赵老大,你别太过分!别以为你们家就多干净!当年你在厂里,不是还偷偷拿过车间里的铜零件回去做煤炉子吗?这事要是捅出去,看你们家卫东还有没有脸争这个指标!”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击中了赵父。他脸色瞬间变得铁青。这件事,是他多年前的一时糊涂,早已过去,他也一直引以为耻。如今被李母当众揭短,他感到无比的羞辱和愤怒。同时,他也想起了一件关于李父的旧事。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老李值夜班时,负责清理一批从图书馆收缴来的“四旧”物资,其中有一些旧的连环画和版画书。老李本身爱好文艺,看到其中一本《黄山松石图》的版画集,印刷精美,一时鬼迷心窍,觉得销毁了可惜,便偷偷藏了起来,带回家欣赏把玩。几天后,他越想越怕,自觉犯了严重错误,又悄悄把画册处理掉了。一次和老赵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他把这事当成年少时的“荒唐事”和“秘密”讲给了这位他认为最可靠的老邻居听,并再三嘱咐:“老赵,这事我可只跟你一个人说过,千万烂在肚子里,传出去可是要命的事!”
被羞辱和愤怒冲昏头脑的赵父,觉得李家先不仁,撕破了脸皮,便也顾不得什么道义和多年的交情了。他要报复,更要为儿子扫清障碍。他将李父当年私藏“封资修毒草”的事情,添油加醋,以“思想反动,私藏并可能传播违禁书籍”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检举信,投入了厂革委会的信箱。
在那个年代,这顶帽子的分量足以压垮一个人。厂里立刻立案调查。无论老李如何辩解“只是一时糊涂”、“早已销毁”、“绝未传播”,都无济于事。没有人关心他是否后悔,是否主动处理掉了画册。他被定性为“思想觉悟低下,深受封资修流毒影响”,受到了严厉处分:撤销宣传科职务,下放到车间最辛苦的岗位进行劳动改造,并接受全厂范围的批判。李家顿时名声扫地,李母在人前都抬不起头。
李援朝在向阳大队,很快接到了家里寄来的充满悲愤和绝望的信件。还没等他消化这巨大的变故,大队书记老周就神色凝重地把他叫去,出示了公社转来的外调公函和芜湖造船厂革委会关于其父问题的证明材料。
“援朝啊,”老周的声音充满了惋惜和无奈,“你的表现,大队和公社都是认可的。但是……你父亲现在这个情况,政审……过不了关啊。这个招工指标,只能……给卫东了。”
消息像一阵风似的传遍了知青点和整个大队。赵卫东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那张薄薄却重若千钧的招工审批表。当他从老周手中接过表格时,他看到了李援朝那双透过镜片射来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了往日的友善,只剩下冰冷的愤怒、鄙夷和深深的绝望。赵卫东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
李家父子,既感到万箭穿心般的愤怒,也陷入了无边的悔恨之中。老李本是个耿直爽快、略带文人气息的人,他后悔自己当年的不慎,更痛惜几十年的邻里情谊和老友的信任,竟如此不堪一击,毁于一旦。当李援朝在春节假期回到芜湖那个笼罩在阴霾中的家时,老李仿佛一夜苍老了许多,他拉着儿子的手,老泪纵横:“儿啊,是爸连累了你……爸对不起你……我们争来争去,争成了这个结果,不值得,不值得啊!我们当初要是能退一步,何至于此!”
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喃喃自语:“我们读了那么多书,却还不如古人懂得谦让。我这几天总想起咱们芜湖老家流传的‘管鲍分金’的典故,那是何等的情义和信任。再想想那‘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诗句。我们这两家,为着一个指标,闹到这般你死我活、家破人伤的地步,糊涂!真是糊涂啊!”他的叹息声,沉重得如同屋外凝结的空气。
李援朝看着瞬间衰老的父亲,听着他充满悔恨的话语,心中的愤怒渐渐被一种巨大的悲凉和自责所取代。他后悔当初没有主动退让,后悔和赵卫东那场毫无意义的争吵。但一切为时已晚,木已成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所有的悔恨、屈辱和不甘,深深地埋进心底,转化为一种近乎残酷的勤奋。回到向阳大队后,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除了拼命劳动,就是利用一切工余时间,捡起早已荒疏的课本,埋头学习。书本,成了他暂时逃离现实、寄托未来的唯一慰藉。
赵卫东顺利办妥了手续,返回了芜湖,顶替父亲进入了造船厂,成为一名工人。然而,他并未能享受到想象中的衣锦还乡和安稳。关于他父亲如何“告发”老邻居,致使李家遭受灭顶之灾的细节,不知如何还是在厂区和街坊间慢慢传开了。人们表面上或许不说,但私下里都指指点点。介绍对象的人一听是赵家,都纷纷摇头,婉言谢绝。媒婆私下说:“那家人,心太狠,几十年的老邻居都能下死手,谁敢把姑娘往火坑里推?”赵卫东的亲事就这样一直耽搁下来。他走在熟悉的街巷,总能感受到身后异样的目光,这让他如芒在背。他开始回避人群,性格也变得愈发阴郁。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几年后,“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这个消息像春雷般惊醒了无数被耽误的青年。李援朝凭借在山区数年坚持自学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在苦难中磨砺出的惊人毅力,在第一年高考中,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安徽大学中文系。那一刻,他捧着录取通知书,在向阳大队那间破旧的祠堂里,泪流满面。这泪水,饱含了太多的辛酸与委屈,也蕴含着新生的希望。
大学毕业后,李援朝被分配到省城一家文化机构工作,凭借扎实的学识和勤奋努力,他逐渐成为研究地方文史,特别是皖南地域文化方面的知名学者。随着国家拨乱反正的步伐,他父亲老李的问题也得到彻底平反,压在全家人心头多年的巨石终于被移开。
而赵家,则笼罩在另一种氛围中。赵卫东的父亲老赵,自那件事后,内心始终背负着沉重的枷锁。邻居的指戳,儿子的婚事不顺,尤其是对老李一家的愧疚,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他原本就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如今变得更加孤僻寡言,常常一个人对着墙壁发呆,眼神空洞。就在老李被平反的消息正式传达的那年春天,一个细雨霏霏的傍晚,老赵不知为何独自走到了青弋江边。有人看见他步履蹒跚,神情恍惚。第二天,人们在下游的江滩上发现了他的尸体。经公安查验,系失足落水身亡。有人说,他是承受不住内心的折磨;也有人说,他是觉得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消息传到省城,李援朝默然良久。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城市的新貌,思绪却飞回了遥远的青弋江畔,那些一起摸鱼捉虾、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仿佛就在昨日。他心中没有多少快意,反而涌起一股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悲悯。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个人的命运,一念之差,往往就是天壤之别。他提笔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中最后写道:“往事已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赵叔叔也已去世,所有的恩怨,都该随风散了。我们都要向前看。”
滚滚青弋江水,依旧日夜不息地向东流去,注入长江,奔赴大海。它带走了岁月,冲刷着两岸的泥沙,也似乎试图抚平历史的伤痕。江畔的故事,关于青春、理想、选择、人性的脆弱与复杂,以及最终的宽恕与释然,都沉淀在流淌的江水中,成为那个特定时代一抹沉默而深刻的注脚。只有那江风,依旧年复一年地吹拂着,诉说着那些或许已被遗忘,却真实发生过的悲欢离合。
【作者简介】
张龙才,笔名淡墨留痕、墨染青衣,安徽芜湖人,爱好文学,书法,喜欢过简单的生活,因为 简简单单才是真,平平淡淡才是福。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追求了过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懂得知足的人,即使粗茶淡饭,也能够尝出人生的美味!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