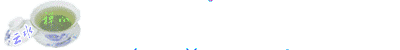小 寒 归 途
作者:墨染青衣
腊月的北风是钝刀磨了七年的刃,一下下刮着长春站广场上每个人的脸。林晚第三次紧了紧驼色围巾——那是母亲七年前织的,线头已经起球,却比任何羊绒都暖。呼出的白气在睫毛上凝成细霜,她眨眼时,霜碎成星。手机屏幕亮起:2026年1月5日,16:37,小寒。
“妈,我上车了,明早到。”发送键按下的瞬间,指关节泛出冻疮初愈的淡粉色。
这是北漂的第七个年关,却是第一次抢到小寒这天的票。候车室里,人群像越冬的鱼群缓慢涌动,空气里泡面、灰尘和归心似箭的气息混成一种奇特的暖。林晚在角落坐下,背包里摸出那本《百年孤独》——书脊开裂,第二百页夹着一朵腊梅干花,花瓣薄如蝉翼,却还留着七年前的淡香。
“姑娘,借个光?”声音沙哑如老树皮。
林晚抬头。老人约莫八十,头发银白却梳得整齐,深蓝棉袄洗得发白,怀里抱着个旧琴盒,二胡的弦轴从拉链缝里探出头来。最特别的是他的手,左手小指缺了一截,右手手背纵横着烧伤的疤痕,像地图上的无名河流。
“您坐。”她往里挪了挪。
老人落座时很轻,仿佛怕惊扰什么。琴盒放在膝上,手轻抚盒面,像在抚摸老友的脊背。
“您也回家?”林晚问。
“回。”老人眼睛望着远处滚动车次的大屏幕,“儿子在吉林市等着。七年了,没一起过小寒。”
林晚心头一紧:“我也七年。”
“七年够梅树开七次花。”老人忽然说,“我家院里那棵,今年该开第八回了。”
广播骤响,人群开始涌动。老人起身时晃了一下,林晚扶住他手臂——棉袄下骨瘦如柴,却稳如老松。
“1948年,”老人站稳后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也是小寒,长春围城。我十四岁,背着这二胡往外逃。”他顿了顿,“手是那时伤的。”
林晚怔住。历史书上的铅字忽然有了温度,烫在心上。
车厢里,泡面撕开声、短视频外放声、婴儿啼哭声混成一片混沌的交响。林晚靠窗,对面是老人。火车启动时,窗外暮色如墨汁滴入清水,一层层染开。村庄零星灯火渐次亮起,每一盏都是一个正在加热的家。
老人打开琴盒。二胡的琴筒是陈年紫檀,琴皮斑驳如老人额头的皱纹。他调弦时,断指在弦上跳动,竟比完整的手指更灵巧。
第一个音符流出时,像冬日第一缕阳光破云——颤巍巍的,却是暖的。
“这不是《二泉映月》。”林晚说。
“《小寒谣》,我自己编的。”老人手指在弦上滑动,“每年这天拉一次,拉完,冬天就短一寸。”
旋律很怪,时而像冰裂,时而像柴火噼啪,转个弯又成了灶台上沸水的咕嘟声。奇妙的是,周围嘈杂竟渐渐低了——抱孩子的母亲停住了摇晃,刷手机的少年抬起了头,所有人都像被无形的线轻轻拽了一下。
列车员推车过来时,林晚买了两份盒饭。老人从布袋里掏出油纸包,展开是两个烤红薯,还烫手。
“换着吃。”他说。
红薯甜糯如蜜,盒饭里的排骨酱香浓郁。交换食物的瞬间,林晚瞥见老人棉袄内袋里露出的照片一角——黑白照,军装青年笑得见牙不见眼。
“我父亲。”老人顺着她目光,把照片完全抽出,“1948年小寒,他留在长春了。母亲每年这天都做一桌子菜,摆两副碗筷。”
照片背面有字,墨迹已晕开:“吾儿,见字如面。小寒至,春不远。替父看看开春的松花江。”
林晚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七年前火车站,他沉默地往她箱子里塞了五盒腊八蒜,最后只说:“北京没有这个。”此后每次通话,父亲总是在背景音里——剁馅声、咳嗽声、关窗声。
“您为什么七年没回家?”话出口她才觉唐突。
老人沉默。车窗外掠过大片雪野,月光下像铺开的宣纸。
“儿子结婚那天,”他终于开口,每个字都斟酌过,“他穿西装打领带,我喝多了,说‘人不能忘本’。他说‘时代变了’。我摔了酒杯。”老人抚摸着琴盒,“后来他公司上市,给我寄钱寄东西,电话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说...我错了。”
林晚手机震动。母亲发来照片:酸菜白肉锅咕嘟冒着泡,血肠切得薄如纸,父亲罕见入镜,正笨拙地摆碗筷,侧脸在蒸汽里模糊又温柔。
“你爸今早五点去排队买的血肠。”母亲追加一句,“说晚晚就爱吃这家。”
她眼眶猛地一热,慌忙低头扒饭。
凌晨三点,火车在小站临时停车。林晚醒来时,老人站在车厢连接处,玻璃窗上结着冰花。他指尖在冰花上描画,画的是朵梅花。
“睡不着?”她走过去。
“年纪越大,越舍不得睡。”老人从兜里掏出个小铁盒,打开是自制卷烟,“我父亲说,人活一世,醒着的时辰是有数的,用一刻少一刻。”
他点烟的手在抖。火光刹那照亮那些伤疤,也照亮他眼中某种深不见底的东西。
“您父亲...”
“最后一批撤出长春的伤员。”老人吐出的烟融进夜色,“他把我推上卡车,自己往回走。我说爸你去哪,他说‘还有兄弟没出来’。”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那年松花江开春特别晚,但到底还是开了。”
雪又下了起来。细碎的,安静的,像天空在筛记忆的粉末。
“其实我失业了。”林晚听见自己说,声音轻得像怕惊落窗外的雪,“公司裁员三分之一。这一个月,我每天在出租屋假装上班。”
老人没回头,只是把烟摁灭:“你知道小寒三候吗?一候雁北乡——雁子开始往北飞,哪怕天还冷。二候鹊始巢——喜鹊开始筑窝,哪怕枝还秃。三候雉始雊——野鸡开始叫春,哪怕雪还没化。”
他转过身,眼睛在昏暗里亮得惊人:“人呐,有时候得学学畜生。春天不是等来的,是叫来的。”
列车重新启动时,天边泛起蟹壳青。老人取出二胡,再次拉起《小寒谣》。这次有人轻声跟着哼——先是那个抱孩子的母亲,哼的是摇篮曲的调;接着是刷手机的少年,调子变成了流行歌;最后整节车厢都弥漫着一种模糊的、杂糅的旋律,每个人都在这旋律里听见了自己家的声音。
林晚望向窗外。铁路边的村庄苏醒了,炊烟从万千屋顶升起,像大地在晨曦中缓缓呼出一口长气。她忽然明白,这世上所有的冬天,都不是靠硬扛过去的——是靠一些微小却倔强的东西:一朵梅花、一首曲子、一句没说出口的抱歉、一锅凌晨五点排队买的血肠。
长春站到了。
月台上,穿黑色羽绒服的中年男人在冷风中跺脚,看见老人时整个人定住,然后飞奔过来,却在两步外急刹。
“爸。”
“哎。”
没有拥抱,没有痛哭。儿子接过琴盒背上,手很自然地扶住老人手臂:“车在P2,雪大,慢点走。”
老人走了几步,忽然回头,朝林晚的方向点了点头。阳光刚好刺破云层,照在他白发上,像落了一层初春的梨花。
出站口,林晚一眼看见了那块纸板——父亲亲手写的“欢迎林晚回家”,墨太浓,顺着纸纹洇开,像开枝散叶的梅。母亲扑上来抱住她,羽绒服摩擦出沙沙声,是这世上最好听的声音。
“瘦了瘦了。”母亲的手在她背上摩挲,一遍又一遍。
父亲拎过行李箱,箱子轮子坏了,他提得吃力却不让手:“血肠再炖就化了,回家。”
车里暖气开得很足,父亲的新车有皮革味。街道两旁灯笼高挂,腊月集市人声鼎沸,摊主在寒风里吆喝:“黏豆包——热乎的黏豆包——”
一切都没变。一切都不一样了。
手机震动,前同事发来消息:“晚晚,有个创业公司在招人,需要内推吗?”
林晚打字:“年后再说。先陪爸妈过个小寒。”
发送。像卸下千斤重担。
家里果然有“红泥火炉”——母亲买的电暖器,做成老式样子,橙光映着天花板上的旧吊灯,影子在墙上摇晃如童年。桌上菜摆满了,中央的酸菜锅还在咕嘟,父亲开了一瓶通化红,给她也倒了一盅。
“喝点,驱寒。”他说。
三盅下肚,父亲的话匣子松了扣:“你走那年,我在你屋里坐到天亮。后来每年小寒,你妈都多摆副碗筷。”他顿了顿,“不是迷信。是想着,万一呢?万一孩子突然回来呢?”
母亲拍他:“大过节的,说这些。”
可她自己眼圈也红了。
夜深,林晚躺在自己旧床上。被褥晒得蓬松,有阳光和樟脑丸混合的味道。她翻开《百年孤独》,那朵腊梅干花飘落掌心——花瓣竟还柔软。
窗外,老梅树在月光下静立。她忽然看清,那些她以为是枯枝的,其实密布着花苞,小小的,紧紧的,像握了一冬的拳头。
手机日历更新:“小寒·三候:雁已北乡,鹊正筑巢,雉始鸣春。”
厨房传来窸窣声。她起身去看,母亲在调明天包饺子的馅,父亲在剥腊八蒜,紫皮蒜在瓷碗里泛着琥珀光。两人没说话,却像合奏一首无声的曲子。
“怎么醒了?”母亲抬头。
“听见春天在敲门。”林晚说。
父亲笑了,七年来第一次在她面前笑得不见眼睛:“那是你妈在剁白菜。”
但他们都听见了——窗外极远处,松花江冰层深处传来第一声脆响。很轻,轻得像错觉。
林晚回到窗前。梅树最矮的枝桠上,一朵腊梅正在月光里缓缓舒展花瓣。不是突然绽放,是慢的,郑重的,像完成一个承诺。
她想起老人下车的背影,想起他说“春天不是等来的,是叫来的”。
这个冬天还很漫长。但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融化——像父亲摔碎又粘起的酒杯,像母亲年年多摆的碗筷,像她自己七年没流过的眼泪。
小寒不寒。
因为人间有归途可返,有炉火可温,有没说完的话可以慢慢说,有错过的春天可以等下一轮。
而此刻,第一朵梅已经开了。
春天正在路上,带着所有迷路的人,一步一步,走回家。
【作者简介】
张龙才,笔名淡墨留痕、墨染青衣,安徽芜湖人,爱好文学,书法,喜欢过简单的生活,因为 简简单单才是真,平平淡淡才是福。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追求了过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懂得知足的人,即使粗茶淡饭,也能够尝出人生的美味!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