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黄河边的冬日思语
文/宋美英
黄河是静的。
我站在齐河红心广场的石栏边,冬日的风从宽阔的河面上削过来,带着一股子干冷的、粗粝的腥气。水是浊黄的,失了夏日那奔腾咆哮的力气,缓缓地、沉沉地流着,像一匹疲惫已极的巨兽,摊开了它古老而皱褶的肌肤。岸边结了层薄薄的、污浊的冰凌,又被水流耐心地啃噬出犬牙交错的边缘。四野空旷,广场上游人寥寥,只有那枚巨大的、鲜红的“红心”雕塑,矗立在铅灰色的天幕下,红得有些触目,也静得有些惘然。今儿是元旦假期的末一天,我却独自又来了这里。心里头,被一些比这河水更浑浊、更滞重的什么,
视线不由地,便飘向了那处缓坡——夏日里,那四个小小的身影,便是从那儿,一点一点,滑入这沉默的巨兽之口的罢。此刻,那里只有枯败的芦苇,一丛一簇,顶着焦白的穗子,在风里瑟瑟地摇,像是大地竖起的、无数面哀悼的旗。可我的眼前,却分明又活了起来,漾开了另一片光景:是七月,天蓝得晃眼,日头毒辣辣地晒着,空气里满是溽热的水汽与孩子们的欢嚣。我们托管班的几十个小人儿,刚在广场上跑乏了,聚在树荫下喝水。他们的眼睛,却都亮晶晶地,齐刷刷地钉在河滩下头。
就在下面,离这规整的广场不过几十步的泥滩上,有四个陌生的孩子,正玩得忘形。一个穿着褪了色的蓝背心,赤着脚,站在刚没过脚踝的浅水里,低头寻着什么宝贝;另一个更小些的,蹲在泥地里,正极认真地堆砌着一座不成形的“城堡”,浑身上下溅满了泥点子,像只快活的小泥猴。还有两个,在不远处互相泼着水,笑声尖脆脆的,能一直抛到我们站的这高岸上来。那真是幅再寻常不过的、属于夏天的、生机勃勃的图画。黄河在他们身后,那时节的水流是丰沛而湍急的,浑黄的浪头一个推着一个,发出低沉的、持续的呜咽。可那声音,在孩子们的欢笑声里,显得那么遥远,那么无关紧要。
我们班的孩子看得眼热,有几个胆大的,扯着我的衣角,声音里满是羡慕与央求:“老师,我们也下去玩一会儿吧,就一会儿!”“看他们玩得多好!”年轻的带队老师也有些动心,看向我。我心里,何尝没有一丝松动?孩子们被课业拘束久了,这难得的撒野时光,这亲近母亲河的渴望,原是这般自然而炽烈。可导游先前的话,像一道冰冷的闸,拦在了那里:“黄河看着平缓,底下暗滩、漩涡多得很,水深水浅没个准数,尤其带了孩子,万万不能下水。”我望着底下那四个无拘无束的小身影,又望望眼前几十双渴望的眼睛,那“不”字,在舌尖打了个滚,终究还是伴着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咽了回去。“不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拿出做负责人的那份不由分说的严肃,“太危险了,咱们就在上头看。瞧,那红心广场多好看。”
孩子们顿时蔫了,小嘴撅得能挂油瓶,羡慕的目光却更黏着地投向下方。我别过脸,心里那点“不甘心”,却像河滩上的水汽,丝丝缕缕地蒸腾起来。我甚至有些羡慕那四个孩子的家长(或许他们就在不远处闲谈?),他们竟能如此放心,给孩子这份野趣的自由。我们的管教,是否太过谨慎,反倒扼杀了一份天性?
那天回到家,已近黄昏。暑热未消,心里头那点事,也像窗外的知了叫,扰得人不甚安宁。我倒了杯水,还没来得及坐下,手机便疯了似地震动起来。点开托管班的家长群,那红色的未读消息数字,正以令人心惊的速度跳跃、攀升。只瞥了一眼,我浑身的热汗,便在瞬间变得冰凉。
消息一条条,触目惊心,带着巨大的惶恐与后怕,炸满了屏幕:
“我的天!听说了吗?红心广场那边,下午有小孩掉黄河里了!”
“是四个!四个孩子!就在咱们去的那会儿!”
“全没了……说是突然一个浪打过来,站水里那个就不见了,去拉的那个也……”
“救援的到现在还没找到人……黄河水那么急……”
“不敢想……咱们孩子下午也在那儿啊!!!”
我握着手机的手,抖得厉害,指节泛白。那些滚烫的文字,化作冰冷的针,密密麻麻地扎进我的眼睛,直刺到心底最深处。耳边猛地响起下午孩子们羡慕的嘁嘁喳喳,眼前闪过那四个鲜活的小身影——蓝背心,泥点子,脆生生的笑。而此刻,他们已被这亘古的、沉默的黄河,吞噬得无影无踪了。一股巨大的、劫后余生般的战栗,从我脚底窜起,瞬间席卷了全身。我瘫坐在椅子上,久久动弹不得。庆幸?是的,有一种近乎虚脱的庆幸,庆幸我那“不近人情”的坚持。但紧随而来的,是更汹涌、更沉重的寒意与哀戚。那四个孩子,他们是谁家的宝贝?他们的母亲,此刻正经历着怎样碎骨剜心的痛楚?那看似平缓的浅滩,那诱惑人的清浅水流之下,竟真的藏着瞬息便足以吞没一切的狰狞。
冷风又起,卷着几片枯叶,在红心广场光洁的地面上打着旋儿,发出“沙沙”的轻响,像一声声细微的、无力的叹息。将我飘远的思绪,重又拉回这严酷的冬日。我望着那一片空茫的、曾吞噬了四个夏日生灵的河面,它依旧那么平静地流着,千万年来,它便如此这般地流着。它滋养了岸边的土地与人烟,听过无数的渔歌与号子,也默然收下了数不清的泪水、悲欢,与来不及长大的生命。它是一位慷慨的母亲,也是一位冷酷的史官。那鲜红的“红心”雕塑,在冬日黯淡的天光下,红得像一团凝固了的血,又像一颗兀自搏动着的、警醒的心。
我想起我的那些孩子们。他们如今,或许正在温暖的室内,写着假期作业,看着动画片,为一点点小事跟兄弟姐妹斗嘴。他们早已忘记了那个炎热的下午,曾怎样眼巴巴地羡慕过河滩下的“自由”。他们不会知道,那一句被他们当时埋怨的“不行”,曾将他们从怎样幽暗的深渊边缘,轻轻地拉了回来。而我们这些大人,这所谓的“负责人”,手里攥着的,又何尝不是一根纤细而坚韧的线?线的那头,是几十个家庭全部的欢欣与未来。那“不”字,有时重若千钧,需要抵挡住所有的恳求、不甘,甚至自己内心那份对“快乐”的迁就。它的背后,不是束缚,而是另一种更深沉、更艰难的守护。
风更紧了,天色向晚,河对岸已亮起了几点疏星似的灯火。我最后望了一眼那沉沉的黄河水。浊浪里,仿佛永远回荡着那个夏日午后,戛然而止的欢笑,与母亲们永无止境的哭泣。而这冬日无声的思语,这冰冷警醒的红心,大约便是黄河,留给岸上生者,唯一慈悲的赠言了。
我转过身,将衣领竖得更高些,慢慢地,一步一步,离开了河岸。身后,黄河水在渐浓的暮色里,依旧不舍昼夜,滚滚东流。那声音,听在耳中,忽然像极了岁月本身,深沉,无情,而又蕴藏着所有关于生命与守护的、永恒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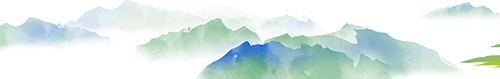



茶水分离 市树市花,扫码聆听超然楼赋
超然杯订购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
丛书号、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