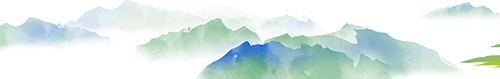话说春节
文/岁月匆匆
这春,来得浩浩荡荡,又来得细腻如丝。当日影在黄道上悄然滑过某个刻度,一种无形的、磅礴的苏醒便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荡漾开来。它并非整齐划一的步伐,而是天地间一场盛大而精密的合奏。当北国漠河还在零下四十度的极寒里,守着漫漫长夜最后一抹幽绿极光,冰封的黑龙江如同沉睡的黑龙,在星光下泛着青凛凛的寒芒时;南国的深圳湾畔,第一朵木棉已不耐等待,“噗”的一声,爆出一团红艳艳的火焰,像一枚小小的、炽热的印章,率先盖在岭南温润的天幕上。是时令的号角,那悠长而不可抗拒的号角,吹过冰封的松花江与雾气蒙蒙的长江,抚过沉默的黄河与渐涨的珠江,越过巍峨的五岳与连绵的三山,最终,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尖上,以几乎无法察觉、却又雷霆万钧的力道,轻轻一叩——于是,年,便这样从大地深处、从血脉源头,悠悠地、确凿地醒了。
醒得最有声势的,怕是黄河岸边那些根须般深扎于黄土的村庄。腊月二十三,祭灶。麦芽熬成的糖瓜,金黄透亮,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甜得粘牙,也粘住了岁末所有匆忙的脚步。那股子醇厚的麦香,混着黄河水那淡淡的、亘古的土腥味,在晋陕峡谷千沟万壑间弥漫,钻进每一孔窑洞的窗棂,缠绕在每一株枣树遒劲的枝桠上。汉子们将一年的气力,对风调雨顺的感激,对来年光景的期盼,都沉沉地夯进那一方方雪白的面团里。巨大的蒸笼坐在比人还宽的铁锅上,灶膛里的火“呼呼”地唱着,那是凡间的祝祷。待笼盖揭开,白茫茫、热腾腾的蒸汽轰然而起,翻滚着直冲窑洞穹顶,那气势,竟与百里外壶口瀑布奔腾咆哮的雾气遥相呼应,带着黄河赋予的、不容分说的暖意与力量,瞬间吞没一切,又在门窗边凝结成晶莹的冰凌花。
而江南水乡的醒,则是另一番韵致,是糯的,软的,浸润在无边丝雨里的。晨光微熹,河埠头石阶上的青苔愈发幽绿。老阿婆用那双青筋微露、却稳如磐石的手,将昨夜浸透的糯米,一勺勺舀进石磨的孔眼。磨轴“咿呀”轻响,乳白的米浆便如泪滴般,绵绵地从磨缝中渗出,流入纱布。滤、压、揉,再拌入新熬的猪板油与秋天存下的糖桂花,那团碧绿的粉团便在掌中活了过来,温润如玉,清香暗透。包好的青团,圆润乖巧,绿得沁人心脾,恰如门前那条不知名的小河——长江某条慵懒的支流——那静默流淌的春水。水是静的,倒映着白墙黛瓦与偶尔划过的小船;日子也是静的,只有厨房里隐约的叮咚和远处若有若无的摇橹声。可那静里,分明孕育着,一股蓄势待发的、春水般活泼泼的生机,仿佛下一刻,就要涨破堤岸,染绿整个原野。
于是,一场星球上最壮阔、也最温柔的律动——迁徙,如期开始了。这不是地理课本上冷冰冰的人口流动箭头,这是亿万颗心被同一根丝线牵引,向着一个叫做“家”的光点,开始的热烈而执着的奔赴。你看见广州火车站那潮水般、仿佛永无止境的人流了么?攒动的人头,焦灼而期盼的眼神,大包小包的行李,汇成了一片由人体构成的、缓慢涌动的海洋,其磅礴与执着,恰似珠江口那昼夜不息、追逐潮汐的浪。那些年轻的脸上,刻着“世界工厂”流水线的疲惫,印着都市写字楼玻璃幕墙的反光,此刻却都闪烁着一层异样的光。他们从轰鸣的机床旁走下来,从闪烁的电脑屏幕前站起来,紧紧攥着的,是一张小小的、却重逾千斤的车票。那车票是现代的符咒,是通往心灵原乡的通行证,一头系着沉甸甸的生计与远方,一头指向那枚名为“家”的强大磁极。
你看见吗?在横断山脉那如巨人褶皱般险峻的盘山公路上,一支支摩托车队正破开凛冽的寒风,倔强前行。发动机的轰鸣在山谷间孤独地回响,后座上牢牢捆着的,不仅仅是给孩子的新衣、给老人的补品,更是整整一年的思念与亏欠。丈夫宽阔的脊背,为身前妻儿筑起一堵挡风的墙,妻子的手臂紧紧环着他的腰,孩子的脸贴在她的背上,在颠簸中沉沉睡去。他们要回到澜沧江边,那个有袅袅炊烟从吊脚楼升起、有宽大芭蕉叶在风中摇摆的寨子里去。还有那掠过天际的银鸟,以云朵为伴;穿越地心与平原的长龙,以山川为邻。它们不仅是交通工具,更像是神话中的灵兽,将上海外滩的时髦光影、北京胡同的雍容大气、深圳街头的速度激情、天津卫的俏皮幽默,统统吸纳、搅拌,发酵成一股复杂而亲切的、独属于现代中国的蓬勃气息,然后,均匀地播撒到每一个翘首以盼的角落,每一个等待填满的胸膛。
这便是中国的“家”了。它不是一个凝固的地理坐标,而是一种弥漫的、可感知的温暖场域。它可以幻化为上海陆家嘴直插云霄的玻璃幕墙上,某一扇窗内为守岁人而亮的那盏孤灯,冷静的光晕俯瞰着黄浦江的流光溢彩;也可以凝练为帕米尔高原雪线之下,塔吉克牧人毡房中央那终年不灭的灶火,火光跳跃,映红着一张被高原紫外线雕刻过的、沉静的脸庞。在山东曲阜周边星罗棋布的村落里,家是厅堂正中那幅巍峨的中堂画,是画下擦拭得光可鉴人的八仙桌,是桌旁太师椅上,白发老者呷一口酽得发苦的茶,对着绕膝的孙辈,缓缓道出的那些“年三十的规矩”与“年初一的禁忌”。老人脸上纵横的沟壑,是比任何竹简史书都更为深邃的记载,那里面藏着“不学礼,无以立”的古训,藏着泰山挑山工般一步一痕的坚韧。而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无垠的雪原上,家是蒙古包门楣上系着的崭新哈达,随风轻扬,是巨大的铜锅里翻滚的手把肉,热气蒸腾,油脂的香气与牧草的清冽奇异地混合。当马头琴苍凉悠远的声响起,那从草原儿女胸膛里自然流出的长调,便如蜿蜒的克鲁伦河,缓慢、深沉,却又蕴藏着融化千里冰封的炽热。好客的蒙古族汉子捧出雕花的银碗,祝酒歌声起,那毫无保留的、太阳般的热烈,真能让草原边缘最顽固的积雪也悄然消融。这“家”的形态,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却奇异般地共享着同一副心肠:一副能将千里万里缩成盈盈一握,能将岁月风霜化为绕指柔的、无比温柔而坚韧的心肠。
守岁的夜,是一年中最为郑重的停顿,是时光河流中一座静穆的沙洲。此刻,“天涯共此时”不再仅是诗句,而是十四亿人共同沉浸的、可触摸的现实。在漠河以北的边防哨所,或许正有年轻的战士,借着极地清澈如水的星光与幽幽极光,与电话那头母亲压抑的哽咽轻声对话。他身后的枪刺闪着寒光,更远处,是沉睡在月光下、辽阔无边的国土,安稳,静谧。在南海曾母暗沙的岛礁上,灯塔规律的光束,如巨人的眸光,划破墨蓝缎子般的海空。值守的人裹紧大衣,望向北斗星指示的北方,那目光穿越重洋,里面有妻儿模糊的笑脸,更有守护一条航路、一片蔚蓝国门的、礁石般的坚毅。这庄严的停顿里,还回荡着“天人合一”的古意遗响。云南丽江古城,纳西人家方正的天井里,或许正举行着古老的“烧天香”仪式。柏枝、青松叶投入火盆,清冽的香气袅袅上升,穿过四合五天井的屋檐,直向墨蓝的、缀满星辰的天幕而去,仿佛是与先祖、与自然神灵一场无声而恳切的对话。而在敦煌,莫高窟静默地立在戈壁滩刺骨的寒夜里,九层楼的飞檐剪影指向银河。窟内,千年前画工笔下飞天的飘带,似乎仍在冰冷的石壁上微微拂动,那穿越时光的色彩,在绝对的寂静中,诉说着另一种关于永恒、关于信仰的“守岁”,悲欣交集,璀璨而苍凉。
当子时如约而至,旧岁与新年在时间轴上完成精准的接驳,积蓄已久的情感与祈愿,终于找到了爆发的出口。爆竹的脆响与电子鞭炮模拟的声浪,从喜马拉雅山脚下沉寂的村落,到东海之滨不眠的都市,从南海渔港停泊的船队,到新疆喀什噶尔老城的巷陌,汇成一片滚地而来、震彻寰宇的春雷。这春雷,惊醒泰山绝顶沉睡的松涛,松针上的积雪簌簌落下;应和着钱塘江口初涨的、试探性的潮讯。它宣告的,是一种彻底的刷新,一次庄严的重启。你看,在湖南湘西某个雾气缭绕的山村,天刚蒙蒙亮,鸡鸣喈喈。族中最为德高望重的长者,已换上整洁的深衣,神情肃穆,率领着黑压压的族人,缓缓打开祠堂那两扇厚重如历史的大门。檀香的气息混合着陈年木料的味道弥漫开来,在祖先层层叠叠的牌位前,他献上新年的第一炷香,烟雾笔直上升,那是血脉承续的庄严信号,无声,却重若千钧。而在东北雪乡,大红灯笼的光晕温柔地融化着栅栏上皑皑的白雪,映得整个院落如同童话幻境。孩子们早已按捺不住,穿着簇新艳丽的棉袄,像一团团跳跃的火苗,尖叫着扑进没膝的、砂糖般蓬松的雪地里,打滚,嬉闹,堆起歪歪扭扭的雪人。那毫无机心、喷薄而出的纯真欢笑,是生命最初的、不受任何拘束的绽放,是献给新年最本真的贺礼。
拜年的队伍,是这一天在大地上流动的、充满声响与色彩的盛宴。在福建龙岩的圆形土楼里,“咔嗒咔嗒”的高跟鞋声与朴实的布鞋声,清脆的普通话与绵软的客家方言,全都混在一起,沿着巨大的环形走廊响起、回荡,汇聚成一首独特的团圆交响。嫁出去的女儿带着夫婿孩子回来了,远行的游子背着行囊归来了,一声声“恭喜发财”、“新年安康”,一碗碗甜到心底、暖到胃里的冰糖枣茶或米酒,将巨大的、堡垒般的土楼填得满满当当,人气蒸腾。那圆楼完美的环形结构,自上而下俯瞰,仿佛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无懈可击的“家”字,将所有人环抱其中,圆满无缺。在新疆喀什迷宫般的老城巷道里,身着鲜艳艾德莱斯绸的妇女,裙摆拂过千年彩砖铺就的地面与墙壁,发出“沙沙”的轻响。维吾尔族大叔笑容灿烂,用不太流利却无比真诚的汉语说着“新年好!亚克西!”。炕桌上,葡萄干、杏仁、巴旦木、馓子、馕饼堆成小山,奶茶的香气四溢。热瓦普或手鼓的乐声一旦响起,无论男女老幼,身体便会不由自主地随之舞动,脖颈的轻移,手腕的翻转,眉眼的传情,那种源自生命本能的欢悦与热情,像天山脉络间骤然融化的雪水,清澈,奔放,沛然莫之能御。
然而,这新生的力,这团圆的暖,终究不是终点。它是一场盛大的充电,一次深情的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初五一过,甚至更早,中国这艘体量惊人的巨轮,便从亲情的港湾缓缓驶出,开始加足燃料,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准备破浪前行。黄浦江两岸,金融区的键盘声与临港新片区的机器声再度奏起精密的复调;深圳湾创业大街的咖啡厅里,氤氲的除了咖啡香,更有熬夜讨论方案时的激烈争辩与灵感迸发的火花;天津港的龙门吊起落不息,集装箱被准确抓起、移动、安放,那钢铁的节奏,是北方广阔胸膛里有力而稳健的心跳。更有一些奋斗,在远离聚光灯的静默处执着地闪光。那是青海柴达木盆地盐湖边上,工程师俯身查看结晶池时,镜片上反射出的、由盐粒与光线共同制造的瑰丽虹彩;是三峡大坝深处某个监测站里,仪器屏幕上那些微微跳动的、关乎千里之外万家灯火是否明亮安稳的冰冷数字;是云南怒江大峡谷最偏僻的山村小学,乡村教师在天色未明时推开咯吱作响的校门,看见孩子们从四面八方山路汇集而来,那一张张被寒风冻得通红的小脸上,比初春最早绽放的山花更为灿烂、充满希望的笑容。
我忽然懂得,这春节,哪里仅仅是一个时序更迭的节日,一场全民参与的民俗?它是这片星球上最古老的土地之一,在某个特定时刻,一次深沉而绵长的呼吸,一次对自身文明基因的庄严确认与集体重温。长江黄河的奔流是它永不停歇的大动脉与主静脉,五岳的沉雄与珠峰的巍峨是它撑起苍穹的脊梁。漠河晶莹的冰雪、澜沧江碧绿的江水、敦煌呜咽的风、内蒙古草原上辽远的长调、新疆戈壁中倔强的胡杨林……都是它广袤肌肤上生动而独特的纹理,记录着光阴,诉说着故事。我们,这大地上的亿万个分子,从天南地北、五湖四海,被同一股引力召唤,向着一个个光点汇聚,完成一场场微小而伟大的“核聚变”,释放出照亮整个寒冬的亲情能量。然后,我们又带着这能量,像被春风扬起的种子,再度散向四面八方。行囊里,塞满了母亲亲手灌的香肠、家乡特产的糕团、甚至只是一捧泥土;耳朵里,灌满了父母絮絮的叮咛、孩子依依的呢喃。我们留下的,是在觥筹交错、围炉夜话中被反复擦拭、又一次确认清晰的“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的身份印记;是被故乡的月光与炊烟温柔抚慰后,重新鼓胀起来的、面对未知前路的勇气与笃定。
美哉,这幅铺陈在烟火人间的壮阔画卷!它从庙堂之高,一直渲染到江湖之远;从繁华都市的璀璨之极,一直绵延至边陲小镇的僻静之隅。每一种生活,无论富足或清贫,无论喧嚣或孤独,都在这个特定的时节,如此认真、如此郑重地“红火”着,仿佛要将全部的生命热情,在这一刻绽放殆尽。这红火,是门楣上的春联,是夜空中的烟花,是碗里的佳肴,更是心底那份无论如何也要过好这个年的执念。壮哉,这血脉中奔流着不息生机的伟大族裔!那有泰山挑山工般一步一个脚印的坚韧,那有黄河船夫般搏击风浪的豪迈,那有江南绣娘般穿针引线的灵巧与耐心,那有草原骑手般纵马驰骋的奔放与自由……所有看似矛盾的气质,都在“中国”这枚无比丰饶、包容的名词下,交融、碰撞、互补,最终迸发出推动文明之舟不断前行的、复合而强大的力量。
当春风终于踱着沉稳的步伐,再度“度”了玉门关,用最轻柔的笔触,染绿西域第一株苏醒的柳枝嫩芽时,这片古老大地上的征程,便又悄无声息地翻开了新的章节。这征程并非史诗中英雄的孤身冒险,它是由每一个你和我,每一个平凡而具体的生命,共同书写。我们用除夕夜的思念充电,以团圆饭的温情武装,将这场名为“春节”的、盛大而周期性的集体充电仪式,转化为推动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浪潮中不断调试、创新、走向复兴的,那磅礴而持久、细腻而坚韧的日常能量。
这,便是中国的春节了。它是原点,是每一次出发时回望的灯塔;它也是归宿,是每一次漂泊后渴望停靠的港湾。它是深情的回眸,检视来路,不忘根本;它更是昂扬的眺望,指向未来,充满希冀。在它周而复始、永恒如四季般的深沉律动里,一个民族,正以最温情、最人间烟火的方式,完成着最坚韧、最惊天动地的成长与蜕变。这脉动,源于大地,深入血脉,响彻云霄,直至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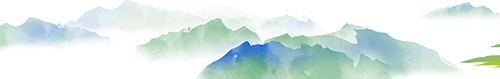



茶水分离 市树市花,扫码聆听超然楼赋
超然杯订购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
丛书号、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